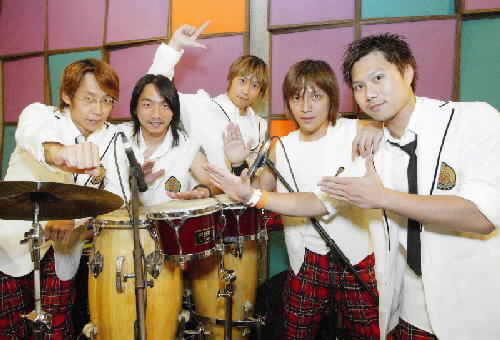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6/12/04 16:54:08瀏覽1131|回應0|推薦3 | |
不過這種工作方式也不是沒有缺點的,正因為它不受任何組織的管束,相對而言,它所受到的保護,在所有的工作方式裡面,也是最少的,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這種工作方式,是以自己個人的工作室,當作上班的地方,因此並不是那種天天或是定期都到公司上班的方式;第二,這種工作方式的收入不固定,通常都是由發案公司給予任務,完成之後才薪資進帳,因此這種工作方式,並不能夠保障固定的薪資收入,而是一種「有任務,才有錢領」的工作方式;然而,社會上的福利雖然有很多種,但最常被我們聽到或看到的,都是銀行所推行的各種福利,然而銀行的福利,基本上仍是在社會制度之下運作的,因此這種所謂SOHO族的工作方式,最大的風險,就是不受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因為目前的福利制度,特別是銀行的福利,大多還是要求申請者「每天或定時到公司上班」以及「固定的薪資收入證明」,然而根據SOHO族的工作特性,很不幸地,恰巧都不符合這兩個條件,所以說「很多身在企業界的上班族,都向我表示他們真的很嚮往『自由工作者』的幸福。但是,他們可曾想到『自由工作者』不受社會制度保障的風險性?」(吳若權,2002:245)。至於五月天呢?他們與經紀公司之間簽有合約,應該是屬於「約聘」,這種工作方式的限制,雖然比自由工作者多,但是,所受到的保障,也比自由工作者來得多。 接著,我再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談吧!五月天可說是台灣目前最紅的團體,筆者也與引文的作者一樣,都在思考五月天走紅的原因,不過從引文的描述當中,筆者就明白了,「講到演唱會,團長怪獸的執著,可以連工讀生對歌迷兇不兇都在意,進場動線、時光、燈光……全都要求,對歌迷的體貼,讓我在八號晚上徹底感受到」(丁靜怡,2005),或許在歌迷的眼中,五月天也是屬於社會行動當中的精英,一種自然領袖氣質的精英;另外,從理性的角度來看,五月天的確可以被稱為一種精英,因為要成為精英,不一定要是科層的、企業的精英,只要能夠凝聚、激發眾人的意識型態情緒,或是天生就具有領袖氣質的人或團體,只要對社會大眾有影響力,都可被稱作精英,因為很顯然地,五月天在台灣的通俗文化場域裡,已經是處於一個「執牛耳」的地位了。五月天對台灣的民眾來說,已經不再是一個由數人所組成的團體,而是一個符號。他們的表演,其實也就是符號的演出,一種擬像的呈現,其實,呈現在你我面前的五月天,是那種經由媒介與其他視覺聲光效果,不斷複製、再現之後的圖像,五月天上的節目、拍的廣告、出的唱片、辦過的演唱會不計其數,他們所呈現出來的圖像,也就隨著不同的時空背景而被一在地複製或再生產,成了名符其實的「五月天現象」,換言之,就是「比五月天更五月天」,這個方面的辯證,尚˙布希亞與尤爾根˙哈貝馬斯是最主要的學者。就五月天來說,筆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為全家便利商店的便當作代言。 通俗文化或大眾文化帶給民眾歡樂,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了,對於文化與社會學者來說,這種文化的現象對於所謂「高雅文化」或「純粹美學」的影響,是他們研究與批判的重心所在,通俗文化研究的始祖---馬修˙阿諾德,是第一個找到審視通俗文化的具體方法,也就是將通俗文化置入文化這個大範疇當中的人,也為文化研究締造了一個「新傳統」,這個傳統便是「文化與文明」的傳統,然而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在通俗文化的「崇拜」現象當中,提出了野蠻人與市儈這兩個概念,並指出其中的「野蠻本性」是受「處境」的變化,而有程度上的強弱。這種觀點或許有些抽象,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卻是隨處可見,「瘋狂追星族」對於各種與偶像有關的符號(如偶像的衣服、照片)之渴望,便是最具體的代表,批判之意不在於偶像,而在於偶像崇拜者(fans)的動作;另外,約翰˙史都瑞在其著作《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當中,指出大眾文化的運作,雖然的確帶給社會大眾歡樂,但是,這種快樂與真正的快樂之間,仍有一段距離,甚至「根據大眾文化的評論,替代性快樂的弊端在於阻礙了『真正的快樂』」(Storey,1997:50),同時,史都瑞引用了范˙登˙哈格的觀點,說明大眾文化的消費現象,其實是一種壓抑,利用大眾文化作品與實踐的特性,來填補內心的空虛,而且,內心越是空虛,對這種大眾文化消費的渴望也就越強烈;甚至還指出,這種文化的消費是具有成癮性的,也就是徘徊於文化的夢魘、無聊與消遣當中的癮君子,就像記者丁靜怡在〈五月天…〉一文當中的描述:「當你專注其中,音樂也能成為讓你暫時忘卻煩惱的嗎啡」,是同樣的道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集體趨騖的現象,集體趨騖依照時間的長短、情緒的強弱、日常生活認同的界定,可分為時尚、時狂、時髦三種,按照三種分類的內容來推斷,五月天的流行是屬於時尚,因為時尚是三類趨騖現象當中,時間最長、最容易被生活化的,因此也可以這樣說,五月天已經變成台灣民眾生活的一部份,無論食、衣、住、行,都可能看到五月天的蹤跡。 整篇〈五月天…〉看起來,是一篇以記敘為主的日記,但是也隱隱約約地,包含了抒情的成分,或許連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她的這篇文章,其實也包含了一些學術的成分,從她的這篇文章,我看到了管理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的相關概念,也就是「SOHO族」、「集體趨騖」、「通俗文化」。前幾天,看到TVBS週刊對於她與部落格的介紹,筆者認為,或許她才有資格,來當一個部落格的推廣大使,不只是因為她的美,也因為她的真與善,因為她除了具有傾城之貌外,也具有如同〈人間四月天〉當中,建築與文學才女林徽音的知性內涵,或許正是這種才貌雙全的特性,而使她受到不少男性的青睞,走筆至此,筆者對於此人的難得,深深地感到佩服……。 |
|
| ( 知識學習|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