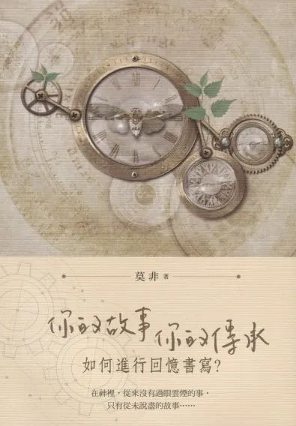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2/01/25 12:20:18瀏覽725|回應0|推薦3 | |
兒時的家幾經變遷,木板地、大榕樹、鞦韆架卻永遠嵌在了記憶裡。孩子離家,父母老邁,在人世變幻中,我們不都渴望一個永恆的家嗎? 清晨,咖啡氤氲中,嫩白透黃的蛋正要起鍋,餐桌旁,女兒倏然回頭,冒出一句:「媽,你想念你的家嗎?」 她眼睛閃爍著。 荷包蛋端上桌。我用圍裙擦擦手,審視女兒面龐。是好奇?善感?她正申請學校,即將到外州讀書。心境在翻攪嗎? 我想念家嗎? 腦中開始搜索,指尖滑出照片,召喚著過去,那孩童時期對家的回憶。 黑白照片中,一座日式平房,在椰子樹下氣定神閒。據說,這原是附近教會外籍牧師的宅所;他因調職返國,爸爸將它買下。 那時的住家大多有院子。L型房舍環繞,中間有個庭院,尤加利和椰子樹列在牆邊,另有迷你池塘和小型球架。 照片中,石質花台前,溫婉的媽媽側身站著,爸爸似笑非笑,瀟灑地一腳踩在花台邊緣,一手插腰挺立。另一照片,徑道自製鞦韆架上,妹妹摟著大氣球,我在後邊裝模作樣,一旁的哥哥單手敬行軍禮。 日式格局的家,進門有道台階,上了木板地,客廳、餐廳、臥房各有拉門分隔。牆上幾扇大窗,盛夏時用不著冷氣,只消打開所有門窗,讓風恣意流竄,帶起木板和磨石地的涼意。
小學時的暑假,日子是過不完的長。午飯後,我抱了一堆童書、零食,霸佔後門台階,在單調蟬鳴及椰樹大葉擺動聲中,與書中人物神遊四海。 後門那棵大榕樹,緊連著舊城門的石砌遺跡,是爬樹及溜滑梯的樂園。前門外鄰家菜圃,種著一畦畦白菜、紅椒、青瓜、紫茄。我和街尾小女孩總順手摘些芫荽,蕾絲細葉散著特異香氣。菜葉、野草地上一擺,就成了菜鋪;買賣間,一下午晃溜而過。 記憶中抹不去的,還有書桌右下抽屜裡那本日記。其中幾頁上的鋼筆字跡被淚水模糊了,記著我和第一隻小狗一起,那歡笑、滿足的日子,還有稚嫩心中死亡的陰影。 家就在回憶裡,有椰樹、蟬聲,有木板地的清涼,還有爸媽的笑,和哥哥妹妹的鬧。 搬走的那天,記憶很模糊。我漫無目標地遊蕩在空屋中,摸摸牆,穿梭於花台、球架間,在拆下來的鞦韆前呆望。 媽媽說我在懷念。 我不知什麼是懷念,只知那天晚上,我睡在新搬進的二樓公寓、我和妹妹的房間,心中悶著說不出的什麼。牆上貼有花彩卡通壁紙;衛浴設備是新式的;房門打開時不會嘎吱作響;新紗窗,蚊子進不來...... 但,我不喜歡。 整整三年後,我們又搬回原處;日式平房杳無蹤影,眼前矗立著六層樓建築。經濟起飛的年代,台北市擔不起菜田、平房或空地。原來菜園之處,成了大樓的一部分,前面開了新馬路;後門仍是巷弄小道,大榕樹與石砌滑梯因處於不起眼的巷弄,存留了下來。 爸爸與建築師設計的新家,仍保有些許庭園;椰子樹逃過一劫,不搭調地聳立在高樓中。窄隘園中另種了七里香,伸枝展葉,奮力捕捉園中僅有的陽光。房內一派大理石地磚,客廳有嵌入式照明,玻璃大窗開向花園,另有檜木屏風、西式酒櫃及木雕實心門。
家,藉著些許存留景物——椰子樹、大榕樹、石砌滑梯,將兒時記憶從日式平房延續到新式大樓。 房子大了,爸媽忙於事業,在家的時間少了。哥哥從高中起就在學校住宿,我和妹妹有各自的房間,躲在青少年的世界中。 記憶中的家,隨著時序前行、改變。 我也改變了,整個人浸在青春的浪漫中。家的安全感是理所當然,理所當然地忽略。我夢想拎著吉他、行囊,哼一曲《橄欖樹》,到遠方流浪。 遠方,就是大學畢業後,踏上海洋彼岸的小城鄉。學位或許是目標,但那「夢中的橄欖樹」,飄逸的「詩與遠方」,更是年輕心靈的嚮往。 小城內學生宿舍裡的一間房,成了暫居之所。五斗櫃旁一張單人床,側邊緊挨著落地明鏡,映出自己的孤獨。書桌靠窗,窗外藍天紅楓,大雁秋歸時,傳來一聲聲寂寞。 期待要擁抱天地之廣闊,卻被語言隔閡與課業壓力,限制在宿舍、圖書館、實驗室的狹窄中。一場不成熟的愛情,是隨風消散的山嵐;關係最終結束時,過客的漂泊不再是浪漫的曲調,而是載沉載浮、險將滅頂的深淵。我急切想抓住一個根、一個支柱。 想家。 嚮往流浪的我,離開記憶的家,在千萬里外的陌生地、磕磕絆絆中,才發現自己何等需要家。 家,不單是房舍庭院,更是家人,以及愛與接納。
兩年後的夏日,在遠方、在藍天下,那幢頂著白色十架的紅磚建築裡,傳來詩班的歌聲: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願站立堅定,如酷熱天遠行辛苦,進入磐石陰影;如曠野中欣逢居所,長途喜見涼亭......」 我從浸禮池中起來,感到一身輕省,透過彩繪玻璃射進的陽光,灑下溫柔的明亮。這裡是盛夏的庇蔭處,是曠野的安歇所,是心靈的家。 心靈有居所,而記憶中的家仍不斷轉變。父母的家,正拆解、重組、轉化。 三兄妹各自結婚,有了自己的家,也添了成員。我們在父母家來去走訪;大理石地磚上,沙發桌幾都撤了,讓小三輪車來回騎溜;「爺爺、奶奶」、「公公、婆婆」的稚嫩喧囂,震著酒櫃上鬆動的玻璃。媽媽從廚房端出一盤盤點心,爸爸操濃厚鄉音,吆喝著維持秩序,卻難掩滿足的笑容。 擋不住時光流逝;孩子大了,父母老了。哥哥把父母家作了整修,進門階梯改成無障礙坡,臥房浴室的門框加寬,讓輪椅容易進出。牆邊釘著扶手桿,中風的爸爸能稍稍扶著站立。媽媽不再忙於進出廚房,而是推著爸爸進出醫院。菜香、歡鬧已成往昔,取而代之的是房間散出的酒精、藥味,和氧氣桶的歎息。 世上的家,為什麼就無法一直維持記憶中的美呢!
對爸爸過世,雖早有預備,但失去爸爸的家,留下的空白與失落,深深嵌在心中。 人世間的悲喜,不斷地添在家的記憶中,一層,又一層。 多年過後,媽媽也有了自己的生活步調:家事、菜場、運動、聚會,看書報,籐椅上打盹。打開客廳兩扇大窗,園中依舊飄著七里香,伴著樹上白頭翁的碎碎念;夏秋風大時,椰子樹仍沙沙作響。物換星移,家中氣氛變換成另一種,那走過歲月的沉靜、安詳。 沒變的是後門的石砌滑梯,沒變的是那棵椰子樹,沒變的是,家人中間愛的聯繫,無論遠近,無論生死。 我一頁頁滑著照片,向女兒解說,笑著、嘆著,卻發現女兒眼中閃爍著淚,眼眶暈紅,不一會兒,竟紅到鼻頭了。 從小未曾離家的女兒,怎有什麼思鄉情呢? 「不知為什麼,或許是因小時候,你們常告訴我以前在台灣的事,我總是看中文卡通、圖畫書,家裡有許多東西......」女兒指著櫥櫃上一個不鏽鋼扣蓋式便當盒,「比如說看到這個,都會讓我很想念,想念你們那個時代,好像我以前就住在那兒,是從那裡來的。」 想念一個未識之處,未曾長住,甚或從未親身經歷,但卻渴望回到那個家! 作家伊莉莎白·雪瑞爾曾描述過類似的感受。她留學歐洲時,首次看到英國景色,那雨霧中的建築,那陌生之地,卻好似孕育她的家園。她無法控制,流下思鄉之淚。那種「歸家」我屬於這裡的強烈感受,卻是向著一個從未到過的地方。
多年後,當她找到了信仰,進入天父家中,她再次嘗到歸鄉感。這心靈的歸宿告訴她:「你有一個終極家鄉,你不會流浪;有一處為你預備好了,是愛與接納的地方。」 記憶的家和現在的家,都在不斷變更;房舍改建,孩子離家,父母老邁,在人世變幻中,我們不都渴望一個永恆不變的家嗎? 耳邊又響起多年前詩班的歌聲: 「在主耶穌十架下,我願站立堅定,如酷熱天遠行辛苦,進入磐石陰影;如曠野中欣逢居所,長途喜見涼亭;到此得釋肩頭重擔,養力奔赴前程......我願在主十架下,為我定居之鄉......」 是有一個永恆的家,為你我預備著。 -END- 作者介紹 羨曦 來自台灣,大學後赴美讀研究所,在留學期間信主。現在與先生及三個孩子住在密西根州。以前學的是分子生物,有了孩子後成為全職媽媽,孩子獨立後開始擁有自己的空間,尋回以往喜愛的讀與寫。2016年開始參加創文網路課程,裝備自己,並摸索文字事奉的道路。2019年加入創文團隊,學習服事。 圖書推薦
《你的故事 你的傳承》 莫非 著 在神裡 從來沒有 過眼雲煙的事 只有從未說盡的 故事 購買資訊: 台灣:橄欖華宣https://www.cclm.com.tw/book/19318 北美:gcwmi622@gmail.com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