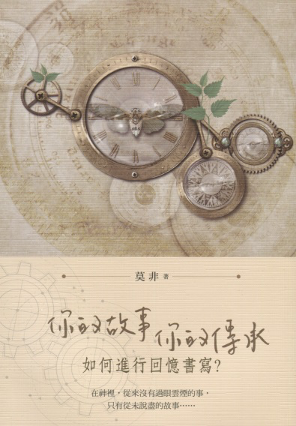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2/01/07 12:05:15瀏覽668|回應0|推薦6 | |
順境並非好運氣那麼簡單,逆境並非沒有價值。作者追述在德國的留學歲月,原來都是最好的安排,令人回味悠長。 德國中部有一座小城市哥廷根,只有十多萬人口,卻擁有一項世界紀錄——這裡的市立公墓,埋葬著全世界最多的諾貝爾獎得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個又一個影響了現代科學進程的人物匯聚在這個小城,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強悍的科研小宇宙:量子力學的開創者馬克斯·普朗克、量子力學的奠基者沃納·海森堡、「數學王子」約翰·高斯、熱力學第三定律創始人瓦爾特·能斯特、愛因斯坦的老師赫爾曼·閔可夫斯基...... 我,一個高考數學連一半分數都沒拿到,高中物理長期不及格的文科生,從來沒想過自己的人生會和這樣一座科研之城發生什麼交集。哦,對了,我知道這座城市,也是從一位文科生那裡——看了《留德十年》,才知哥廷根大學是國學大師季羨林的母校。 讀那本書時,我即將到德國的另外一座小城市做交換生。從老家坐夜火車去辦留德簽證的途中,我翻開了這本小書,邊看邊幻想自己未來一年在德國的生活,美好的或是艱辛的。甚至一路想到,離開之時也要仿季老的文題,來一篇《留德十月》。想著想著,意識便矇矓了,一路滑向夢鄉,不知火車正轟隆隆地急速開向我命運轉折的方向。 結束交換學年之時,我確實寫了一篇《留德十月》的仿作。沒想到的是,又過了十個月,我竟然拿到了哥廷根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那年秋天,我獨自飛到德國,從法蘭克福機場坐火車到了哥廷根。一下月臺,就看到一個醒目的牌子,上書Stadt, die Wissen schafft——「創造知識之城」。
我去哥廷根的路無比順暢。當年還不認識神,常常連連驚呼自己運氣太好了。信主後再回望,在聖靈的光照下,一個接一個的恩典顯現出來,才後知後覺是神一直在為我開道。 我申請德國大學的時候,只寄出過一份申請材料。倒不是我孤注一擲,我剛準備寄第二份申請的那天,出門前順手查了下郵箱,發現自己已經被哥廷根大學錄取。因為哥大的申請截止時間比一般德國大學都早,所以我在身邊同學還吭哧吭哧準備申請材料的時候,就已經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引人羨慕。 當時也有掙扎。因為我特別喜歡柏林,很想去那裡讀書生活。但是申請柏林的大學,要經過一個特別繁瑣的程式,耗時極長,還不知道是否能成功。而我必須在幾周內決定是否接受哥大發出的錄取通知書。我的德國導師認為,學校和專業都很不錯,如果放棄很可惜。而我本身有點懶惰,雖然愛柏林,但是想著繼續申請的麻煩勁兒,就想算了算了。做出決定之後,我連已經準備好的海德堡大學的申請書都懶得再寄出,一心準備去哥廷根。 錄取通知書有了,下一步要解決的就是住處。哥廷根是一座典型的德國大學城,人口的五分之一都是學生。在這裡,學生宿舍顯然無法滿足需求,租房是件很困難的事。許多留學生因為沒法提前到那裡找房,初到之時不得不住旅館。而我當年,在網上隨便看了幾個房源,寫了幾封郵件,再拜託我在哥廷根的直系學姐看了下房,非常輕鬆地遠端敲定了住處。 然而,真正踏上旅途的時候,卻有意料之外的沉重。 在我出發的前一日,奶奶過世了。那天,我拖著行李箱,直接從靈堂趕去機場。背負著百斤重的行囊,輾轉五座城市,花了兩天兩夜。我頂著失去至親的劇痛,一路哭到德國。在疲憊不堪,悲痛虛脫中,開始了自己的留學之路。
神預備的路,祂也會陪伴到底。初到哥廷根,我受到了諸多照顧。 還沒下火車,神就為我安排了一位好心的中國大哥。好巧不巧,我們坐同一節車廂從機場輾轉到同一個並不熱門的目的地。一路上,我們也未曾搭話。下車時,我費勁兒地從行李架上取出一堆大大小小的箱包時,他大吃一驚,連忙上前幫我搬運行李,還請來接他的同事開車送我去了暫住之地。後來又幫我搬家,陪我度過了在異國他鄉的第一個中秋節。 這位大哥姓陳,從國內來出差。哥廷根並不是一個商業發達的城市,除了大學之外,幾乎沒什麼大型企業團體。可是這裡偏偏就有一家很低調的計量行業隱形冠軍,在中國也有分公司。而我不早不晚地遇見了中國分公司每年會來德國出差一次的陳大哥。 那時候,我遇到很多「剛巧」的事情——學姐的室友剛巧有幾天不在,讓我初到時可以暫住;新房子沒有網,剛巧有熱心鄰居願意讓我蹭網;買二手生活品,剛巧遇到一位大姐要回國,半賣半送把東西都給了我,還主動用自行車幫我運送;因為喜歡做甜品,在網上求購烘焙用品,剛巧有素不相識的網友想念從前在英國留學時常吃的scone,便送我一套烘焙模具,讓我做scone來交換...... 如此種種剛剛好的善意,包裹住了我脆弱悲傷的心,像是神加在我身上的降落傘,讓我安穩地降落在異國小城,開始了新生活。
神為我在哥廷根安排的第一個住處非常特別,是個巴勒斯坦人聚集的小樓。除了路遇的陳大哥外,我在哥廷根交的第一個朋友是Ahmed,一位在耶路撒冷長大的穆斯林。他的房間在走道的第一間,正對著樓梯口。我第一天提著大箱子上樓的時候,他看見我就熱情得像個房屋仲介,幫我把行李拿到房間,又馬不停蹄地帶我參觀公用廁所和廚房,告訴我周圍有什麼超市餐館。 那時候還沒開學,我也不認識其他人。因為住得近,常常去他那裡蹭網,我們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有次我在他牆上看到一張奇怪的表格,問他是什麼。他說那是穆斯林每日禱告的時程表,並開始和我說起了信仰。從一個穆斯林小哥那裡,我第一次知道了,原來聖經分為舊約和新約,而穆斯林也會讀舊約。 我雖然對宗教信仰不太瞭解,但是一直很好奇。當時哥廷根的華人團契做迎新活動,會送許多小禮物。我本來想去參加一下,領點所需的日用品,順便再多聽關於基督教的知識。之前提到的那位好心幫我送貨上門的大姐,一邊推著自行車,一邊勸我:「你可千萬別去,去一次就會被教會的人纏上。我有個朋友成了基督徒,就天天給我傳福音,我煩死了。」 我生性愛自由,聽她這麼一說,立馬被勸退。雖然初到哥廷根,生活處處被眷顧,但是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恩典都是從神而來,單純覺得自己運氣好。隨著學業的繁忙,時差和上網不便帶來與親朋好友的隔絕,我很快就撐不住了。 在哥廷根的第一個冬天,我陷入了深深的抑鬱。金色褪去,陽光日漸稀疏,白雪覆地,一切歡悅都被掩埋。
那時候好鄰居Ahmed也搬走了,我孤獨時也不能隨時找人聊天。房間裡依然沒有網路,無法聯絡遠方親友,我孤苦伶仃,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我迎來了人生中久違的低潮,各種不順隨著我的恍惚度日接踵而來。我一面疲於解決各種突發事件,又一面更加抑鬱,進而引發更多大小事故,陷入一種不得解脫的惡性循環。 在外人看來,我只是過得有點神思恍惚,興趣缺缺;而我覺得,自己被困在了某個虛無之境,再也出不來,與歡樂隔絕。就彷彿陷入一片荒無人煙的皚皚白雪中,又或者是墜入了永無陽光的深海。悲觀、絕望、莫名的煩躁纏累著我,讓我生無可戀。 不認識神的時候,困在虛無的絕望裡真是苦啊,但是神卻沒有棄我於不顧。 幾個月後,我意識到自己一個人撐不下去了,想要換個有網的房子,最好有室友可以陪我說說話。那時候雖然並不懂得禱告,但是依然經歷了一想就實現的奇蹟:某天我隨手刷了一下學校後勤網頁,居然刷出一個馬上能入住的雙人間,而且是在全校最受歡迎、申請排隊時間最長的宿舍區。我和同班同學Ada一起去看了房之後,非常滿意,立即租了下來。 Ada是個熱情又體貼的阿爾巴尼亞女孩,和她同住之後,我常常被她明朗的笑容和關心治癒,狀態好了很多。然後我又發現,還不夠,我內心還是有一種無法抹平的空虛感。想了想,也許是缺少可以和我用母語進行深度交流的朋友。我有兩位同專業的中國同學,但只是泛泛之交。其餘好友都是外國人,感覺關係再好都有一層難以跨越的隔閡。 於是我又開始發愁:我要去哪兒認識點中國人呢?總不能在大街上看到一張亞裔臉就攔下來,問能不能交個朋友吧?
機會很快就來了。在一個學校組織的活動上,我偶然認識了一個基督徒姐姐。她30多歲的人了,還是三個娃的媽,但是皮膚白皙光潔,目光靈動如少女,臉頰的酒窩裡盛滿甜美的微笑,恬靜而美好,讓人很想知道她的喜樂從何而來。 我主動和這位姐姐搭訕,說起了自己想多認識點中國人。她說:「你要不要去哥廷根的華人團契看一看?」我想起之前那位大姐的話,心中有幾分遲疑。她似乎讀懂了我的心思,又補充道:「不一定非要有信仰才能去,那邊也有很多慕道友,不用有壓力。學語言的人,也應該多瞭解下這個國家的文化,沒有壞處。」 因為對她一見就有莫名的好感和信任,我欣然走進了教會。 我其實很害怕一個人去跟所有人都不認識的聚會場所。第一次敲開牧師師母家的門去查經的時候,我非常緊張。可是大家只是熱情地招呼我吃飯,並不把我當作外來者,給予我過多關注。我開心地大吃一頓之後,就放下了拘束感。 那一天,我還認識了兩位讀博士的女孩子,我非常欣賞她們。和她們的友誼,是我最初保持一直不斷去教會的動力。 而教會的愛筵則是我留下的另外一大理由。一顆被德國硬麵包折磨到死的胃,得到了中國大碗熱菜的深深撫慰。神真是太瞭解我了,先用這種方式吸引我,因為我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吃貨。 我不得不承認,最開始去教會,只是為了讓孤苦的留學生活變得豐富一點。可是漸漸地,我就對基督徒的生活發生了濃厚興趣。我清晰記得,這個轉變發生在一次分享會之後。 那天,在場的基督徒都毫無保留地剖開自己的生命,與眾人分享。那些生命中最殘酷和最喜樂的時刻都被擺在桌面上,彷彿是獻給神的祭品。他們的真誠,情到深處的眼淚,信主之後的如釋重負,讓我的心緒久久難平。
平日裡,我只跟要好的小姐妹混得熟,對其他人瞭解不多。可是那次聚會之後,團契裡的基督徒對我來說不再是只知道名字和面孔的扁平存在。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如此立體地呈現在我面前,讓我知道了神可以如何改變一個人。 那天,我聽了許多讓我感動的故事。而我最想記下的,卻是一句話:「這個世界到處充滿懷疑,但是幸好有一樣是可以讓你堅信的,那就是上帝。」 當我聽見一位姐妹用異常溫柔而堅定的語氣,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簡直羡慕得快哭了。因為,我被擊中了軟肋。 長大後,脫離了小孩對大人權威的信仰,我突然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對所有人和事都抱有很大的懷疑和不信任。這種感覺其實讓我很孤苦無助,整個世界失去了可以安心依靠的支撐。我曾經和好友討論過,因為這是個無信仰的時代,所以我們才會活得如此迷茫空虛。那位姐妹的話,像黑暗裡的微光,讓我點燃了一個希望。也許,她的神也可以是我今生最堅實的依靠。 那次分享會之後,我決定不是只去嘻嘻哈哈混飯吃。我想好好讀《聖經》,也想更多了解基督徒的世界。我期盼著,也許有天我也會福至心靈,找到堅信上帝的理由。 我真正認識上帝的路,道阻且長,此處暫且不細表。後來,我因為搬家換城市,輾轉過數家教會,才後知後覺,當初神在哥廷根為我預備了多麼好的一個團契。和北美華人基督社區的興旺不同,歐洲國家極缺華語傳道人。德國許多商業發達,華人密集的城市都沒有固定牧師。而在華人不足千的哥廷根,卻有牧師夫婦駐紮,後來還來了一位對慕道友頗有負擔的全職傳道人。 哥廷根教會還有非常紮實的成人主日學,有精通希伯來語的姐妹講解猶太經典,讓我信主之前就對《聖經》有概覽式的瞭解,每個主日,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吃得飽足。我雖然一直內心堅硬,但是卻懵懵懂懂地以慕道友身份為教會做工——因為每次愛筵都吃太多,十分不好意思,於是自告奮勇開始司廚。 後來,我搬去其他城市,才驚訝地發現,很少有教會每周聚會都有愛筵。通常德國的華人教會,都只有茶點供應。一來因為人多,難以操作,二來也有成本考慮。 神多麼眷顧我這個吃貨啊,直接為我準備了一個最適合我的教會。
當然,神的心意並沒有那麼簡單。「愛筵」這個預備,並不僅僅為了滿足一個久久不願回轉的孩子的口腹之欲。在司廚的過程中,我一直背著慕道友的身份,卻毫無違和感地融入了基督徒的世界。因為,我在還沒有真正認識主之前,就不知不覺成為了祂的同工。 這又是一個獨特的安排。在柏林教會,慕道友是沒有資格參加服事的。後來,我搬到柏林,一直找不到歸屬感。我和教會之間有一道無形的牆,一道橫亙在沒有決志的我和已經受洗的基督徒之間的牆。我像一個被禮貌對待的客人,遠觀著他們的熱心與虔誠,卻被擋在神國的大門外。 雖然當年我那麼想去柏林讀大學,卻順其自然地去了哥廷根。這樣一條看似違背我初衷的路,其實是神早已為我安排的,最恰當的屬靈之路。如今回首在哥廷根的年日,每一幀回憶都有神恩典的顯影。只是當年還不認識主的我,對此毫無知覺。 想起季羨林在《留德十年》序言裡,借用納蘭性德的一句詩詞來總結自己在哥廷根的日子——「當時只道是尋常」。是啊,當時只道是尋常,豈知尋常當中皆是神保守和帶領的草蛇灰線。 幾年前,我重回哥廷根訪友。火車緩緩駛入車站,我抬頭又望見那句哥城的標語——「創造知識之城」。在這座城市,我認識了神,認識了那個真正創造知識的造物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哥廷根正是我得著智慧的開端。 —END— 作者介紹 阿門 教育文化行業工作者。喜愛美食美景,從文學、音樂、繪畫、雕塑、舞台劇等藝術形式中汲取養分。2021年開始在創文書苑學習為神寫字,希望筆下能流出活水江河。 圖書推薦
《你的故事 你的傳承》 莫非 著 在神裡 從來沒有 過眼雲煙的事 只有從未說盡的 故事 購買資訊: 台灣:橄欖華宣https://www.cclm.com.tw/book/19318 北美:gcwmi622@gmail.com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