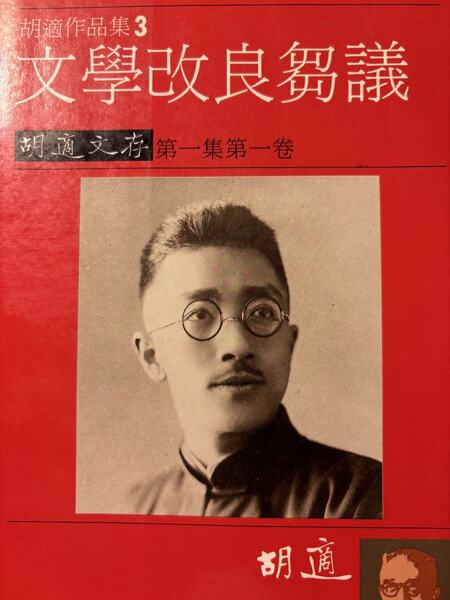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07/27 16:06:17瀏覽144|回應0|推薦8 | |
第一部:堂堂溪水出前村(原作於1993年,原名:「三十歲以前的胡適之」。2024年修訂) 十三 前面提到,胡適把自己對文學革命的「八不主張」寄給陳獨秀,後來略加修改,總結自己的意見與和朋友討論的心得,發表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由於顧慮到國內守舊勢力很大,還是哥大學生的胡適在國內也沒什麼名氣,所以這篇文章的標題相當謙虛──「文學改良芻議」。然而這篇文章力量之大,造成了民國初年的「新文學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千百年來「語、文分家」的文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文獻裡,這篇當數第一(註1)。當時的新青年還是通篇文言,主編陳獨秀對新文學的形式結構,還很疑惑,看到這一篇文章後,再無懷疑,在下一期新青年裡發表「文學革命論」,盛稱胡適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之急先鋒」,並激烈表示「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聲援。」(註2) 此二文一出,引起廣大的迴響,連古文學家錢玄同也贊成新文學的主張。1918年,新青年開始登載白話文,並采用胡適最先提倡的新式標點。同年4月,身分已是北大教授的胡適,在新青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明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國語來創作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才有文學的國語,如此「國語」才是真正的國語。這聽起來有點夾纏,但其實很簡單──我們怎麼說話,就怎麼作文;也就是說,我們既然講的是大白話,我們就應該用大白話寫文章。白話寫成文章,是一種「鍛鍊」,逐漸的我們的白話就會變得精緻,然後再回到我們口說的國語,也會變得生動又活潑,充滿了文學的元素(註3),這就是胡適主張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註4)。胡適同時為「白話」的這個「白」字,下了一個註解(註5): ──白話的白,就是戲臺上「說白」的白。當時戲臺上的各種戲曲,唱詞可能都文謅謅不容易懂,但是說白卻都是用大白話。 ──白話的白,就是清白的白,明白的白,只要說清楚講明白就可以了,所以就算其中加了幾個文言字眼,只要大家都聽得清明,就是白話。 ──白話的白,就是黑白的白,乾乾淨淨不用堆砌,把事情講明白就好。如果故意用一大堆詞藻來繞圈圈,讓人看不懂,那就不是白話,跟詰屈聱牙的文言沒什麼兩樣。 胡適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他不但把白話提升,而且把白話解放了。試看他的「八不」,其實都是在矯正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文學陋習,並不是什麼桎梏教條。比如他說「不用典」,其意是指不該用很冷僻的典故叫人看不懂,也不該刻意用典故讓原本可以清楚表達的意思顯得彆扭,而不是什麼古人古事都不可以提到;又比如「不避俗字俗語」,其實重點在「寫實」,一個鄉村老婦講話,難道會像古文家一樣駢四儷六?怎麼講就怎麼寫,才是真實的文學;又比如說對仗,並不是完全不能用,但這是只是雕飾文藻的末技,不應該掩蓋文章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如果只是妙手得之,增加文章的趣味或感覺,自未嘗不可(註6)。 注意胡適這兩篇歷史性的文章,其一發表於1917年1月,其二發表於1918年4月,中間相隔了一年多,我有點懷疑,後者刊出的時間是經過考慮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這一年多的「新青年」上,陳獨秀、劉半農、傅斯年等都發表了討論文學革命的文章,各種讀者來函、通訊討論也是一篇接一篇,但是「新青年」的銷路還是只有可憐的一兩千本,1917年下半年甚至因為訂戶太少而停刊半年。也就是說,文學革命的「火」雖然被點起來,但並沒有如預期的「燎原」。這時候,鬼點子最多的錢玄同,決定同語言學家劉半農合作,出一道「奇兵」,為白話文學運動加溫。錢玄同虛擬了一個人物叫「王敬軒」,投書1918年3月的新青年,名為「文學革命之反響」,用一副遺老的傲慢態度,大罵白話文和推廣白話文學的人物,不但全篇文言,而且一個新式標點符號也沒有,擺明了就是來「踢館」的。而劉半農則在同期中發表「答王敬軒君」的文章,把那個虛擬的王敬軒給罵回去。 醞釀了一個月之後,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立即以其清晰說理的形象,反襯出「王敬軒」的守舊昏庸,時機真是好到不能再好。錢玄同玩上了癮,乾脆一人分飾三角,先化名「崇拜王敬軒先生者」,回罵劉半農,再創造一個「戴主一」來反串「公正第三者」,最後再用自己的名字寫了一個「跋」去支持白話文學,一時把這個議題吵得沸沸揚揚。中國人本來就愛看熱鬧,尤其青年學生看到舊派人物被罵得抬不起頭來,大為快意;而此時魯迅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恰在5月新青年發表,文字辛辣無比,更為白話文學添加柴火,古老的北京城像爆炸一樣,新青年洛陽紙貴,銷路被推高到一萬多份,一改往日蕭條的景象。 錢、劉以大學教授的身分,搞這種「炒作」的把戲,目的倒並不是要多賣幾本雜誌,而是希望藉由「罵戰」吸引文化界,來捧紅白話文學。錢玄同深知,罵一個虛擬的,沒人認識的「王敬軒」,效果還是不夠,一定要拿「大咖」出來當箭靶。錢的計畫非常縝密,在他第一次假扮反派的時候,就讓「王敬軒」把舊派人物林琴南、嚴復拉進來壯聲勢,然後在回罵的時候,也把林、嚴二人也拉進去「陪罵」,尤其說林琴南把外國小說翻譯成文言,不但扭曲原著,而且根本不通(註7)。罵得那麼狠,目的就是為了「引戰」。果不期然,「躺著中槍」的林琴南到了1919年2月再也忍耐不住了,在「新申報」發表短篇小說「荊生」,藉主人翁之口,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人罵得禽獸不如,甚至還意淫式的把他們打得屁滾尿流;這還不夠,林琴南同時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老友北大校長蔡元培,直接送報館發表,大反白話文,儼然一副「告御狀」的高傲態度(註8)。沒想到這麼一來,反而助長了新青年教授們「被迫害」的形象,錢、劉二人的「詭計」終於得逞,「白話文學」不但成了最時髦的新名詞,也立時成為文學主流(註9)。 [註1]:白話文學運動的「文獻」很多,如果認真研究起來,胡適後來的「建設的革命文學論」寫得更深入更好;但是思想是漸進的,就如同胡適早在1914年就已經考慮到如何改良中國文字的教授等等議題,逐漸演變成所謂的「文學革命」;但「文學改良芻議」首倡「八不」,是胡適初試啼聲,第一篇把文學革命本質清楚明白敘述出來的文章,爾後白話文學的理論均脫胎於此,因此稱作第一並不為過,而胡適亦因此篇文章而名聲大噪。 [註2]:相較於胡適的溫和個性,陳獨秀顯得衝動。對於白話文成為文學主流的態度,胡適主張漸進,因為白話文需要鍛鍊,而傳統的文言文有助於白話文的滋長;但是陳獨秀比胡適更激進,認為白話文學就是正宗,不容任何討論餘地,甚至說要拉大砲去轟擊「舊文學的陣地」,因此胡適亦稱,陳獨秀才是白話文學的「急先鋒」;而史家郭廷以認為,胡、陳二人有如政治上的梁啟超與孫中山。 [註3]:我個人有一個還頗自豪的經驗。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閒談,發了一點議論,在座一個大陸朋友聽完驚嘆,說我短短兩三分鐘的講話裡,竟然用了七個成語!我連忙問,用成語有沒有讓你聽不懂?他說沒有,因為你用的成語都是很通俗,我們口頭常用的;不但聽得懂,而且聽得很舒服。我後來思考,大約是我愛寫東西,下筆時常常會考慮用字遣詞,琢磨如何用最好的辭彙來表達自己的意思。久而久之,我在說話的時候也會不自覺的像是在寫東西一樣。這並不是什麼「特異功能」,只要多讀多寫,就很容易「出口成章」。胡適一再強調,白話要成為文學,需要「鍛鍊」,而流傳下來的成語就是精練的產物之一。 [註4]:白話歷經百年的鍛鍊後,今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處處可見。我印象最深的是張曼娟有聲書,其語言之精緻,聲調之優美,幾無一個贅字,聽起來真是一種享受。讀者亦可以四處去尋求一些標語廣告,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註5]:這些個註解寫於1917年11月「答錢玄同書」,說得極好。這讓我想起31年前我初寫胡適的時候,有一位日後成為「打假專家」的大陸留學生,非常鄙夷胡適,說胡適沒有深度,「寫得清楚明白誰都行,有什麼了不起?」事實上,就算是白話,就有人可以把它搞到看不懂的地步。清楚明白是白話文的基本要求,確實不難,但還是很多人做不到。 [註6]:我想起中學國文老師講過一個例子:某人喪弟,為文時為了對仗,寫出「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這種句子,其實他根本沒有哥哥。 [註7]:林琴南不懂外語,他的翻譯是由懂外語的人口語翻出,他以古文寫出。這可能是古今中外最離奇的翻譯方式,林琴南以此法翻譯的外國小說多達十幾種語言,數十位作家,二百餘部作品,產量如此豐沛,係因林有捷才,下筆極快,人家把故事講完,他也寫完了,而且是優美的文言文。問題是這些翻譯文雖然優美,但(與原著相比)錯誤很多,有時甚至變成一篇新的小說。在翻譯的「信達雅」三原則中,大概只達到「雅」這個應該最難的標準。 [註8]:蔡元培雖然是革命黨,但是望重士林,連軍閥都很尊敬他。林琴南的公開信,也引來北洋政府的注意,想要干涉此事,此舉更營造出這些新派學者「不畏強權」的形象。他們本來就是青年領袖,這麼一來更成了被擁護的對象。我個人以為,陳獨秀、李大釗後來轉到政治界發展,與此事不無關係。 [註9]:林琴南寫小說罵人不免刻薄,但追根究底還是錢玄同等人玩得太過火了,惹惱了林琴南。在新文學運動的大師中,還是胡適最厚道,當時就覺得不該這麼惡搞;在爾後著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胡適稱讚林琴南運用古文的能力,比很多人運用白話的能力強得多,所以相當優美,也算很有成績,算是間接還他一個公道。1924年林琴南過世,錢玄同等人想到當年把無辜的「前輩」拉出來當沙包打,亦不免有些愧疚之感。
|
|
| ( 創作|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