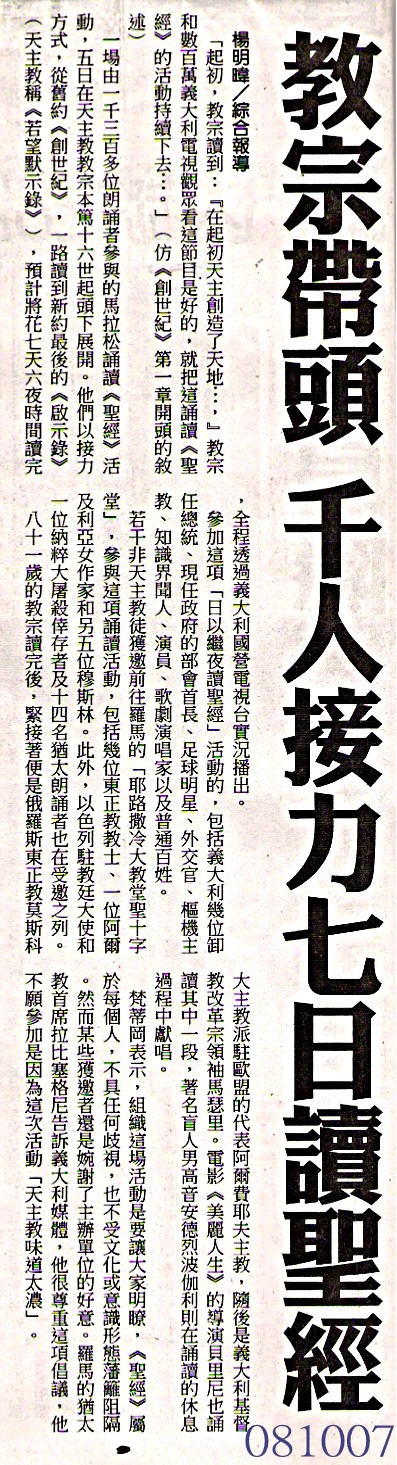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10/07 22:19:44瀏覽780|回應2|推薦33 | |
二個多月前在聯網遇到的一個故事,曾讓我聯及到李藍的《白夜》,一個幾乎快遺忘了的故事。而上一次聯及,似乎是十幾年前自己在對自己的自我做些心理回溯的時候。 故事只翻看過一次,是十六歲時從同伴的手中轉來的,印象很是模糊了,從最近在網上找到的資料裡,是民國五十七年出版的,當時我才七歲,相信應該是同伴家中父母或者兄姐們的舊書。 當然,現在要找似乎只有在圖書館了。 故事敘述的是一個苦讀出身,好不容易得到份可糊口的公職的青年,與他的父母關係及影響之間。 青年的父親在大陸時,原是個帶有些養尊處優、帶有跋扈的大地主,逃難時除了將他們母子帶出來外,也將他一個外頭的年輕女人帶了出來,不太記得他財富是在逃難過程中流失或者什麼因由消失了,後來落的只能在巷子口賣茶葉蛋維生,只能活在緬懷過去的失落之中,故事的開頭似乎就是從青年必須從其父親之請,給他父親及這個也有弟妹的家庭送錢,然後鋪展出青年父親在大陸上的生活、個性,及他的母親知道他父親另有外室後的種種,解析出青年分裂開的父親影響與母親影響世界的。 故事裡青年主要由母親勤苦教養成人。當然的,在記憶中的感覺上,作者似乎對青年父親那樣的發展,應該也有許多關於本性及歷史轉變的同情,但青年無法接受那種狀況的母親,似乎在教養兒子的過程中也有離開人群的封閉,而當青年稍可自立後,一些病癥卻也因此而出現,在經常一個人的狀況下,鄉愁加上壓抑,口中經常發出些忘了現在、季節不分的懷鄉囈語,而青年也在不懂如何是好下,就應著她的囈語予以回應,映像很模糊了,似乎是些雪啊、樹啊、牲口及下人的。 而故事結束在青年的母親亡故後,青年也因此打擊而被送進了精神醫院,而作者似乎也描述著他跟探視他的人提起他甚至不願意那種醫院中放風的自由,能與其他人接觸的自由,寧可一個人在一個小柵欄中過著種沒有人打攪的自由的。 當然的,十幾年前想起這個故事時,就曾稍檢討起當時有沒有能力看懂這個故事的,以及自己有沒有些陰鬱是在是在無法釐辨作者的更深一層表達中形成的。 那是剛考過高中聯考的那年,是屬於我改變了通勤時間後,新接觸到的些年長同伴間傳來的,當然,當時學校是連武俠小說都禁,這類書籍就算不屬禁,應該也不在鼓勵範圍的。 當時家中雖然也訂報紙了,不過當時打開報紙仍只是為了寫週記,真正印象中有過的,似乎還只有沒看全連載的《蛹之生》,及家姐大概是因為上課需要,大一暑假帶回家的王禎和小說集,這個故事算是進入過我腦海的第一個當代長篇吧! 當然的,我自己是在三十歲以後無意中翻開過《文心雕龍》,才對「位體、置詞、通變、奇正、示義、宮商」有些俱文觀念的,而之前在一些囫圇吞棗的心理分析,雖然有檢討過自己關於「故事」的意義的認識,但那時對於「然」、「所以然」的更源頭認識的並不夠,對更多腦海痕跡外的「所以然然」漂浮更多,甚至對於悲劇之外還有很多深藏的「宿命」而不自覺,以致在那之前對於自己帶有些意氣及記憶曾寫下的,常有的不足及不倫之感,那時才開始較清晰了些。 至於之後呢?那不只產生過對於文字的一種畏懼,對於那十二個字,至今有的仍不只是慚愧! 當然的,最初悲劇的形成,不知道是一種事實,還是為了避免悲劇。當然的,創世紀裡第一個悲劇中的「分別善惡」應該是既有樹也有果的(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只是在以自己腦海的形成中以往有關於「禁果」的突顯而不自覺,以致順著翻譯文字而沒有看到那棵樹的,因此「吃果子拜樹頭」曾讓我懷疑那是不是一種忘了天地的地痞說,因此傳統的禮儀冠蓋之邦也讓我觀星望斗過的懷疑過那會不會是傳承或翻譯有誤,以致歧路中至今仍有許多更待洗鍊的。 當然的,直語傷人,委蜿又傷腦筋,而樂園又究竟是種化境還是種悟境,我就經常仍因人、因地及因心情而模糊了! 拿最近來說,最近見到一種說法,說是佛陀只有殊聖心而不懂情色,因此難免想及觀世音佛祖「如幻聞薰聞修」的「如幻」與「聞薰」,想到了佛陀那種自幼有八個人為他洗澡、八個人為他更衣那種優渥中尚還能夠有的殊聖心,以及路加福音中關於耶穌最後吶喊中的「胎」與「乳」的語句轇轕(註),因此感覺又有點頭大,也許就不去想它能較為我淨吧! 註: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耶路撒冷的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因為日子將到,那時,人要說:那荒胎的,那沒有生產過的胎,和沒有哺養過的乳,是有福的。那時,人要開始對高山說:倒在我身上吧!對丘陵說:蓋起我們來吧,如果對於青綠的樹木,他們還這麼做,對於枯槁的樹木,又將怎樣呢!
|
|
| ( 心情隨筆|心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