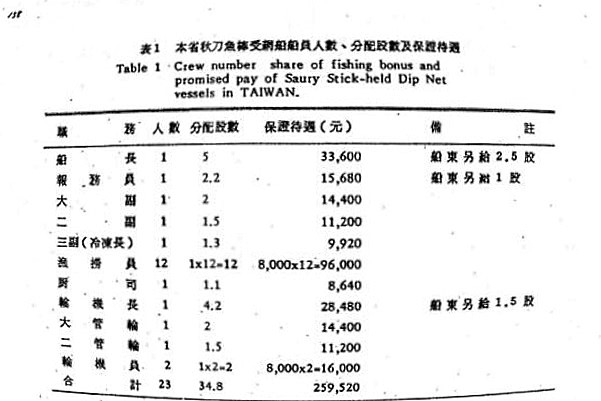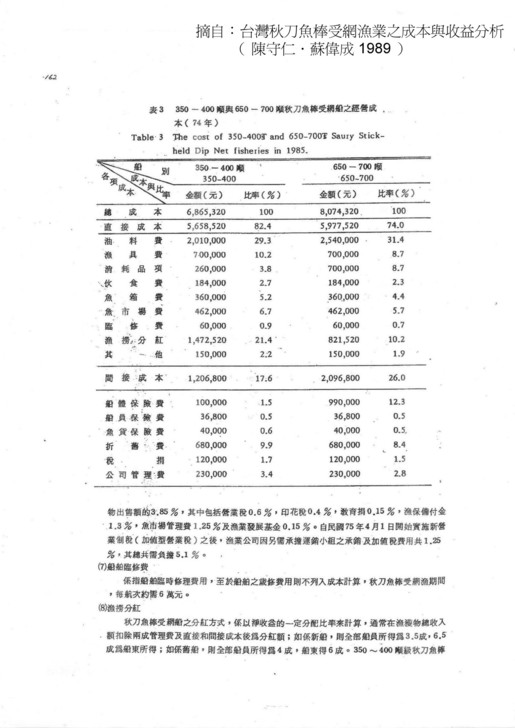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7/04 18:17:07瀏覽238|回應0|推薦1 | |
船長那年三十八歲,是從十幾歲就開始上船工作的,據說他的兄弟們全都在海上生活,在南太平洋的漁區裡,我還見過同一艘船上他也在做船長的大哥跟當二車的弟弟,但由於沒有了解到他上一代的狀況,不過我想即使稱不上出自漁業世家,資深的討海人那是絕對稱的上的。 「 做事情巴結點啊! 」 「 大家拼一點啊,出來就是要賺錢的! 」 「 累?這樣就在喊累?你就還不曾碰到過澎湖船長呢! 」 船長在工作外的時候不太說話的,因此到現在除了他的三字經外,讓我能記憶深刻的,就是他工作時常掛在嘴邊的這幾句話吧。當然的,船長的三字經大部分都出現在工作的時候,在一般的生活上倒罕的聞及,那裡面除了能略窺他以前的工作環境養成外,或多或少也包含些工作壓力在裡面吧! 「 第一次出來抓『善肉』( さんま , 秋刀魚 ),有這種成績,也不輸給那些前輩,回去公司也交代會過,…… 」 這是在秋刀魚漁季快結束前公司另一艘同型船隻船長傳來的話,當時我無意中看見船長那種面帶深刻鬱結的表情。我想他當時的心情一定不怎麼好過。 當然的,漁獲量一定會是漁業公司衡量一個漁船船長盡責與否的標準,不過以我當時未能全然設身處地的想法,那個既曾讓一個船員在作業時受了重傷,在轉載時又走了六名船員的漁獲量,甚至包括船長能有機會接手這艘船,也都是因為前任的船長沒處理好船員集體怠工提早返航而被辭退,有太多那樣的心情實在也沒有多大的必要。 「 什麼愛的教育,我看教出來的也是差不多的啦! 」 「 我們以前哪是這樣!做到眼珠子都要蹦出來,也是做,就想說別人能受的住,我們也就受的住! 」 「 現在的這些喔,連體力都不行,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喔,唉! 」 類似上列的幾句感觸,似乎一段時間一段時間的都可以從船長們的無線電對話中聽到。當然的,一個人能做到漁船的船長,他本身一定已有其相當的特質,如果他要把別人當成自己來看的話,這些感觸或也都有它某種程度的真實,在此之前自己也有過短暫在工廠中帶人工作的經驗,因此當時也頗有同情的,而且我有點在想船長們或許都是長時期的在海上過著種忙碌、隔絕的生活的,社會的底潮有時候也不是他們有時間去了解的,包括當時剛退役不久,一個甚至不是在外島、還能兩份報紙輪定的兵役期下來的我,對那時剛進入的臺灣社會似乎都還覺得有點陌生呢! 「……」 其實船長也遇到過一次幾近眾叛的情形的,那時候他的表情真的也算夠「 怨嘆 」的了,不過當時我不曉得是否也無意中也有點成為眾叛裡的一份子,他的難過我不太敢去正視,因此比較能察覺的也只是他那幾天都沒有罵人、甚至發起工作的命令都顯的蒼老而無力。 一般說來,在船長給我的感覺裡,我向來還覺得他處理事情頗果斷、也頗精明的,因此當有人向他提出要離船的第二天,當他要大副向大家宣佈只要是能提出理由的他會考慮時,直覺裡的不太可能,甚至讓我懷疑起他這個動作背後的方向性,不過後來證明這種懷疑可能是錯誤的。 當然,船長或許也沒料想到有這麼多人會提出吧,船員裡除了跟過他的阿成外,包括幹部裡的大副、二副都寫了上去,因此之後他有好多天沒有動作,甚至那幾天有他沒有離開過駕駛艙跟寢室的感覺,那直到他要報務員發放一些他過去只有在漁穫特佳時犒賞的、還是犒賞時加倍的、他的私人飲料後,才再看到他低著頭、不是很愉快的出來巡視時,也許我當時還沒有那麼不堪到想離開、只是尷尬在大副拿著筆紙在眼前、只是情況好像也有點像大副說的「跟他一起、不好做事」!只是又再煩了大副又再說的「大家都寫了喔」!在旁邊等著沒離開的意思,對船長的一些歉意真的也是有的。 「…………」 同樣的,那更是個更發不出聲音的難過吧。船長最難過的時候我並沒有發覺,還是報務員告訴我我才知道的。討海人的心情跟難處,或許真的也不是當時的我能完全體會的,關於這一點我也向報務員承認過。那次報務員說起了長期在海上的那種寂寞,坦白說,向來接受的教育裡還是沒有太多男人能訴苦的部份的,因此聽到時我只說了「那可能還不是我能體會的!」、「海上景色、事務對我而言還不時的有新鮮的感知!」的話。 那次知道船長的母親過世,是在船隻結束北太平洋的作業之後。那天本來只是大副找我喝酒,剛開始我也並未察覺大副有何不同,喝著間大副告訴我他母親過世的事情,然後我也只是陪著他把半瓶酒喝完,大副那時不說話,我也不曉得該說什麼,甚至輕問了句,知道大副的母親是出港前就生著病,都覺得問的好多餘,接著我突然間好想再喝酒,剛好報務員下來時也就向他提了,他問我為什麼,知道後,他才告訴我船長也遭遇同樣的情況,他說船長已經有一個多禮拜關在房間裡幾乎都不說一句話了。 船長在船上是如何調整心緒的,坦白說我不太明白。不過我相信他是個忍耐度頗強的人,當然的,在猜測裡那包括他可能接受過澎湖船長的不少訓練。在那船長們聯絡用的無線電頻道裡,我們經常都可以聽到有些船長會在上頭又吼又唱的,而那種從外頭傳來的聲音、在那種隔絕的環境中,包括只是聽的我們,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慰藉的作用,雖然有時那是在工作中、在面對不太安全的器械、或不小的風浪、兼船長分心下控制不好的麥克風而顯的刺耳下。不過我們的船長似乎比較不是屬於這種性格的,在SSB上他會主動找其他船長說話,也僅於工作上的事,甚至在別的船長找他聊天時,他也只是簡短答應聽的多,當然的,他此時會比平常面對我們有稍愉悅點的表情,應該也是正常的,不過因此他稍內斂的性格不太能夠讓他的船員見到他的一些性情,或許也有他的道理吧,那直到一次透過一課的小學課文,我才稍稍的見到了點他嚴肅以外的情況。 「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天這麼黑,風這麼大……」 那次是出港約三個月後,一次避風浪的夜航吧,當時我跟 大元 在駕駛室內值班。是在晚飯後不久吧,船長吃過飯後在房間裡坐過了下,出來一坐在窗邊,就不斷的複念著這些小學國語課裡的課文,而當時我雖然也同樣不曉得有後面的一些情形,不過個性上比起 大元 還是老氣了些,因此當 大元 暗笑起來拉我的衣物指著船長時,我也只是給了他苦苦的一笑,但 大元 似乎就忍不住了,看向船長時竟笑出了聲音來。當然的,就後面的一些情形看來,船長這時是興奮的、愉快的,喜歡 大元 這種聲音的,不過他當時還是看過來的沉了一眼,還帶著點逗 大元 笑的、更大聲的念著,然後越念笑容越大,後來咯咯的笑聲,就取代了那些默書的聲音了,而當 大元 更笑彎了腰的時候,我那自己看不到的笑容,想來大概也頗燦爛的。 「 .ㄅㄚㄅˊㄚ: 你又有好久沒有回家了,你現在在船上好嗎?媽媽說你在船上很辛苦的工作, 要我們寫一封信給你,但是我不知道要寫什麼,這次考試大姊得了第一名,我有一 題數學寫錯了,只拿第三名,……… 」 這就是後來的情形。當然的,這段書信裡的文字,到現在的回憶裡我似乎都還認為那是讓我那次愉快的認識船長的所在。不過那還不是接下去的情況,或許吧,要將這種快樂與我們這種下屬分享,船長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吧,當然,也更或許就是他那種赧怩讓我這段記憶更深刻的。 那時候他笑容笑久了,似乎也覺得有些無趣,伸了個懶腰、喊了句「 無聊嘎! 」後,抓了抓頭就點起菸來了,臉孔頓時間似乎又回到了船長的模樣,不過那種似乎屬於按奈不住的的欣悅,似乎在他的抽菸時的煩躁裡還是表現出來的,這時海岸電臺頻道裡正播著的陸上通話表的女聲,似乎就成了他的新大陸了,他睨了我們一眼,然後捉狎了句「 我來捉弄她一下! 」就跳下座位走向話機了。 不過台北海岸臺的小姐,跟我們一樣不可能知道他這時暗藏的心情的。或是吧,忙碌於值勤中的她們會比我們還更沒有時間吧,因此在船長持續了段怪聲怪調的呼叫,引來了忙碌中的小姐還算有修養的罵聲後,他更調皮的改以故作正經的語氣說是要掛號時的模樣,及之後他以無辜的作假聲音說他不知道這時候不能掛號的語勢,以及臨結尾時還忍不住爆出笑聲匆匆放下話機的姿態,甚至掛上話機後還要再品頭論足一番的,說這個小姐一點都不懂幽默的表情,也實在有夠誇張的了,至少是至今在現實裡我都還沒有再遇到過的,而且後來要不是我的問話有點食古不化兼煞風景的話,可能還有更多會是我料想之外的呢! 「 我這第二個女兒可愛(古椎)喔!這個最能貼我的心了,你看!她還特別的故意用注音符號,又還怕我沒看到欸,還能知道要圖的那麼大讓我注意欸! 」 之後船長就興奮的說要拿信給我們看了。在等他從房間出來的時候,我才對他那天的不一樣稍稍有點原來如此的感覺。當時個性有點枯燥的我,坦白說不太欣賞他對海岸台小姐的那種幽默,然而就在疑惑著會是什麼信讓他如此時,他已經開著顏拿來兩張信紙了,而且他那種迫不及待的興奮好強烈、好強烈,似乎是我信紙還未拿妥,船長就怕我們沒有注意到似的、迫不及待的就指了注音符號裡特別塗注的大大的上聲告訴我們上述的那段話,而當時在強烈的感染著他歡悅的容顏與開懷的言辭的同時,羨慕之餘,我連他大女兒寫了些什麼似乎都沒有映像,當然的,那可能又是當看著時他又急著告訴我們在同一封信上他那學齡前的兒子在信末已能寫上的名字的興奮吧!當然的,那可能也是報務員這時聽到笑語也出了來,船長在聽見我喚報務員「 報仔 」時,還更反璞歸真的說了我上船這麼久了還這麼「 生份 」,問我何不稱呼他那我聽都未曾聽過的「 二齒 」時的表情,跟他平常嚴肅的面孔比起來也太輕浮了吧! 「 自己就在歹命囉,還讓他跟我在歹命,沒在傻說! 」 「 女兒要學鋼琴,兒子要學心算,在山頂(岸上)賺那三百、五百的嗎? 」 這是後來船長對我發出的兩個問題的回答。當然的,對於這船長說這兩句話時一時面色變化究竟的不解,及他讓當時的我真的有點達到難堪的狀況,這是我至今都仍有些耿耿於懷的。當然的,在前面時我好像就用過了煞風景及食古不化的字眼,不過在檢討之餘坦白說我仍認為自己實在是有點冤枉的。 或許缺少那種身為人父的感受吧,當當時的笑語聲漸漸走向下坡時,在羨慕之中,隨著他兒子的話題,我想我也只是輕鬆的問了句「 船長!那以後你會讓你兒子上船嗎? 」然而卻不曉得為什麼這樣的問題,會讓他的心情起了這麼大的變化,更或許那是在一種近距離下的特寫效果吧,當他在說「 自己歹命 」時那種似乎是憤怒中帶著鄙惡的情表,就讓我的笑容頓時僵住的尬在那裡了。 當然的,樂於工作,融工作於生活,我想這是我在自由教育中稍灌輸過的、也是尋找中的某種理想吧!因此我在船長高興之餘,希望得到的應該是另一種答案吧。在下船後的回顧裡,我怎麼都覺得我當時是興奮的在問一個快樂的船長,只或許年紀少他一個地支的我,或許是拜社會經濟的稍豐裕之賜,稍稍的能有些所謂的生涯規劃的概念在萌芽吧,二個多月的海洋生活下來,也已經有些適應後的快樂,稍早前我也有點認為是該拋開一些《 港都夜雨 》歌詞裡的「 青春男女,不知自己,要往那裡去 」,來看這片海的時候了,該正視一下漁業生活的漁業吧,或許吧,也正是這些剛開始寧取樂觀的烏托邦,讓潛意識裡所希祈的答案跟船長的出口有太大的差距吧! 後來的第二個問題就更是尬在那裡太久後不得不發出的了。當然的,或許那時候的我真的很不識趣,那時我在有點不得不堆出笑臉的又問了:「 船長!那你就認為上船歹命,怎麼又還能夠有辦法在這裡做,還能夠做到船長! 」當然的,因此在又得到的答案裡,包括他那像鄙夷我對金錢天真的語氣,我的笑容就再也堆不出來了,也就只好抓了抓頭避開幾步閃在一旁了。 當然的,其實在剛開始上船聽到船長用「 山頂 」這兩個字表達陸上的時候,說真的自己也有些不能太能夠習慣,也許吧!剛離開陸上不久,聽到以那種詞語表達的我,會有點聯想到自己是否是尚未進化的山頂洞人,不過後來聽大車、大副在不同的語氣下也都這樣使用,才再想那或許是他們長久使用的習慣語大了些。 「一個運氣好的船長出來一趟,分個七、八百萬的也不是沒有的事!」 當然的,一個船長在船上到底能夠賺多少,當時我是一直不懂得問的,這又是過了好久後、在快要返回臺灣前報務員無意中說出來的。當然的,當報務員在說的時候,我似乎也不懂得去問那得多好的運氣、或者他所謂的一趟是半年還是三年的、或是那是擁有自屬船隻的船長,而七、八百萬到底是多大的數字我想我也並不太有概念,倒是上船前在那短暫待過的親戚工廠裡,看過好多他們為了近千萬的債務爭吵的情形,那是種自己即使有心也無能為力的情形。 其實當時對於船長所說的「 三百五百 」,我也並非完全沒有概念的。當在看到徵募船員的分類廣告時,對於裡面所提到的高薪,我無法否認也是打動我的原因,不過我當時認為那是在海洋工作危險的代價,我有點想朝那個代價換幾年的學費,但是那種想法好像在下高雄不久就清楚了,清楚以一個沒有經驗的生手,那是不可能的,清楚如果漁獲不好拿的還是當時勞動基準的九千多,包括後來領的一萬三千二,還是報務員在途中才宣布的,說是由一些漁業團體奔走而來的。因此決定上船的時候我也決定把收入輕鬆點看待,反正有過當兵領餉的經驗,再加上一些對經濟學課文裡那種「相對於人類的無窮慾望,資源勿寧是稀少」的解慰,關於這方面我還算相當的看的破,甚至在還沒下網前見到一次霧海中別國船隻在下網的詩情畫意景象時,天真的我還告訴一旁比我還興奮的船員還說過「 看的到這些,不管賺多賺少都也都值得了! 」的話,不過這句話的效果或許還是只能偶而拿出來當心理建設吧,有時候在實在太過疲累的工作狀態中,甚或當有老船員笑笑的在用「 別人的兒子死不了你不知道喔! 」回答那些回沒有服過兵役的船員的怨詞時,或是自己用磨練去看船長的一些不合理的舉措後仍無法釋懷時,在「恤民如子」的前識下,難免的還是會想到他行事舉措的背後,又有哪些是屬於鋼琴跟心算的。 「陸軍○○旅○○團○○連○○兵○○○。」 「長女○○○。」 「次女○○○。」 「長男○○○。」 船長的字寫起來跟端端正正差的不遠,頗好看的,型態上一些勾、劃的末端稍稍帶著點飛舞跟延長的意思吧。其實船長寫下的字我看過不多,大概他也很少寫字吧,認真說來船長寫過的字讓我起過注意的也只有一張寫在厚紙板上的秋刀魚起落網的工作分配圖,及一本船長當計算紙使用的筆記本上的一頁。 前者當然分配後就看不到了,不過在宣布前他跟我說了點他分配的理路,當時反正也只有服從,倒是下船後才想過可能的不同造成的不同,對船長在短時間識人的果斷,還是有點佩服的。而筆記本上的那一頁我就比較有機會返覆的去觀察了。 那一頁上船長是使用橫行直寫的方式寫下的,那些勾啊劃的如果不去計算的話每個字大概有接近兩行的大小吧。最右首他寫下的是一個陸軍部隊的詳細番號跟文書兵的職稱,下頭還有他的名字,其他的就是些不規則棋佈的、重複的、冠上長男長女次女排行的子女姓名。當然的,當時我能注意到的只有這些,甚至這些多少是在反射到心理學投射測驗裡的羅夏克墨漬或主題統覺測驗時囫圇吞棗去衍想過的,因此船長在船上的領導統御模式跟動機,或許在我看到那些信之前就已經經過自己的誤導也說不定,當然的,在一切為反共的教育模式下,接受、抗拒的兩極魯男子樣態,在接觸心理學時分析的部份會讓我有點心機的感覺,當時也並不願意深入去想的,甚至也多少知道這些必須帶著些前題的東西的偏誤程度,並不想只從某個角度去透視船長的。但是我好像曾想藉這些字來告訴一個先前曾提到過的、叫 大元 的船員,在看待事物時別偏重耳濡目染的俗觀,不過當想分析之前我卻也怯步了,畢盡那是太多猜測性質的東西,而且在給他一些不便舉例、含含糊糊方向性的東西後, 大元 太快的反應也確實讓我尬笑不已的,那時候我好像是覺得他吸收了不少幹部的暴力傾向,想從階級、次序來點出他一個人處在某一個角色的人格特質吧,別套用他自己看的見的就加諸在別人身上反而失去更理想的狀況,因此我就先用了測驗的語氣,問他對這頁文字能想到什麼再來找方向,結果他竟然在沈思下後說了「 我看懂了,船長的字比你漂亮! 」的話,當然的,從國中後交作業大概都用趕的,從小習得的又是大姊像報紙鉛字大小的字體,又缺少大姊書法的根基,這點我是不得不笑著承認的。 「 會害怕嗎? 」 「……」 「 別說你害怕,這次我也怕的很。唉,那時候若不是想說就已經轉載一半了,要再安排時間麻煩,較早點避可能就沒那麼危險了! 」 船長一職應該是兼技術與管理的,剛開始由於沒有其他的方向性,我也只能從一些老船員說的、會將不聽話的船員綁在木頭上丟下海拖到他快沒氣才拉起來的船長來對照,或是三副說的那種「 別嫌了啦,我還不曾看到過船長會到冷凍室來巡來看的,更別說魚多的時候還會下來跟我們一起排魚! 」來增加對他的好感,他那很傳統的恩威並施方式,在那幾乎是公開的船長通話中也多少能體會的到。當然的,那個時候船員荒或許還沒有目前嚴重,不過船長對於船員的選擇大概也沒能有多少的彈性,再加上或許對秋刀魚燈誘法方式的撈補船長缺乏經驗吧,而且很多的問題似乎是在船長跟公司臨出港前才給他的、一個有過一次捕秋刀魚經驗的二副開始的。 那些包括剛開始船長、大副跟二副在工作討論上的不愉快,似乎也都攤在我們船員面前,包括當二副說船長將船當拖網船在開、沒讓聚魚燈發揮他應有的效用、不小心被他聽到後,他不曉得是話沒聽全還是故意的,將船定住又等不到魚聚來後對二副的尖酸用語,坦白說都產生過問號的,不過這些基於二副的其他性格,及對某些專業不甚了解的服從本質,對船長也需要練習的同情,是也蓋過二副在經驗上發出的氣燄的,不過那在秋刀魚漁季結束前的那場讓船隻折損嚴重的風暴裡,也許遭遇到生命交關的際象吧,在大副、大車搖頭下的「 早就該走了說! 」聲中,對他解釋的是因為不想浪費時間在中斷轉載後再尋找一次轉載時間而沒有提早走避上,就多有懷疑了,雖然事後他指著氣象圖在無奈、不得以的語氣中告訴我們是怎麼走出那場風暴時仍可看出他的勇敢,不過對那次船隻的折損及險象環生,對他的判斷考量還是出現過畏懼的。 「 這樣就說睡眠不夠,那到了『放酃啊』( 流刺網 )時要怎麼辦,要是遇到『酥料( 網遭海浪纏旋 )』睡你都沒的睡喔! 」 這是剛離開高雄幾天船長在問過我習不習慣時、對我所提出的些像日出而作日落後又得值二至四個小時航行班、以及船朝東北行走每天黑夜減少的恐嚇,而說是恐嚇,大概是遇上的幾次他還是有讓我們睡點覺吧!而且到了鮪魚的魚季,雖然靠港時對他處理二副跟報務員間酒後的衝突而要二副及一個船員離開的作法,在剛開始時我就有他處理的不盡合情理的感覺,不過既然出港了還是願意樂觀的去相信這是他熟悉的作業,盼望一次滿載而歸吧,不過似乎有些問題是出在這艘不純為流刺網設計的雙拖網漁船的,最後我好像所能滿載的也只是船長那淋漓盡致的脾氣。 「 人家十五個人起個五百件網,一大早十點前就起好了,我們十八個人,每次起到下午二、三點還在起,那是要跟人抓什麼? 」 當然的,關於船長這類憤忿喪氣的怨詞,礙於船長的威嚴,及生手最好還是有耳沒嘴的觀念,也不好向船長說什麼,倒是有一次在談話中跟報務員交換的些意見裡,或多或少的曾吐露過不同位置的我們所產生的些不同看法吧: 「你們抓出這種成績,網又起的這麼慢,吱……」 「怎麼好像抓不好全是我們的責任的樣子?下下去的網我們也都起上來了,漁獲不好好像應該是船長判定下網位置比較有關係吧!哪裡魚多魚少,好像也不是我們所能夠決定!」 「怎麼會沒有關係!你們網起的慢,船長就沒有時間走船,想到也到不了,這裡可不只有我們一艘船的,有些地方還得排位子,慢了就排不到好位置了!」 「嗯,這些我真的是沒想到,呵……,不過為什麼會起的慢你應該也想到過吧!」 「你們那何只是慢而已,而是我沒有見過那麼慢的。別人的船十四個人起五百件,早上十點多就起好了,我們十八個人起七百件,每次都起到中午都還在起,人性嘛,船長看不到下面,下面就在摸囉,我下去看過,很簡單嘛,為什麼大車去的時候一槽三個小時就起的起來?」 「喔!你這樣認為嘛?我不太曉得喔。你那種比較是我不了解的,那大車去的時候也起過四、五個小時的你怎麼不說,你不能老以一次最好的情況去做比較對不對?海裡面有各種不同的狀況,十四個人、十八個人,那是另外的問題,一樣就那一套機器,規模不經濟呢?更何況還有體力透支的惡性循環,是不是?」 「是嘛?」 「大車去幫忙是可以鼓動一下士氣,但是這是長期性的,不是加個三、五天班就結束的,即使不是很粗重,每天也都至少十五、六個小時以上欸!」 「不……,我還是不這樣認為,會時間長也是你們自己造成的,我看過他們拉網的樣子,愛拉不拉的!」 「喔?不曉得該怎麼講,我自己在前面沒有幾天。也許是我在裡面感覺跟你不一樣。下面也有大副他們對不對?他們會因為做事做到都打起來了,也不是不想做快!嗯,你剛才也講了船長看不到下面,那才是個大問題,船長就想趕,不曉得網積了多少,等處理掉又趕,又積,狀況怎樣他不曉得,然後就生氣,就罵,越罵下面越不敢回報他,狀況就只好一直這樣循環著。隨便罵,罵的連自己的威信都沒有了,而且這樣趕網破壞的狀況很嚴重的!」 「你說的這種情形當然也有,不過還是你們新手太多了,網會積也是他們拆魚拆的慢才會積到吧!」 「也不全然吧!好,你也知道新手多,那你有沒有給點時間讓他們學,更何況拆魚需要些判斷力,判斷力教過後還得磨一段時間才有的。才要開始磨你上面就用罵、下面就用打,然後就拿笨啊、不用心那種角度看,那永遠都是那樣不是?就算我相信你們比我們聰明,學起來比我們快,剛開始再短也要一段時間吧!更何況控制權在你們手上,船員狀況怎樣你自己曉得,沒時間走船你們要衡量啊,網下的多也不表示魚穫就一定多,是下網的地點重要呢?還是網的數量重要呢?你們都可以斟酌的啊!」 「我還是不這樣認為!齁!已經抓這麼少了,網再少下那還得了,別說船長不答應,公司也不會答應,連我都不能夠同意!」 「我也不是要建議你們少下,你好像並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說,……,呵,怎麼講,我應該是想說凡事不要只從一個角度去認定,範圍是可以加大擴充的,你也別那麼激動,這樣很容易像是階級對立的感覺。算了,這也不是我能多說的,上去了!」 「你大概不知道船長曾要公司托人帶一套錄影設備出來喔,你知不知道公司怎麼說?」 「怎麼說?」 「公司說沒有用,以前也有船長帶出來過,不過很快就壞了,有很大的跡象顯示是被故意破壞的!」 「喔?」 當然的,關於人類在時間內體力與能力的開發與極限,當時自己沒有多一點的認識,甚至在關於脾氣的壓抑與爆發間,相較於某些船長口中的「 我那些海牛! 」裡,自己有沒有對自己相同角色的同情也不甚知曉。當然的,船長也並非完全的不開明,也見過他趁大副在開船的時間下來尋找過原因,甚至有一次在我不太情願的、又承我當時的直屬老船員到前頭溝通時,我那種以「 拜託喔! 」開始、原以為又是廚師急了在亂按的怨詞後,廚師指向船長時,見著他想以一種速度來帶領、卻更理不出那些纏結的網堆時,想到他是如何急躁到電鈴按的讓人無從分辨時,甚至那次在一點脫口而出的莽言後,在想到自己騎虎難下中冒出的「 船長也一樣啊!我們是要將工作做好,那也不是發脾氣就能解決的了! 」時,也不曉得是愧對於船長還不知道結果的求好心切,反而有一陣子理直氣壯後的惶恐的,不過在某一種長期的思考裡,從船長與大副的控船的比較裡,船長時而快時而慢平均起來的時間並不比大副短的。當然的,據說起網的工作是屬於大副的,在那分成三「 槽 」(座)的網裡,曾經聽過船長在回答另一位船長「 那麼拼命是要做什麼,有幫他起一槽就不錯囉! 」時船長回答的「 沒辦法啊,我的大副就手腳遲頓,自己不多做些哪能夠! 」裡,船長的那種自發的強烈責任感也不是我在心裡所能抹滅的。 當然的,當時的思想是否比現在天真純正些,現在也頗值懷疑,不過當時離經濟、企管的教科書較近是一定的,而那些科目在稍認真點接觸時是在軍中吧,在幾乎是未經討論的學習中存在的大概只有理念吧,而將這些理念付諸在對軍隊非意志人性下,而且又是一個較邊緣散漫的團體,或是上船前親戚較浮濫經營以致失敗前的工廠中的觀察,我所能得到的體會也真稱的上是迷亂。其實船上真的曾稱得上出現怠工的行為,在我的認為裡那只出現在結束作業前的幾天吧,而且也僅止於少數一、二人。當然的,那是從我對那七、八個青少年的一般看法,而且在此之前我還聽過船長跟幾個船上的青少年說起了可以介紹他們到分紅(註)較高的公司,以及他那擁有一艘自己的船的將來願望。 當然的,其實分紅應該已經是行之多年的制度了,這裡所謂的高跟低大概是一些經費的估算以及帳目建立的問題吧,因此那對於船長的忠誠是該著眼於漁業或是公司,或多或少的都有些矛盾,甚至那產生了一個青少年問起我時我那種「 船長啊?船長心地不錯啊,是不是好船長我不知到,不過好人應當是不會有差錯! 」的看法了,當然的,在這句話裡頭有些是屬於希望這個有點「 有路無厝 」的青少年別太近利有耐心的學習,不過也算對船長較整體上的看法吧。 當然的,也不曉得是不是學理裡自己還是有個對規模的理想,尤其上船前還曾經剪下一份關於「一船公司」出事後浮出問題的報導,因此在返航的那二十幾天中,倒也想過一些如果依船長的個性、在船長也是船主下、在行事上是否能有較真切面對問題、對人事上凡事較長遠計,而較能有穩定的人事上的不解。當然的,有些的不解是來自大車也搖頭過的、關於普遍船公司對船隻成本過高的估算,及海上風險的無從估計的。當然的,關於一個時代的顯學如何受政局的左右也是無法估計的,在關於「人」的討論裡,從船長們的口中似乎只聽到較多無奈的感嘆,「人」在自由下的不確定性,船長們或許也有他們的無力感吧,一個短暫感染過軍事上終極管理作為的人,若沒有耐心再細從那些人性反向的因再出發,觀念要在海上那種競爭環境再去改變,大概也不容易吧! 「 別人能下的,我們也能下! 」 這是船長在南太平洋一次風暴邊緣所下的決定。那時看著他皺著眉站在船邊似乎在對判斷上也有不小的疑慮,不過也不曉得是他早上原本決定不下網的宣告心情上已有休息中的鬆懈,還是那次兩個多月不曾有過休息對休息有太多的渴望,雖然對報務員曾說的公司願將一艘四、五千萬的船隻交給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寧願去相信船長,不過在他的語氣裡似乎勇氣與跟進好像還是大過他對自己船隻的判斷,因此在笑笑的執行他要我叫起大家的指令時,會多有疑慮那也就很正常了。 當然的,在產值裡魚撈單位在政府機構中是不是算冷衙門,還是海上的一個比較屬於無政府狀態,在相較於報務員所說當前在學校受過漁業教育的這一代,在上過一次漁船後大部分都考慮轉業後,雖然也不曉得那是相對經濟環境比較上的多、還是社會價值已經折損了已經不是能夠封閉的漁村原有的社會規範的多、還是讀書所產生的智慧會缺少勇氣毅力的多,就真的就不容易去了解了,而且雖然說大車還曾說船上永遠只會缺船員不會缺船長,不過對於傳統漁業與現代漁業間青黃不接的現象,還是希望有關單位對未來能早做規劃吧! 當然的,附帶一提的是,或許有過那段在海上的生活吧,下船後對於一些海上喋血新聞中的兩造,總覺得有太多的遺憾與不值,當然的,雖然不太願意相信在臺灣還有我在下船後才看到的傑克.倫敦在《海狼》筆下拉森式的那種船長,所幸我曾經遇到的也不是,不過好像還是多少存在有,當然的,雖然凡事真的不太願意以「 出來就是要賺錢的!」 的方向去解決問題,甚至我也相信包括我所遇到的船長及更多的船長,不管他們自己知不知道,他們都也絕非只是為這個目的而在海上,因此在遇到一些吃不起這口飯者,或者有其他因由一段時間後不願再吃這口艱苦飯的成員時,在循循善導仍不能時,就送他下船吧,不要太以侮辱性的言詞及暴力對待吧,尤其在這大量啟用大陸漁工及外籍漁工的又加上種種文化價值觀的現在。當然的,這或也得更請漁業公司多給些船長體諒吧,在這是個朝自由化發展的社會裡,不是能夠有太多能夠任人鞭策的「海牛」的時代了,漁業單位也該多指導他們充實這方面的智能,或建請漁業學校讓將來的船長們好多些領導才識吧! 當然的,還得說的是,末尾所說的只是透過對於一個近達十年前所遇到的一個船長的感觸而出發的,在措辭用字間亦深覺有種以偏概全的惶恐,寧仍相信在世界各海域上的臺灣漁船船長們都是深明大義、處事謹慎的,在此除了以一種寄語海疆平和的心情外,更多的或許仍是寄盼船長您們長年在海上曾有的勞心與勞力能免於一旦無名與無情的吞噬吧! 當然的,希望別嫌我囉唆,再附帶一提的是,在返航的途中船長最曾針對的就是他回去要建議公司將那層甲板挖去的事提出他的看法。當然的,在這件事上當時的我也只僅只於想到就算結構安全或許可以克服變通、但公司也未必接受他雙拖網漁船只為流刺網單一作業所作的改造,而且這種想法我也只放在心上,不敢面對他那像找到正確答案似的確信。 當然的,船長不知道曾向公司說過與否,但若接受他的建議那兩年後的虧損可就大了,當然的,包括這些也都只是我事後的聰明,聯合國公海流刺網的禁捕的消息,就更不是當時我這個臨時年輕討海人料想的到的,而且在流刺網的作業中,雖然也感覺到一點殘忍,不過身處其中是不能多朝那樣去想的,甚至包括禁捕的消息剛出現時,我都仍還想以伊索匹亞的難民、人類食物的觀點想化淡那曾經有點是劊子手的助手的一些腦海影像呢! 當然的,伏羲定網罟的伏羲氏,好像要在這時候才開始對我有過意義,不然會一直只是教科書中該背的課文罷了,甚至在公司少東接船時迎面向船長對漁獲量的抱歉,提到的也還都是那個漁區的魚隻較小,該帶較小網目網具的話語呢! 註:
|
|
| ( 創作|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