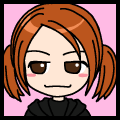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8/03 18:49:13瀏覽4022|回應1|推薦42 | |
《時間長巷》這本書,從大學時代起就一直躺在我的書櫃裡,至今重讀,脫下了包覆在外的政治薄膜,又顯露更深一層的文學價值。 閱讀《時間長巷》的歷程,對我而言,只是一種非常純粹性的,就當一位在政治界與學術界交錯奔走的學者,以書寫方式自我剖析的幽微心情。他在自序〈我的雙城記〉裡,將政治與學術形容為冷靜與熱情兩座遙遙對峙的城堡。當中的五十五篇散文,依時空對象被區隔成三輯,從第一輯對政治的熱情騷動、對左翼思想的迷亂幻滅;第二輯在靜宜中文系兼課時,回關單純學術環境的沉潛思考,一直到末輯回歸內心文人的反芻。 雖然全書由濃至淡終究未曾與政治論述全然脫鉤,但也許與他不間斷研究台灣歷史與投身文學運動的感觸有關,陳芳明始終懇切卻謙卑,把屬於文學的仍然留給文學,其他論述只是因為心情、只是因為對人群的觸覺而已,並不會過度覆蓋文字,讓讀者因過於鋒利的批判而擾亂閱讀步調,反而更能因為他在政治歲月中面對的事件,而更了解他書寫當下的心情以及創作的目的。 〈第一輯‧左翼道路〉 然而,通過這樣的告別,歷史才有可能產生斷裂。─〈斷裂〉 這是對一個新舊時代的切割。〈初識毛澤東〉、〈斷裂〉、〈巨人〉等篇章藉由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先後逝世及越戰、中美斷交等撼動國際的事件,經由各種書籍輿論,也透過當時海外所學的催化,陳芳明娓娓道出當時自己、海外留學生與台灣各種思潮的傾軋;〈背叛〉、〈歧路〉等數篇,則是由歷史學術出走至政治浪潮的困惑、掙扎以及抉擇。他將自己投入政治運動的路的決定稱之為蜿蜒前進、沒有終點的「歧路」。 而〈黑暗如碑〉之後陸續拆解出真正的主題-左翼道路,藉由接觸左派書籍、與左翼人士的偶遇交談,讓中西方思想像兩道滔天巨浪在他思想的兩端衝撞襲擊,使他陷入宛如白先勇〈芝加哥之死〉裡的研究生吳漢魂那樣無以為繼的苦悶。只是吳漢魂隕落了,陳芳明沒有。他選擇面對甚至參與,不惜在某些程度上拋棄過去抱守著的學術思維,雖然徬徨,但最終他還是寫下了:「背叛,是我唯一的選擇」這樣的文字當作文章的結尾,在我讀來,未曾感受任何殺戮之氣,那只是一個沈重的、甚至是不得已而暫且劃下的句號。 這樣一把闡述的刀,落下的力道恰恰好,用學術(或說是「文學氛圍」比較恰當?)鋪陳政治心情一直是隱藏在紙背的主要脈絡,有主觀意識卻比選擇過份疏離或盲目狂熱的文字,來得有閱讀性。從來一直不主動接觸帶有政治性的文字,或許是以往先入為主的偏狹印象使我停留在假借文學的旗號,卻高舉刀光劍影下赤裸裸政治文字的傷痕性批判,讓我感到哀傷,只不過,現在已然對那種裂帛式吶喊漸漸釋懷,那也是另一種學子的熱情傾訴;只是陳芳明平靜低吟的告解,能讓我更心平氣和去看待,學界如何經歷、感受與描繪一場大時代的各種震盪。 〈第二輯‧澀味燈光〉 就在那年(註1),川端完成日本文壇矚目的小說《雪國》。同樣都是把生命奉獻給文學的作家,川端在那個時代絕對不能了解為什麼台灣作家會寫的那麼緊張而痛苦。─〈尋訪〉 或許是離開校園之後歷經的波折,使陳芳明體會回歸校園的意義與重要性,自一九九二年起,他回到大學任教,展開了政壇(台北)與學院(台中) 的迴圈旅行,再加上高雄人的身分,台灣中西部山海景色不僅融入了他的「台灣文學運動史」與「台灣文化概論相關課程」,也讓他從一個原本自認是「中國歷史研究學者」的身分,轉而能夠實踐「謙卑地面對台灣的人文歷史」的心願。 〈描繪生命的地圖〉中,他要學生畫下心中的台灣地圖;〈帶你們到鹿港〉是一次校外教學,讓學生體會先民辛勤開鑿的生命痕跡;接著從沙鹿的風到溪頭的林、霧社的雨到立霧溪的痛,追隨光陰從陳盈潔到張惠妹,甚至反芻二二八事件與詩人吳新榮。所有四季更迭或歷史的行腳文字,皆成為被孕育著的幼苗,在陳芳明的敘述裡似乎得以成長茁壯。 是故,必須提及的是,我竟對〈澀味燈光〉一篇感到困惑了,並不是矯作,但也許是沒有任何理由而純然構成,用咖啡的澀味來開啟海外流浪時的寂寞,卻在中年時以紅酒猝然作結:「紅酒在口內鋪設粗糙、發麻的感覺,在無形之中阻止情緒的氾濫,成功地完成了一場淡化寂寞的儀式。」也許有時文人也會有不明己之所云,又或只是一種十分抽象的、虛無的感發,無法被解釋也不必有理由? 相較之下,〈尋訪〉所顯露的意義便十分明朗而令人激賞。陳芳明非常清楚的解釋了同一個時代的台日兩地作家的文學表情截然不同的原因:「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劃開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賴和的〈一桿秤仔〉與楊逵的〈送報伕〉(註2)自然不必多言,張文環的〈閹雞〉與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註3)也同樣深切刻劃了所謂殖民時代的文學面貌。如果那樣的文學潮流是人間,川端康成的《雪國》裡緩慢細膩優美到不像話的情調,就是天堂了。 〈第三輯‧激流亂雲〉 年代變得久遠而古老 不僅政治家有孤獨感,身為文人,面對浩瀚天地,我們也必須咀嚼寂寞。雖然行文至此仍然貼近政治運動,但筆觸不免有些沉澱了。一種舊時代的傾斜,就讓它慢慢躺臥成為一段讓人憑弔的歷史故事,於是他把線索伸父母對那個未曾傾斜的時代的印象、自己對當時父母的印象,延伸到對兒女的那些未曾吐露的歉語。 「女兒是那窗外的霧,已是那一片我難以領會的霧,……霧湧大地,湧來我未曾理解的秘密。中年父親的心情如我,撐起滿窗的等待,咀嚼滿屋的寂寞。」 如此心情想來與廖鴻基的〈出航〉(註4)有著ㄧ靜ㄧ動的異曲同工之妙了。 最後一個特別的主題則著重在於陳芳明一直持續不懈的詩創,從少時到盛年直至現今已邁耳順,艾略特、葉慈、余光中、洛夫、葉珊,甚至是前輯提及的左翼詩人何其芳,都對他的詩學道路有著深切的影響力。〈墓前花〉便是陳芳明前往麻州小鎮康科特的沉睡谷(SleepyHollowCemetery )拜訪梭羅(H.D.Thoreau)的墳墓時所創作的詩。因為一朵墓碑前盛開的小花,讓詩的開關被啟動,正是詩人的天份與本能。透過對梭羅的探訪致敬,讓他暫時擺脫現實喧囂的紛擾,得以返回文人本質,重新思索文學家創作的真諦。雖然他在〈秋天的簽名式〉裡還是補了一句梭羅書中的話:「對人民從不干涉的,便是最好的政府。」 但我想,是因為梭羅文字裡透露出的,資本主義巨獸的崛起下,深厚的人文關懷。與陳芳明回歸台灣土地的意識隱隱契合罷。梭羅曾經表達,「人祇有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才稱得上是豐富而堅強的。」從小我到大我,從個人、家庭,走向台灣社會這片土地,政治或許有立場,就連海外的台獨或統派都各有左右翼之分;但關心台灣的立場,卻是始終不變的──無論身在政壇或文壇。 〈最後〉 雖然這本散文集有許多政治歷史脈絡,但書寫所展現的文學價值卻超過了作者思想本身。以一個「理性學者」的身分,挑燈夜書,才能成就整齊優美而不過於浮誇的文字,是讓我敬仰的地方。 註1:那年:指一九三五年。文中說明同年作品有:發表在日本〈文學案內〉雜誌裡,楊逵的〈台灣文學運動的現狀〉、〈明日台灣文學的承擔者〉與賴和的小說〈豐作〉 註2:〈送報伕〉為中譯,原作為日文〈新聞配達夫〉,初刊於東京《文學評論》,1934年10月出版 註3:〈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亦為中譯,原作為日文〈パパイヤのある街〉,當時並獲得日本知名文藝雜誌《改造》的年度小說佳作獎,在台籍作家中非常難得。 註4:廖鴻基以一次出航敘述與女兒之間的緊密疏離關係的散文〈出航〉,獲選為九歌九十五年年度散文獎得主。 陳芳明簡介: 陳芳明,台灣高雄人。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台灣文學研究會創辦人之一,美國《台灣文化》總編輯。曾任民主進步黨文宣部主任,並同時任教於靜宜大學;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台文所所長,開設台灣文學史與台灣文學研究專題課程。著有散文集《掌中地圖》、《夢的終點》等,及文學、史學評論相關學術論著多部。 |
|
| (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