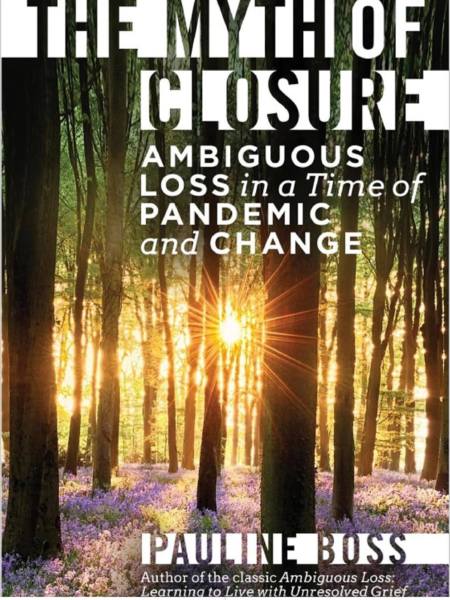比死亡還要難以接受的,是不告而別。~龍應台
昨天一個母親患有失智症的老友,傳來龍應台的《給美君的信》時,正好在讀心理學教授Pauline Boss的新作The Myth of Closure: Ambiguous Loss in a Time of Pandemic and Change。(生命終結的迷思 : 談大瘟疫時期的模糊失去)。失智症,又稱阿茲罕默症,目前仍屬無藥可醫、不可反轉的病症,歐美有四分之一的老齡人口被此症困擾,更大一群的長期貼身照顧家屬,身心健康的折損無以計數,卻較少受到社會關注。
從博士班就研究「模糊失去」並成為該領域權威長達40年的Dr. Boss稱,大瘟疫下無豫備丶無法陪伴的失去至親,比正常時期親人的逝去,更難接受,更多懸念,更難撫平傷痛;想邁向未來,卻是舉步維艱!
如何定義「模糊的失去」 (ambiguous loss) ?Dr. Boss是這樣定義的 : 「模糊的失去是一種沒有完結篇的失去。」或者,「一種身體或心理的不明失去,且沒有解決方案。」(“Ambiguous loss” is a loss without a conclusion. Or, “an unclear loss that can be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and it has no resolution.”)
她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教學和輔導數十載,在大瘟疫降臨前,被「模糊失去」綑綁、長時期無法走出傷痛和憂鬱的例子,如空難,或911/災難無法找到親人屍體的家屬;或因各種原因而將親生子女送人領養,或親生子女被拐騙而行蹤不明的爸媽。
家有失智症親人,同樣艱難,但模糊的失落程度更複雜丶煎熬更久。病人在親人眼前每天一點點地失去,形體存在,但心和靈卻愈飄愈遠。
Dr. Boss將模糊性失去或失親約略分為兩種,一種是形體上的模糊失親,如前面所述的親人被拐賣、突然失蹤生死不明;另一種就是失智症這種形體仍存在,但精神上已非本尊的失親。面對這種走出生命正常循環(老病死)的「模糊的失去」,親屬受苦更深更久,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朋友,他/她們,需要更多的時間被理解和被陪伴。
龍應台透過書寫來處理她的「模糊的失去」,她和年輕的母親對話,還原她印象裡充滿生命力的美君。
失去,不是只有一種方式;道別也是! VIDEO
~*~*~*~*~*~*~*~*~*~*~*~
《給美君的信/龍應台》(轉載)
65歲的作家龍應台辭職回家,照顧93歲的母親應美君。
美君患上了阿茲海默症,誰都不認識,在照顧母親的過程中,龍應台提筆寫下了給母親美君的信, 並把這個過程寫成了一本書:《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
“此生唯一能給的,只有陪伴。而且,就在當下,因為,人走,茶涼,緣滅,生命從不等候。 ”
美君是我的母親,她今年93歲了。 她還活著。可是失智,已經不認得我,不記得我,不能和我說話。
事實上,她已經“離開”我了。
說不清楚她的病癥是從哪一年開始。
因為失智症是那樣一個逐漸的過程,就像一顆方糖進入咖啡,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就融化了。
寫這本書,原因很單純。我想和美君說話,可是她沒法跟你說話。 在我完全沒有準備的時候,她已經變成了一堵墻,而這堵墻是這輩子對你恩情最深的人,是你最愛的人,最尊敬的人。我真的覺得蠻傷心的。 我只能用文學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美君上學時用的木頭書包, 箱蓋內側有她自己寫的兩行字:“此箱請客勿要開,應美君自由開啟”。 美君聰明極了,又非常的有個性。 她的木頭書包,沒有把警告語寫在箱子外面,反而寫在箱子裡面。 為什麼?說明她不是寫給旁人,而是寫給一個已經偷偷打開的人。 一定是她的爸爸媽媽,或者是她的兩個討厭的哥哥。 最後一秒鐘,我警告你趕快關起來!
那時候她才幾歲?真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慧的小孩。 她性格裡有一種狂放不羈。我記得年輕的時候,她笑起來,不是那種掩嘴巧笑,她是豪放地大笑,拍著大腿,笑得簡直要在地上打滾。 她比我愛美,比我講究,出門一定要穿旗袍。 她那黑色的緞質旗袍,開襟裡頭要塞一條小小的白色的手絹,而且一定要灑香水。 她是大小姐,我的父親是窮小子,還是外鄉人。 1947年,他們在杭州天香樓結的婚。 美君會下嫁給他的原因……我想是因為他帥(笑)。 我們都認為爸爸比媽媽漂亮,可是為什麼他們生了四個子女,沒有一個像爸爸,都像媽媽?幸好媽媽比爸爸聰明。 1949年,24歲的美君,跟著自己的湖南丈夫,在隆隆戰火中,背井離鄉,一路顛沛流離,最後落腳到了台灣。三年以後,龍應台出生在高雄。
我14歲時看到的美君,是一個織漁網的婦人。 那時候美君42歲,還算年輕,正在掙札著要讓四個孩子同時上初中、高中、大學,每一個孩子都需要學費。 她跟漁村的婦女們一起,手裡拿著梭,從早到晚織著漁網。 她那麼愛美的一個女人,脫下了她的旗袍,赤著腳,坐在骯臟的水泥地上。 一張漁網大概是一個客廳的大小,要織半個月,手上織出了繭,可以換回來80塊台幣。 她也去養豬,做很粗的勞動,穿著套鞋,踏進小河裡去割草。 她什麼都願意做,自力更生,是因為她愛她的兒女。 她的丈夫認為女孩子讀書幹嘛,讀師專最好,將來做小學老師,18歲就可以嫁人。她替她女兒去跟丈夫說:“女兒要上大學。” “她如果不讀大學,以後就會跟我一樣。” 她借錢去交了我的學費。 後來我才意識到,美君其實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只不過她的時代沒有這個詞。 17歲的時候,憲兵隊亂抓人,她就敢代表整個街坊, 手無寸鐵,一個人跑到憲兵隊去跟憲兵理論。 六十五歲,她還去紋眉,紋眼線。七十多歲了,還在問我要不要去隆鼻。去做各種讓自己美麗的事情。 她還曾經建議我去隆乳。 那一刻我大概三十多歲,她六十來歲,是我現在的年齡。 我們倆一起站在梳妝台的很大的一面鏡子前面。我在梳頭,她也在梳頭。 她說,你知道嗎?你可以去做什麼什麼事。我當然嘲笑她一番。 這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起來的、我們倆之間和“女孩子”有關的談話。 除此之外,她從來不和我談“女孩子的事”——你要怎麼選男朋友,怎麼相夫教子,怎麼煮飯做菜,怎麼伺候公婆——從來沒有過。 她好像沒覺得我是個女孩子。 很可能是她希望我能夠盡其所能地發揮我的才能,因為她自己的才能沒有得到這個機會,時代不允許她發揮。 我終於受足了教育,而且受的教育越高,我走得越遠。她歡歡喜喜,目送我遠行的背影。 然後她就老了。眼皮垂下來,蓋住了半只眼睛;語言堵住了,有疼痛說不出來;肌肉萎縮了,坐下就無法站起。 曾經充滿彈性的肌膚,像枯萎的絲瓜垂墜下來。曾經活潑明亮的眼神,像死魚的灰白眼珠。 她不曾享受過人生,因為她的人生只有為別人付出。 我在城裡過自己的日子,而她在人生的最後一裡路,孤獨地走著。這,對嗎? 2017年4月1日,我在香港參加生平第一次禁語禪修。 禪修的時候,就在那一剎那,我決定了:搬家,搬回屏東,照顧美君。 人到了50歲之後,會發現好時光不多了。重要的事情不可以拖。 我再拖下去,我不知道美君還會不會等我。
搬家的過程很迅速。母親原本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 我佔下哥哥的頂樓倉庫,等於住在母親的樓上。 改造倉庫只用了三個禮拜,第四個禮拜我就搬家了。
我開著車,拖著滿滿一車行李,多數是書。兩只貓跟我一起南下。 從此以後,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大聲對媽媽說話: “應美君你在嗎?應美君你今天好嗎?睡得怎麼樣? 風太大了是不是?等下我幫你拿條圍巾好了。” 媽咪在,貓咪在,那裡就是家了。 43年前,我離家去台北,美君一定有親自送我上火車。 我上車的那一刻,有沒有回頭看她一眼?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沒有。 留學時,父母到松山機場送我。我進海關之前,有沒有回頭看美君一眼? 一定沒有。 原因是,當時我的心目中是沒有父母的。 父母就是理所當然地在那,就像家裡的家具一樣,你不會跟家具說對不起。
我離開美君時,她50歲。 輪到我50歲時,安德烈16歲。他去英國當交換生, 我去機場給他送行。他進海關之後,我等著他回頭看我一眼。但是他沒有回頭。 我當場崩潰。心裡想:“這個16歲的小孩怎麼這麼沒有良心?” 我對兩個兒子的愛,需索無度。 但回想起當年我自己離開母親時,卻沒有一刻想到,美君需要我。 甚至是在往後的30年中,都沒有想到,她可能想念我。 我一心向前,義無反顧,並未為她設想過。
“我後悔,為什麼在你認得我的那麼長的歲月裡, 我沒有知覺到:我可以,我應該,把你當一個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們彼此之間做些什麼? 我們常常約會——去看一場特別的電影,去聽一次遠方的樂團演奏,去欣賞一個難得看到的展覽,去吃飯、去散步、去喝咖啡、去醫院看一個共同的老友。 我曾經和兩個同齡女友清晨五點摸黑到寒冷的陽明山去看日出點亮滿山芒草。 我曾經和幾個年輕的女友在太平洋畔看滿天星斗到淩晨三點。 我曾經和四個不同世代的女友在蒙古沙漠裡看檸檬黃的月亮堂堂從天邊華麗升起。 我曾經和一個長我二十歲的女友在德國萊茵河畔騎腳踏車、在紐約哈德遜河畔看大川結冰。 而你,美君,從來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單裡。
對於父親和母親這樣的人,我們最容易被陷在墻的結構裡頭。 這個房間叫做廚房,你就不要想它還可以是個書房。 可是其實,母親從來不只是母親啊。 她是應美君。她有名有姓。她有性格,她有脾氣。 她有傷心的時候,她有她內在的無可言說的欲望。 其實如果可以早一點有覺悟,早一點跟母親做朋友,真是福分,對吧? 搬回屏東這事,我晚了三年。 現在,不說話的她,對我是個謎。 你知道,我真想念她。特別奇怪的是,她人就坐在你旁邊,然後你想念她。因為她事實上已經走了。
比死亡還要難以接受的,是不告而別。 美君將來也會去到爸爸身邊。 當時在葬父親的時候,已經在旁邊留好了墓位。 上一代不會傾吐,下一代無心體會,生命,就像黃昏最後的余光,瞬間沒入黑暗。
寫《天長地久》的最後三個月,那真是沒日沒夜地工作。 這本書,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任何人,將來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 任何人,在每一天時間的進展裡頭,都在忘記,都在走向終點,不是嗎? 這件事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在我們每天呼吸的空間裡頭,為什麼不去好好地了解它、面對它? 如果整個社會的集體意識,對於失智、對於衰老、死亡、陪伴,對這些事情的認識水平提高的話,是會不一樣的。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太遲太遲的領悟。所以我寫了這本書。 希望比我年輕的讀者們,如果可能的話,你不要太遲。 這個世界,沒有任何天長地久。 你必須把片刻當做天長地久,才是唯一的天長地久。 (2021.12.29 星期三)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