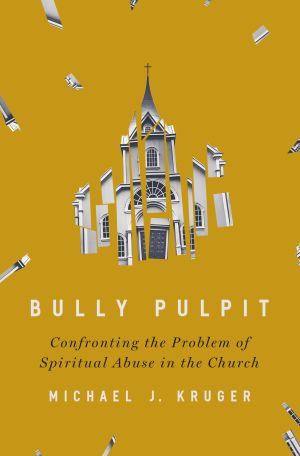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03/04 23:52:58瀏覽797|回應0|推薦3 | |
【講台霸凌】第四章尸體的蹤跡– 為什麼教會不阻止霸凌領袖呢邁克爾·J·克魯格/白帆譯 惡魔是真實存在的...它們住在我們內心,有時會獲勝。-斯蒂芬·金 1986 年,在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電影《異形》中,主角雷普利(西格妮·韋弗飾演)發現了一個名叫紐特的小女孩,她是 LV-426 星球上人類殖民地的最后幸存者。她的父母和她認識的每個人都被可怕的外星生物消滅了。當這個受到創傷的女孩終於開始說話后,她問了裡普利這個富有洞察力和悲劇性的問題:“媽媽總是說沒有惡魔——沒有真正的惡魔——但有……他們為什麼要告訴小孩子這些呢?” 孩子們有一種單刀直入的能力,會問成年人喜歡回避的問題。如果世界上有壞人,我們為什麼要假裝沒有呢?我想,我們可能會像雷普利在電影中那樣回答:“大多數時候是真的。”換句話說,既然大多數人都是好人,我們就不要在意少數人的不好。 有些教會對屬靈虐待有這樣的心態:既然屬靈虐待的牧師很少見,我們就不要談論這個問題,就假裝他們不存在。當然,問題是,他們確實存在。正如耶穌所教導的,有時,看似好人,實際上是壞人:“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太7:15)。 換句話說,要警惕惡魔。 現在,有些人可能會對“惡魔”這個詞來形容霸凌牧師感到猶豫。也許有人會說,他們肯定沒那麼糟糕。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太嚴厲了?好吧,如果有人更喜歡“貪婪的狼”,那完全沒問題(盡管我不確定是否存在有意義的差異)。但我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使用“惡魔”一詞,即指霸凌牧師經常發生的現實有兩個側面,就像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著名小說《化身博士與海德奇案》中的主角一樣,一面是溫暖和善良(面對大多數人的時候),另一面是殘酷和黑暗(只有受害者才能看到)。就像史蒂文森的小說中一樣,大多數人無法接受同一個人可以兼有兩種面具的事實。 這就引出了本章的主題。如果我們要解決屬靈虐待牧師的問題——海德斯先生就在我們中間,可以這麼說,——那麼,我們最好承認他們的存在,並學會如何發現他們。但是——這是一個可悲的現實——教會似乎通常不太擅長這樣做,不擅長捕捉惡魔。 在一個又一個的虐待故事中,同樣的悲慘事件不斷上演。這位虐待牧師多年來,一直有破壞性行為,直到有人終於勇氣發聲。但即使以后,大多數教會什麼也不做。 (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有些教會將攻擊發聲的人。)即使教會做了一些事情,也往往是半心半意、不充分的回應。當罕見的教會最終因虐待而罷免一位牧師時,這就引出下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們花了這麼長時間才採取行動?為什麼你能容忍這種行為長達二十五呢年? 我們問這些問題是因為有証據——大量的証據—揭露這些牧師的破壞性行為。查克·德格羅特(Chuck DeGroat)在他的著作《當自戀來到教會時》(When Narcissism Comes to Church)中指出,這樣的牧師常常會留下“關系碎片場”。他觀察到:“通常,在自戀牧師被公開曝光之前,會有多年痛苦的小遭遇被掩蓋。 這些牧師有傷害同工的記錄,最終,通常是在很多年之后,這種情況就會追上他們。這是一眼還看不出來的罪惡跡象,只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才變得清晰可見。正如提摩太前書 5 章 24 節所說:“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如同先到審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隨后跟了去的。” 簡而言之,施虐的牧師會在身后留下‘尸體的蹤跡’。 這就是惡魔所做的。那為什麼教堂看不到尸體的蹤跡呢?他們為什麼不把這些點聯系起來呢?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問題不僅僅在於一個施虐的牧師,而在於,教會文化助長了(有意或無意)虐待行為。 或者,正如奧克利和金蒙德所觀察到的那樣,“我們[傾向於]關注壞蘋果以及它的問題所在,而不是關注存放它的木桶。”本章中,我們將關注木桶。 責任結構不充分:什麼尸體?一些教堂看不到尸體的第一個原因是:這些尸體被隱藏起來。可以說,霸凌牧師把他們埋在后院,而教會的問責結構不完善,意味著人們無法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時甚至不想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 尸體以多種方式隱藏。首先,許多牧師虐待的受害者被壓制或被迫離開。在一個又一個屬靈虐待的故事中,遭受虐待的人被孤立,並被趕出了該事工。人們看不到整體模式,因虐待的受害者為擔心遭到報復而不敢發聲,就悄悄離開了,而那個施虐的牧師卻留下來了。 如果施虐的牧師仍然存在,那麼,他就可以控制敘事。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受害者有時會因整個事件而受到指責。他們才是問題所在,而不是施虐的牧師。 其次,施虐牧師破壞關系的模式往往不會向更大的領導機構透露,當然也不會向整個教會透露,只是在某些委員會或小組內傳達。韋德·馬倫 (Wade Mullen) 觀察到,“許多受害者發現,他們向某個組織提出的虐待報告是由專門的團隊處理的,或者是由一小群執事會成員處理,而不是與整個執事會共享。” 現在,一定程度的保密是可以理解,也是明智的。所有的不滿都不應該在全教會面前宣泄出來。也就是說,一些教會已經學會了“管理”虐待牧師的關系碎片場,其方式與現代政客沒什麼不同——它被隱藏在人事委員會中,以至於永遠見不到陽光。這種方法非常有效,有時甚至連牧師自己的長老都不知道這種關系的破裂已經發展成長期模式,或者至少不知道它有多深、多廣。 第三,即使虐待受害者挺身而出,並被領導機構聽到其聲音,但問題也常常被淡化和最小化——這被視為任何部門都不可避免的沖突。你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嗯,那只是鮑勃牧師。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或者通過堅持認為,這正是當你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時會發生的事,以此來將問題最小化。我們在《使徒行傳 29》前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蒂米斯 (Steve Timmis) 的案例中,看到這種反應,他最終因屬靈虐待而被解雇。他的捍衛者表示,這些沖突僅僅是由於“領導風格的沖突”或“被強勢領袖激怒”。 像這樣的最小化模式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為它部分正確。每個事工都有一些沖突。我們生活在一個墮落的世界,沖突就是教會的一部分。 但是霸凌牧師有一些不同,他的關系碎片場不僅在沖突數量上不同,而且在沖突深度上也不同。通常,他身后的生命都被真正摧毀了。許多人離開了事工,也有許多人則完全放棄了基督教信仰。此外,施虐的牧師常常存在未解決的沖突,他們通常與許多以前共事的人疏遠。 一旦出現這種模式,教會領袖就需要進行計算。所有這些沖突都有一個共同點:牧師。到底是這些人都有問題,還是牧師自己有問題呢? 可悲的是,有時,長老們看不到尸體,只因為他們不願意看到。盡管后院挖開了所有的洞,他們只是不斷地告訴自己,一切都已經好起來。 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呢?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人性的神學觀點不正確:他們認為這樣的惡魔不存在——至少在他們的教會裡不存在。 對墮落的錯誤看法:沒有惡魔改革宗福音派經常談論全然墮落的教義——罪比我們意識到的更深刻、更有害,影響著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行動、思想、意志)。雖然每個人都沒犯什麼大罪,但每個人——甚至牧師——都有可能犯下嚴重的邪惡罪行。 盡管許多教會在紙面上確認了這一重要教義,但當涉及到屬靈虐待的情況時,就很快會被遺忘。一旦受害者有勇氣說出虐待行為,通常會遇到齊聲反駁,比如:“我認識這位牧師,他永遠不會這樣做”,或者“這位牧師多年來已祝福並幫助了無數人。他永遠不可能做這樣的事。”領導層沒有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並仔細調查,而是認為這種虐待是不太可能的存在,因此不太深追事情的真實狀態。 換句話說,惡魔不存在(至少在我們的教會裡不存在)。 具有悲劇性的諷刺意義是,虐待牧師的捍衛者經常對受害者的正直和品格提出質疑,暗示他們是在污蔑或誹謗領袖的“好名聲”。因此,當涉及到牧師時,全然墮落的教義被遺忘了,但當涉及到受害者時,卻被記起了。 拉維·撒迦利亞被揭露之事告訴我們,即使是最受尊敬和愛戴的領袖,也有可能行出難以形容的墮落。撒迦利亞的捍衛者辯稱,他永遠不能、也永遠不會這樣施暴。但不乏証據表明,他的確如此行。盡管存在可疑的短信、不可靠的解釋以及多名原告的証詞,但撒迦利亞的捍衛者仍然支持他們的領袖。 如何解釋教會和基督教組織忽視徹底墮落的影響,並為他們的領袖辯護的傾向,即使有具體的証據表明事實並非如此?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他的暢銷書《與陌生人交談》中,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答案。格拉德威爾列出了許多備受矚目的刑事案件,包括杰裡·桑達斯基和拉裡·納薩爾的性虐待案件,並表明,盡管有大量証據表明,犯罪者有罪,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假定為無罪。為什麼?只因所謂的真理默認理論。當人們在互動時,“我們默認真理:我們的操作假設是,與我們打交道的人是誠實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假設並不是一件壞事。格拉德威爾認為,人類默認真理,因為我們需要這樣做,才能在社會中合理有效運作。你能想象,如果每個人都經常懷疑、質疑和猜疑別人以及其每一個真理主張嗎?這將是一個悲慘的世界,更不用說效率低下了。 但問題更大了。格拉德威爾指出,除了假設人們通常說真話之外,人們還常常錯誤地認為自己擅長發現不說真話的人。我們認為自己有能力,通過評估人們的舉止、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來確定他們是否在說謊。但統計數據卻恰恰相反。格拉德威爾提供了一個又一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執法人員(警察、法官和中央情報局特工)也無法有效識別壞人。格拉德威爾認為,我們假設大多數人都在說真話,而對識別撒謊者的能力過於自信,這兩者結合起來,就在識別人的欺騙性方面提出一個嚴重問題。 但問題變得更糟。格拉德威爾指出了這些案例中的第三個因素:當我們被迫相信壞人的一些真正困難時,就特別不擅長發現這些壞人。他寫道,“當我們被迫在兩種選擇之間做選擇時,對真理的默認就成為一個問題,其中一種是可能的,另一種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是否更容易相信一個可愛的、討人喜歡的人像杰裡·桑達斯基這樣,在幾十年裡性侵了許多十幾歲的男孩,還是更容易相信這只是一場淋浴間打鬧、一場大大的誤會呢?后者更容易讓人接受。我們是否更容易相信,像拉裡·納薩爾這樣受人尊敬的奧運隊隊醫是一個可怕的性侵者,或者有些女孩誤解了骨盆檢查的含義?同樣,許多人發現,后者更容易被接受。 格拉德威爾的研究也適用於教會中的屬靈虐待。教會法庭——長老會、執事委員會——常常認為,他們善於發現不誠實、欺騙性的牧師。但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默認面前的人說的是實話,特別是如果這個人有著長期看似忠誠的事工記錄。我們可以想象他們心中的困境:更有可能的是這位受人尊敬的牧師一直在專橫地虐待、霸凌他的羊群,還是人們過於敏感,被一位強勢的領袖激怒了? 如果評估被指控牧師的人認識牧師本人(教會法庭上幾乎總是如此),情況就會變得更加復雜。如果是這樣,他們很可能已經對牧師評價很高。為什麼?因為惡霸不會欺負所有人。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就不會持續太久。霸凌者很少橫向或向上欺凌。他們幾乎總是欺負下面的人。因此,牧師常常對評價他的人——他的同輩——非常好。 由於全然墮落的教義已經退居二線,這些人並沒有意識到,正如所指出的,屬靈虐待的牧師幾乎總是有兩面人:一面是迷人、親切、討人喜歡。但另一面可能是專橫、高壓、具有威脅性——同樣,就像杰基爾博士和海德先生一樣。他們對誰能看到他們的哪一面是有選擇性的。在很多方面,施虐的牧師就像施虐的父母一樣。有時,父母對孩子是仁慈和愛憐的,有時卻是殘酷和具有報復性。他們在兩個角色之間來回切換。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壞人就在面前時,我們卻無法看到問題嗎?至少在原則上,對全然墮落的神學信仰應該有所幫助。如果定期教導這一教義,應該會使任何個人和任何教會法庭都面臨自稱為基督徒的可能性,甚至是牧師,可能會犯下可怕的罪。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假設被告有罪,僅僅意味著這些指控不排除其可能。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會進行合法的調查。 但我們還可以做更多。格拉德威爾指出,某種罕見的個體並不是天生就認為每個人都是誠實的。某種性格類型是違背常理的——格拉德威爾稱之為“說真話的人”。這些人“不屬於現有的社會等級制度。”因此,他們“可以自由地脫口而出令人難以忽視的事實,或質疑我們其他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漢斯·克裡斯蒂安·安徒生的故事《皇帝的新裝》中,小男孩是說真話的人,而其他人都在和裸體的國王一起玩耍,男孩脫口而出:“看看國王!他什麼都沒穿!” 大多數長老會、教會法庭和基督教事工的執事會都是由內部人士組成,而不是來自教會普通會眾,他們通常由領袖的親密同工,甚至是家人組成。那麼,他們怎樣才能客觀地追究這位領袖的責任呢?這與警察追究其他警察過度執法是同樣的問題。他們都是同一個俱樂部的成員。因此,真正的問責很難實現。 這些團體需要的是一個說真話的人,也許是幾個。這些基督教組織是否有可能需要重新調整其領導結構,以納入“不屬於現有社會等級制度”的局外人?我們將在第七章進一步探討這種可能的重組。 對恩典的誤解:每個人都是惡魔基督教的核心始終是關於恩典。保羅說得好:“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夸。”(弗 2:8-9)。近年來,特別是在改革宗、福音派圈子裡,人們對恩典產生了新的關注。許多人呼吁“以恩典為中心”的講道,重點不是我們的好行為,而是基督所完成的工作。這是一件好事。 但為了強調這種恩典的美麗,有些人採取了額外的措施。既然我們都是靠恩典得救的絕望罪人,那麼,我們就不能區分罪的等級。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聽到“所有罪,都是平等的”或““我們都是同樣的罪人。”這樣的話語是為了維護恩典;也就是說,沒有人比其他人更好。 現在,“所有罪,都是平等的”,這句話有部分正確,這取決於一個人的意思。如果有人用這句話,只是為了表明任何罪都足以使我們與神隔絕並招致祂的憤怒,就是正確的。神是如此聖潔,任何違反祂律法的行為,無論在我們看來多麼微不足道,都是值得祂公義審判的罪。 但這並不是該短語的唯一使用方式。有人則用它來“消除”所有罪惡,使之無法彼此區分。或換句話說,它把所有人都描繪成同樣邪惡。如果所有的罪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犯了罪,那麼,沒有人比其他人更聖潔。在一個對“平等”著迷的世界裡,這個詞的這種用法特別有吸引力。讓每個人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單一、無差別的群體。 換句話說,這種對恩典的理解,要求我們相信自己都是惡魔。 但這種信念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其一,說所有的罪都是一樣的,就是將罪的后果與罪的可憎性混為一談。雖然所有罪的影響都是相同的(使我們與神隔絕),但它們並非同樣都令人發指。聖經清楚地區分了不同的罪。某些罪的影響更為嚴重(哥林多前書 6:18)、罪責(羅馬書 1:21-32)、應有的審判(彼得后書 2:17;馬可福音 9:42;雅各書 3:1),以及一個人是否有資格從事事奉(提摩太前書 3:1-7)。 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恩典的誤解被用來為霸凌領袖辯護。有人認為,如果我們都是平等的罪人,就應該給霸凌牧師一個機會。他們是罪人,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如果不這麼說,我們就會把自己放在對牧師審判的位置,讓自己比他人更正義。相反,我們需要“向霸凌牧師展示恩典”。 可悲的是,這種對恩典的誤解常常被歸咎於受害者自己。他們因“不寬容”、“心懷怨恨”或(我們再說一遍)“不表現出恩典”而受到指責。 不難看出,這種神學錯誤有多麼嚴重,讓受害者覺得自己有罪,好像他們的鐵石心腸阻礙了“和解”,完全忽視了虐待行為本身的可惡性,忘記了有些罪比其他罪更嚴重,有些罪人比其他罪人更壞。正如第三章所示,牧羊人虐待羊群是最令人震驚的事件之一,這種對恩典的濫用,忽視了聖經中所有關於維護公義和正義,以及保護無辜者的段落。 可悲的是,另一個對恩典的誤解被用來為施暴的牧師辯護,並進一步傷害受害者。有人認為,如果我們都同樣有罪,就必定意味著,施虐的牧師和受害者對沖突負有同樣的責任。對恩典的錯誤理解被用來淡化虐待的可惡性,並加劇受害者的罪惡,無論這些罪惡是什麼。 我們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傾向,要對沖突雙方“公平”。但有時,我們認為公平意味著我們必須對雙方承擔同等的責任。否則,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找出真正的罪魁禍首。當我們已經知道每個人都是罪人時,為什麼還要費心去調查呢?告訴雙方承認他們(同等)的罪,並找到相處之道,這要容易得多,而且在許多人看來,甚至更屬靈。 因此,長老會有時會發表諸如“這裡的每個人都有罪”或“雙方都有責任”之類的聲明,把虐待變成了純粹的關系沖突,與保羅和巴拿巴的分歧沒有什麼不同。 需要明確的是,我並不是說,虐待的受害者不是罪人。他們是。我也不是說,受害者永遠不會做錯事,他們會錯。但正如詹妮弗·米歇爾·格林伯格所說:“每個人都是罪人,但並非每個人都是施虐者。” 對和解的錯誤看法:與惡魔見面吧!大多數執事會或管理機構不喜歡團隊分裂。像大多數基督徒一樣,他們希望看到爭端迅速得到解決——這很好。事實上,現在似乎有比以往更多尋求和睦的部門。但這種建立和平的渴望,有時會導致教會匆忙讓虐待受害者與施虐者和解,這是一種病態考量。因為教會經常將整個問題僅僅視為“沖突”,所以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專注於正義或問責制,而只需將受虐待者和施虐者放在一個房間裡,每個人都承認自己有罪,問題就解決了。 也就是說,人們只需要與惡魔見面即可。 但這種做法令人深感擔憂。虐待案件不僅僅是沖突,而是落在不平等的競爭環境裡,就相當於丈夫毆打妻子,然后和事佬告訴夫妻倆只需要做婚姻咨詢,在那裡,他們都承認自己有罪。但這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當然,妻子也是罪人。但無論她犯了什麼罪,也不能為丈夫的虐待做辯護,也不應減少教會優先解決虐待行為的必要性。 正是這個錯誤,使得朱迪·戴布勒的和解事工變得如此悲慘。 正如第一章所討論的,戴布勒應該是教會以聖經方式來解決沖突的主要領袖, 但她的和解方法卻常常繞過那種會導致真正問責的事實調查,而是假設雙方都同樣有錯為基點,來展開和解。正如《今日基督教》報道的那樣,“她並沒有把客觀地描述事實作為首要任務……即使調解是因虐待指控而促成的。和解倡導者表示,相互認罪並不是應對不公正行為的適當起點。” 關於和解的正確方法,我還有很多話要說(將在第 5 章討論馬太福音 18 章)。目前,當教會尋求霸凌牧師與受害者之間的和解時,需要牢記以下幾項原則: 首先,不應要求受害者與施暴的牧師會面,除非他已被追究責任。和解的基礎始終從所發生事件真相開始,並對所發生事件的追責。擔責是教會的工作,而非是受害者的。如果教會未能提供這種擔責和保護,卻堅持讓受害者與施虐者會面,這就把重擔轉嫁到受害者身上。教會正在讓受害者做教會自己沒有做的事情。現在,受害者必須証明自己的受虐情況,卻得不到教會的保護或幫助。這種情況為施虐者提供了更多攻擊受害者的機會,實質上是再次虐待他們。 其次,受害者不應該會見施暴的牧師,除非牧師真正悔改。人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場景:教會確實追究了一名霸凌牧師的責任,但該牧師仍目中無人,且不願悔改。但除非有真正的悔改,否則不可能有符合聖經的和解:“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他若懊悔,就饒恕他。”(路加福音17:3)。在這種情況下,虐待的受害者應該等到教會確定牧師已經真正悔改,僅僅聲稱悔改都不夠,他必須向能夠正確評估此事的管理機構表示悔改。 第三,受害者在情感和屬靈上做好准備之前,也不應該與霸凌牧師見面。即使施虐者被追責並悔罪,也不意味著必須立即召開和解會議。許多虐待受害者都受到深深的創傷,以至於他們很難與施虐者在一起,直到真正的治愈發生。這可能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 如果虐待的受害者拒絕見面,頑固不化的牧師可能會將受害者描繪成不寬容,且不願意和解的人。他將佔據道德制高點,讓自己成為和平締造者,讓自己成為心懷怨恨的受害者。這就是為什麼在滿足指導方針之前,教會甚至不能要求受害者與施虐者會面。這樣,阻止聚會舉行的就是教會,而不是受害者。 J·R·R·托爾金(J. R. R. Tolkien)的《雙塔》(The Two Towers)中的一個場景恰如其分地說明了與一位頑固不化、濫用職權的領袖締造和平的危險。在巫師薩魯曼毀滅性的背叛之后,他終於遇到了甘道夫和洛汗國王希奧頓。盡管薩魯曼犯下了令人發指、難以形容的暴行,但他並不承認自己任何過錯,也沒有表現出任何悔意。與此同時——這是關鍵——他仍然想要與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交換和解協議。他要的是所有施虐的領袖都想要的:沒有悔改和問責的和平。 托爾金如此准確地描繪了一個虐待領袖的語氣和態度,這是值得注意的。當薩魯曼對希奧頓說話時——曾試圖將國王連同他的子民一起消滅——但此時,他給人的印象是善良、通情達理、平和:“你為什麼不以朋友的身份來?我非常想見到你。”然后,他提出了和平:“我說,希奧頓國王:我們可以擁有和平和友誼嗎?你和我嗎?這是我們的權柄。”當他與甘道夫交談時,薩魯曼邀請他進行一場和平對話:“為了共同利益,我願意糾正過去來接納你。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嗎?你不來嗎?” 在所有這些陳述中——盡管看起來流暢而迷人——請注意,沒有人承認有罪或做過錯事。相反,薩魯曼做了一些虐待領袖所做的事情:他把自己描繪成真正的受害者。他翻轉劇本,讓自己成為悲傷的一方:“盡管我受到了傷害,但洛汗人,唉!雖然我曾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我還是會救你。”當他與甘道夫交談時,他沒有承認自己的罪過,而是指出了甘道夫的罪過:“你很驕傲,不喜歡建議。” 換句話說,都是別人的錯。 值得慶幸的是,盡管薩魯曼甜言蜜語,希奧頓和甘道夫並沒有被愚弄。他們不進入薩魯曼的房間來促成和平協議。希奧頓很直白地說:“當你和你所做的都滅亡時,我們就會享有和平... 。薩魯曼,你是個騙子,有一顆敗壞的心。”同樣,甘道夫也沒有接受會面的邀請:“不,我想,我不會來。但聽著,薩魯曼,最后一次!你不願謙卑下來嗎?”甘道夫沒有按照薩魯曼的條件見面,而是簡單地呼吁薩魯曼悔改——並且真誠而誠懇地懊悔。但是,像大多數濫用權力的領袖一樣,薩魯曼不會心軟。因此,甘道夫解除了他的職務:“薩魯曼,你變成了一個傻瓜,但又很可憐。你可能仍然遠離愚蠢和邪惡,並一直在服務。但你選擇留下來... 。我將你逐出了修會和議會。” 結論當執事會或基督教組織面臨牧師或領袖虐待的指控時,我們需要意識到,他們可能已經有了以下假設:(1)這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什麼尸體?); (2)這位牧師看上去是個誠實、善良的人,是我們所認識和喜愛的(沒有惡魔); (3)每個人都是可怕的罪人,各方都必須受到指責(每個人都是惡魔); (4)不需要問責,因為只要雙方見面(只要與惡魔會面)就可以解決沖突。 考慮到這些假設,再加上大多數霸凌牧師所採用的廣泛而有力的防御策略,我們面臨著一個相當令人擔憂的含義:在目前的系統下,要對一位牧師進行屬靈虐待定罪是極其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案件特別嚴重,且有大量的外部証據(視頻、錄音、電子郵件),否則,屬靈虐待牧師不太可能因受害者的証詞而受到指控,讓教會法庭了解真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場艱苦的戰斗。 顯然還有更多工作要做。如果我們要與教會中的虐待作斗爭,我們必須了解的不僅僅是導致其不受制止的神學錯誤。我們必須還要了解施虐者及其支持者為自己的虐待行為辯護所採用的一系列策略。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這個主題。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