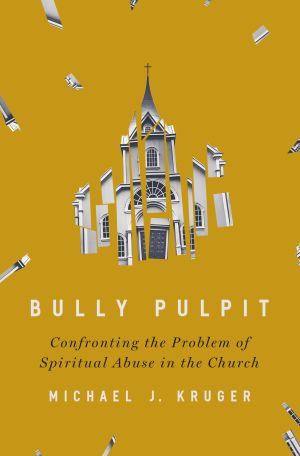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03/10 12:48:21瀏覽548|回應0|推薦3 | |
【講台霸凌】第五章翻轉劇本-濫用權力的領袖及報復策略邁克爾·J·克魯格/白帆譯 邪惡總是借其出色的欺騙力量而獲勝。古往今來,病態的天真和詭詐的罪惡之間一直存在著災難性的聯盟。 -G。 K·切斯特頓 2018 年 4 月,美國最具標志性、最成功的教會之一--柳溪社區教會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師比爾·海波斯 (Bill Hybels) 宣布,他將在服事 42 年后辭職。從許多標准來看,他的事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柳溪教會每周吸引近兩萬五千名信徒來到教會的主區和七個衛星區,為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教會樹立了榜樣,說明如何通過建立對非基督徒友好和歡迎的敬拜體驗,來有效地接觸靈魂失喪者。海波斯牧師似乎會騎馬馳騁,漸漸消失在夕陽下,為神的國度完成令人驚奇的事情。 當時的會眾並不知道,早在 2014 年,指控就開始浮出水面,稱海波斯多年來一直與教會中的女性(包括員工)發生不正當的性關系。雖然教會的長老們進行了內部“調查”,並確定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海波斯也稱自己“清白”——但指控並未消失。 因此,為了搶佔先機,海波斯最終向《芝加哥論壇報》公開發表講話。據《論壇報》報道,海波斯斷然否認所有指控,聲稱前工作人員和教會成員都在撒謊,並莫名其妙地勾結起來攻擊他:“四年來,這是對我們教會長老和我的一次有計劃的、持續的攻擊... 。我想對全國所有被誤導的人說...過去四年,我用你們允許我說的,盡可能強烈地發聲:對我的指控是錯誤的。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証據表明我有不當行為。” 除了向媒體發聲外,海波斯還在自己教會的“家庭會議”上,公開否認了這些指控,他的講話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 盡管海波斯試圖控制話語權,但一年后,一項強有力的第三方調查,得出了結論,這些女性一直在說實話,而且所發生的,不僅僅是曾經發生的性虐待,而且還在繼續發生中。該報告還指出了屬靈虐待。據說,海波斯有一種恐嚇和言語攻擊教會同工的模式。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就會“加大掌控力”。這種逆轉如此明確,以至於整個Willow Creek執事會最終也辭職了。 整個案件雖然悲慘,卻凸顯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現實:濫用職權的領袖採用侵略性且精心策劃的策略,來避免自己被曝光。這些策略也出現在全美各地的案例中,施虐的牧師似乎都在重復同一劇本。海波斯採取了一些最常見的策略,包括大量否認、召集一群捍衛者、攻擊指控者,以及讓自己成為一場陰謀劇中的受害者,那些指控者的目的是要毀掉他的名譽。簡而言之,施虐的牧師試圖通過“翻轉劇本”來保護自己。不幸的是,這些策略奏效了。 本章的目的是幫助教會理解這些策略,以便識別和解決問題。以下是施虐型領導者最常見的防御策略: 建立捍衛者聯盟施虐牧師的第一步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捍衛者聯盟,他們可以為他說話,為他辯護,甚至對受害者發起進攻。這個聯盟實際上成為了霸凌牧師的律師團隊,致力於不惜一切代價為他辯護。 聯盟的建立通常不是在提出指控的那一刻開始的。大多數霸凌牧師多年來一直都在建造聯盟,在執事會中與人建立關系,以防類似指控情況出現。雖然主任牧師與長老有親密關系是完全正常行為,但這些親密關系常被利用,使牧師在屬靈虐待的情況下免受問責。一旦指控曝光,幕后網絡就開始運作,牧師對所發生的事編織了自己的敘述。當受害者向執事會講述他們的故事時,這位施虐的牧師已經讓大多數長老反對他們。這也是很多受害者選擇離開的原因,因為牧師已控制了話語權,受害者意識到沒有希望對付霸凌牧師的策略。 一位虐待幸存者講述了他的故事: 起初,我試圖面對施虐者。后來沒有成功,我已來不及與朋友分享了,因為他先於我告訴他們,不要跟我說話,不要回復我的短信、電話或電子郵件。由於他強制要求人們對他忠誠,所以,即使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也不會跟我說話。我立刻就被孤立了。 施虐牧師建立捍衛者聯盟的能力,超出了他與這些人的個人關系。這也是因為他要求他們,做一些對他們來說,心理上更自然的事情。一般來說,人們更喜歡充當辯護者,而不是指控者,特別是在基督教背景下,尤其是代表牧師。因此,大多數長老或會友很快就成為牧師的積極捍衛者,甚至游說其他人加入這一保護牧師的事業,而很少有人成為受害者的支持者。畢竟,后者要求他們指控牧師,而那一位卻是被神呼召的領袖。這對大多數人來說,很難做到。防守是英雄行為,而指責卻有風險。 這整個場景再次提醒我們,教會中屬靈虐待問題遠遠超出了個別霸凌牧師的范圍。屬靈虐待得以繼續,是因為捍衛者自願保護並支持牧師。 堅稱沒有遵循適當流程在 1997 年的政治類電影《搖狗》中,羅伯特·德尼羅飾演的發言人康拉德·布裡恩,他描述了掌握話語權的最重要因素:“要改變故事,就改變主角。” 換句話說,讓主要問題是所指控的犯罪以外的事情。這是一個旨在翻轉劇本的舉動。 對辯護律師來說,他就是想要轉移大眾對委托人有罪的注意力,這是至關重要的。“改變領先地位”,是最常見的法律策略之一,就是提出大量程序性異議:沒有搜查令,沒有給予米蘭達權利,陪審團沒有收到適當的指示。不久之后,談話的焦點就不再是犯罪行為,而是程序。這正是被告想要的。 教會中的虐待案件也不例外。施虐的牧師經常大聲抱怨沒有遵循適當的程序,從而轉移人們對他們所做事情的注意力。他們如此大聲地反對,以至於他們開始看起來像受害者,而受虐待的人似乎是真正的肇事者。 在我研究的許多案例中,程序問題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虐待本身幾乎被遺忘,這並不罕見。人們感到不安,但並不是對牧師的虐待行為。相反,他們對在起訴過程中沒有遵循某些程序步驟而感到不安。在他們看來,受到虐待的是那位施虐的牧師;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通常,這些人對真正受害者的錯待並不關心。 當然,准確和公平的司法程序確實很重要,就像世界上的法庭一樣。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有人受到指控,我們必須確保他們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對待。但如果程序問題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牧師虐待本身被遺忘,我們應該感到擔憂。 在所有程序性反對意見中,其中一個被宣揚得最響亮:受害者沒有遵循馬太福音第 18 章,所以讓我們更充分地以批判的態度來審議。以下是該經文的段落: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隻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証,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太 18:15-17) 雖然馬太福音 18 章是處理會眾罪惡的重要章節,但並不詳盡,並不意味著能解決所有可能的情況。不幸的是,有時,它被視為可以適用於所有情況的萬能處方。以下要澄清幾個與虐待案件相關的重點: 首先,我們必須記住,馬太福音 18 章隻適用於那些被控犯罪的人,經文不僅說“如果你的兄弟犯罪”,而且還說“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你。”因此,這段經文並不適用於一個人指控另一個人犯罪的所有情況。例如,如果教會同工看到牧師虐待其他同工,他們沒有義務直接去找牧師,但可以直接向執事會報告牧師的不良行為。事實上,提摩太前書 5 章 19 節——“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証就不要收。”——意味著對牧師長老的此類指控可以直接提交給教會領導層。 可以理解的是,施虐的牧師很想阻止人們向執事會提出投訴。因此,牧師的辯護者或牧師本人經常會斥責投訴者,說:“你為什麼不按照馬太福音 18 章的要求,先去找牧師呢?”問題是,馬太福音 18 章並不適用於這種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幾節經文之后,耶穌給出了當一個人得罪另一個人時的例子:無情的仆人虐待欠他錢的人(太18:21-35)。當其他仆人注意到他的不良行為時,他們不會直接質問他。相反,經文說:“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31節)。主人沒有問:“你們有沒有親自去面質那個無情的仆人呢?”不,在這種情況下,該規則不適用。 其次,即使原告應該遵循馬太福音18章,但未能做到,這並不意味著執事會或其他管理機構就該忽視霸凌牧師的罪行。一些虐待牧師將《馬太福音》第 18 章視為米蘭達權利——如果不遵循技術程序,那麼,他們就無法因犯罪而受到起訴。但不遵守馬太福音 18 章,並不會給某人一張“免獄卡”。即使原告沒有遵循正確的步驟,教會仍該追究牧師虐待行為的責任。當然,原告未能遵循馬太福音 18 章的問題,也應該得到解決,但不應試圖將這兩個問題化為同一問題,好像未能遵循馬太福音 18 章,罪就等同於那個霸凌的牧羊人。 第三,即使原告遵循馬太福音第18章,並且施虐牧師承認了一些不當行為,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不應向教會領導層報告。一些牧師希望他們的受害者遵循馬太福音第 18 章,這樣,他們就可以通過快速道歉來“解決”問題,並在其他人不知情的狀況中繼續下去。換句話說,施虐的牧師有時會利用《馬太福音》第 18 章來讓受害者保持沉默,並隱藏他們的沖突記錄。 但有些行為確實足夠嚴重,以至於成員有理由向更高的領導機構報告,即使施虐的牧師似乎對此表示歉意。當然,這包括需要執法部門介入的公然犯罪行為。但有理由認為,成員也可以合理地舉報屬靈虐待行為:口頭攻擊、斥責或羞辱教會成員、威脅解雇員工等等。將此行為引起監督牧師事工負責人的關注,並不違反馬太福音 18 章。 第四,有些虐待案件非常嚴重,讓受害者私下與虐待牧師對峙是不負責任的。例如,如果一名牧師對一名女性同工進行性騷擾,用麥克奈特和巴林杰的話來說,堅持讓她與施暴者一對一會面是“不可原諒的,也是心理上的暴力”。 所實話,難道未信主的丈夫發現在妻子身上所發生的事后,會以《馬太福音》18.12 為由,將她強行帶回一個房間,與那性騷擾者單獨相處嗎?然而,在比爾·海波斯的案件中,女性受害者因不遵循馬太福音 18 章,不願和與海波斯私下會面而受到責備。 同樣的擔憂是否也適用於某些屬靈虐待案件呢?我想是這樣。再次,人們可以理解丈夫如何(正確地)拒絕讓妻子單獨會見一位口頭恐嚇和攻擊她的牧師。正如屬靈虐待專家麗莎·奧克利 (Lisa Oakley)解釋關於《馬太福音》第 18 章中所說,“當我們遇到屬靈虐待的情況時,就會出現權力的不匹配。事實上,一開始就試圖讓人們聚集在一個房間裡,這在其他形式的虐待情況中也是不該做的。 雖然界限並不總是清晰的,並且不可避免地存在可爭論的灰色地帶,但我們應該記住,馬太福音 18 章並不是適用於所有可想到的情況,也不是包羅萬象的處方。 重點是:如果牧師被指控有虐待行為,就要警惕程序問題是否會帶轉真正的目標,成為所有相關人員最關心的問題。 聲稱自己是誹謗的受害者如果一位牧師被指控屬靈虐待,他宣稱自己無罪,這並不奇怪,也並非不合適。事實上,他可能是無辜的。但那位牧師宣稱自己被誹謗,就完全不同了。這不僅僅是聲稱自己無罪;而且還強烈反控原告行事卑鄙,是罪惡行為。這是一種將自己變為受害者、將原告轉為問題的方式。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旨在翻轉腳本的策略。 在屬靈虐待的案件中,誹謗或八卦的反訴太常見了。一次又一次,霸凌牧師辯稱,這些原告者針對他而策劃的一場陰謀,他是被謀害的,是因為仇敵串謀,為了玷污他的好名聲。如前所述,海波斯在他的《芝加哥論壇報》採訪中提出了這一主張:“四年來,一直持續著這場對我和長老們有計劃的攻擊。” 邁克·科斯珀 (Mike Cosper) 在他的播客《火星山的興衰》中,注意到同樣的趨勢:“在沖突中的教會中,有一個明顯的模式,想要平息沖突的領袖,通過稱這一切為‘八卦’,並將那些分享此事的人貼上‘分裂’或‘狼’的標簽,以解決沖突。” 另一種策略是,濫用職權的領袖還利用誹謗一詞來搶佔先機。一些教會和組織制造了一種環境,就是任何人對領袖發表負面言論,都會被控為誹謗。換句話說,這些團體通過潛在的誹謗指控來威脅人們(無論是明確的,還是含蓄的),從而使人們保持沉默。這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創造了一種事工文化,使人們生活在恐懼之中;如果他們敢於發聲,就會受到嚴厲批評、指控或解雇。當拉維·撒迦利亞的一名團隊成員談論撒迦利亞令人不安的行為時,該人就因“散布謠言”而受到譴責。 這種恐懼讓人們保持沉默。在我研究的幾個屬靈虐待案例中,一位霸凌牧師虐待同工——甚至持續了很多年——但他們從來不知道其他同工也經歷著同樣的待遇。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情況隻是孤立案例。這種沉默的原因很明顯:如果他們對另一位同工談論主任牧師的負面言論,就有可能被指控為誹謗,並可能被解雇。所以,出於恐懼,他們都保持沉默。這使得虐待行為持續多年而不受制止。 教會或基督教組織如何才能避免創造這種使人不敢發聲的文化呢?首先,他們需要確保對誹謗有正確的定義。雖然這個術語經常被使用,卻經常被誤解。誹謗不僅僅是對另一個人說一些負面的話,而是明知是錯,卻仍然說出來(或至少不認為它有真實的根基)。換句話說,誹謗,涉及通過傳播有關他人的謊言,來損害他人聲譽,是有其惡意的企圖(撒母耳記下 10:3;列王紀上 21:13;箴言 6:16-19;16:28;詩篇 50:19 –20). 在這裡,我們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誹謗是一種非常嚴重的罪。說謊以污蔑他人,是主所憎惡的(箴 6:16)。這樣的謊言會毀掉一個人的名譽和事工。但是,說真話並不是誹謗,以適當的方式因牧師的虐待行為而發聲,也不是誹謗。 當被指控的牧師提出強烈的誹謗反訴時,就充滿了諷刺意味。如果沒有証據証明原告在撒謊,那麼,牧師本人就可能犯有誹謗罪。換句話說,牧師對不公正指控表示擔憂,可能在實際意義上,卻是對他人做不公正的指控。當牧師的辯護者重復聲稱,牧師被誹謗時——卻沒有任何証據表明指控者有惡意——那麼,他們也可能犯有誹謗罪。 現在,人們可能想知道,如果教會進行調查,並且霸凌牧師被無罪釋放,這意味著什麼。是否突然使最初的指控變成誹謗呢?一點也不。我們已注意到,要定一位牧師有屬靈虐待是多麼困難。所有的可能性都對指控者不利。畢竟,對史蒂夫·蒂米斯、詹姆斯·麥克唐納和比爾·海波斯的初步調查,都以某種形式的無罪為結果。因此,“無罪釋放”並不一定証明最初的指控是錯誤的,可能隻是意味著沒有足夠明確的証據,或者調查機構無法譴責自己的人。不管怎樣,如果受害者真誠地表達了他們的擔憂,就不涉及誹謗。 簡單介紹一下八卦一詞,它是誹謗的近親。兩者相似之處在於,都涉及負面報道。不過,雖然誹謗是假的,但流言蜚語卻可能是真的。八卦,並不一定是虛假信息,而是惡意分享這些信息,即損害一個人的聲譽、娛樂或刺激他人。 八卦,也是教會應該解決的嚴重之罪。但我們必須記住,並非所有負面報道都是八卦。一個人可能會毫無惡意地分享針對某人的負面信息。事實上,被虐待的受害者可能出於許多正當理由,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以獲得指導性建議,為他們所忍受的事得到咨詢和鼓勵,或者警告他人關於牧師的不良行為。最后一個原因尤其值得注意。人們甚至可能會說,教會成員有道德義務大聲說出牧師的不良行為,以保護其他會友免受傷害。當保羅警告他人關於銅匠亞歷山大的不良行為時,保羅似乎就是這樣做的:“你也要防備他,因為他極力敵擋了我們的話。”(提后書 4:15)。 其次,除了理解誹謗的定義之外,教會還需要誠實、公平地評估指控牧師虐待的可能性,以避免形成圍繞誹謗的恐懼文化。在一些教會中,人們對會眾抱有懷疑的態度,好像他們總是處於撒謊或對領導層提出錯誤指控的邊緣。最擔心的不是會眾可能被虐待,而是牧師會被霸凌。因此,當人們帶著擔憂站出來時,就有一種內在的傾向,認為這些人可能在撒謊,牧師需要得到信任和辯護。 但教會需要考慮這種內在的傾向是否合理。針對牧師的虛假虐待指控是否普遍存在?統計數據是否表明會眾容易在虐待問題上撒謊?我們掌握的所有指標都表明,答案是否定的。雖然沒有關於屬靈虐待指控的硬性統計數據,但性虐待案件中,虛假指控的比例徘徊在 2% 到 7% 之間。鑒於大多數虐待案件都沒有報告,實際比例可能還要低。如果這與屬靈虐待有相似之處——而且這兩種形式的虐待往往是相互聯系的——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虛假指控是一個統計上顯著的問題。 教會還需要考慮,當人們站出來,為屬靈虐待問題發聲時所付出的巨大代價。通常,他們不被相信,他們的品格受到攻擊和玷污,並被趕出他們所愛的教會(例子見第六章)。是什麼促使他們謊言指控?他們會得到什麼?他們常常會失去一切。 這並不意味著人們永遠不會在牧師是否虐待他人的問題上撒謊,當然有。當它確實發生時,應該格外認真對待。但我們不應該假設原告在撒謊。 現在,有人可能會說,除了撒謊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虛假指控。即使原告沒有說謊,他們的說法也可能是錯誤的。他們可能認為自己遭受了虐待,但實際上並沒有;他們可能隻是過於敏感的性格,導致他們夸大了所發生的事情。他們隻是把事情夸大了。 很公平。必須考慮這種重要的可能性,並且更需要進行獨立的第三方調查(更多內容將在第 7 章中介紹)。與此同時,有一個因素可以幫助澄清原告是否小題大做:是否有不止一名原告站出來?如果多人站出來講述類似的故事和指控,那麼,他們的可信度就會大大提高。很難想象,所有人都有同樣的傾向,喜歡夸大事實,並看到不存在的東西。那可能嗎?當然,這是可能的。但細想一下,大部分情況下,這有可能嗎?不會。 可悲的是,即使有多名目擊者站出來,也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被相信。在我研究的許多案例中,多名目擊者講述了同樣的欺凌和恐嚇故事。即便如此,教會領導層也不相信這些証詞。這些案例再次表明,起訴屬靈虐待是多麼困難。 攻擊受害者的性格在哈維·韋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2020 年性侵案審判期間,他的“羅威納犬”律師唐娜·羅圖諾 (Donna Rotunno) 的攻擊性策略很快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她沒有為韋恩斯坦辯護,花時間証明他是一個永遠不會做這些事的善良正派人,而是採取了一種老派的焦土方法:摧毀受害者的性格。在為期七周的審判中,她的策略是將受害者描繪成機會主義的操縱者,她們利用與韋恩斯坦的性行為來提升自己的事業。她對一名可憐的証人進行了九個小時的盤問,經常導致她在証人席上失控地哭泣。 她的信息很簡單:目擊者才是真正的肇事者,而不是韋恩斯坦。 同樣的防御策略是屬靈虐待案件中最常見的策略之一。施虐的牧師往往有自己的“律師”團隊,他們非常願意配合。在一個又一個的案例中,施虐的領袖將注意力轉移到指控者的所有性格缺陷或行為問題上。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旨在翻轉劇本的策略,而且很有效。虐待受害者常常不敢站出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在那些站出來的人身上會發生什麼,而那些過去發聲的人,生活已被毀了,他們不想落得和他們一樣的下場。 這種對受害者的人格攻擊以多種方式發生。首先,施虐的牧師可能會提起受害者過去的罪。既然每個人都是罪人,受虐待的人也落在罪中就不以為奇了。而且由於施虐牧師通常與受害者有著長期的關系,對他們的犯罪模式非常熟悉。除此之外,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施暴的教會經常迫使其成員公開承認他們最黑暗的罪。因此,施虐的領袖完全有能力,通過挖掘証人生活中的所有問題來進行報復。 正如我們在第 2 章中指出的那樣,我們有理由懷疑施虐牧師關於受害者罪行的說法。通常,施虐的牧師對一個人的罪的看法是錯誤的,或者至少夸大了這些罪。無論如何,這個策略仍然有效。由於害怕自己的罪被曝光,許多受害者根本避免站出來。通常,他們隻是離開教會,以避免尷尬,因為憤怒的主任牧師會無情報復。 其次,除了強調過去的罪之外,施虐的牧師還可能攻擊受害者處理沖突的方式。他可能會編造一個故事,將受害者描繪成無情、憤怒、鐵石心腸、不願和解的人,同時將自己描繪成一個伸出橄欖枝,卻屢遭拒絕的和平締造者。 這種陳述忽略了幾個因素:其一,當人們受虐時,可能會猛烈抨擊,或感到憤怒。是的,這種行為是有罪的,但這並不能否認牧師的虐待行為或免除他的責任。如果一個惡霸在學校欺負一個孩子幾個月,而那個孩子最終報復,整個事件的責任不會突然轉移。惡霸仍然要對這幾個月的虐待行為負責。 這是教會需要非常小心的地方。由於受害者所經歷的事,通常會出現“受害者表現出不合作、不信任、恐懼、憤怒和鐵石心腸的情況。”與此同時,施虐的領導者,在參與過程中,至少在表面上經常展現出合作和和解的態度。事實上,“他似乎明白了這一點,且正在努力改變。”這裡的危險在於,在一開始,可能會讓人看起來,施虐者是好人,而受害者是壞人。這往往會導致悲劇性的結果,“教會的支持和教牧關懷聚集在施虐者周圍,而施虐者[似乎]非常努力地想要和解。” 但之前關於虐待的研究表明,施虐者和受害者的這種外在認知,隻是一種表面上給人的感受,一旦施虐的領袖面對自己的罪行,並被要求悔改,他的合作精神往往會消失,而且很快會消失,他會開始猛烈抨擊那些追究他責任的人。此外,當受害者有時間和空間來治愈和康復時,他們自我防衛的牆往往會倒塌,他們會重新開始信任他人。 換句話說,隻要施虐的領袖不必承認真正的不當行為,就很樂意伸出橄欖枝。就像《指環王》中的薩魯曼一樣,他不會懊悔自己的行為,但仍堅持與受害者達成“和平”。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這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想要和解的好人,同時卻從不承認自己所造成的嚴重傷害。 第三,有時受害者被指控有受害人心理。在我讀到的許多証詞中,受害者被描述為太容易被牧師權柄的合法表達所冒犯和困擾。某些教會很會利用這一點,憤怒地指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心態對會眾的影響,於是,這裡的問題就不在於霸凌牧師,而在於“被現代世界影響”的會友過度敏感。 與這種策略密切相關的是,你不能相信受害者的証詞,因為他們的經歷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判斷。有人認為,他們是當局者迷,就會過於情緒化,因此証詞不可靠。如果挺身而出的受害者是女性,通常霸凌牧師會使用這種策略。對於一個有虐待行為的牧師來說,很容易讓一屋子的男性執事相信,女人不值得信任,因為她和所有女人一樣,太敏感,因此不可靠(當然不像他)。 這種反應除了嚴重缺乏愛和同情之外,更別提對女性的貶低了,而且還存在邏輯缺陷。其一,為什麼受虐者是唯一因個人經歷而影響判斷力的人?難道教會長老的個人經歷不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力嗎?個人教會經歷難道不會讓虐待行為更難被發現嗎?或者讓人相信這是極不可能的?而他們和主任牧師的友誼難道不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力嗎? 而且,我們永遠不會把這個論點應用到生活的其他領域。如果我們因堅持認為哈麗特·塔布曼的經歷影響了她的判斷,就會忽視了她和其他人的証詞,忽略他們曾經遭受令人難以置信的、如奴隸般被虐待的事實,這又該怎麼辦呢?我們真的會認為她容易夸大其詞,因為她是當局者迷而過於情緒化——可能是因為她是個女人?我希望不是。 第四,有虐待行為的牧師捏造針對受害者的指控,以便讓自己看起來更好,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在我讀到的西南部一個教會的証詞中,一位虐待牧師,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調查,散布針對一位長老和他妻子的謊言,告訴成員,他們試圖把他趕走,這樣他們的兒子就可以成為新牧師。對此類宣稱卻沒有証據,完全是捏造。但願虐待案件中這種徹頭徹尾的謊言很少見,但我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中卻看到了這種行為。 這種誹謗受害者品格的策略令人深感不安,之所以它們被使用,是因為有效。悲劇在於,一些教會允許對虐待受害者提出此類反指控,使他們暴露在外,得不到保護。這應該引起基督教領袖的認真反省。 宣傳自己的優良品格和成就施暴的領袖不僅非常願意攻擊受害者的品格,而且還試圖吹噓自己的品格和成就。在這一點,宣傳個人為祝福教會所做的一切:他忠誠地工作了二十年,建立了許多教會,他指導了無數的年輕牧師,一直是教派的忠實成員...。簡而言之,施虐的牧師想要展示他們(經過精心編輯的)簡歷。 這一策略的特點是:讓施虐的牧師獲得優良品格推薦書。他或他的支持者可能會組織一場活動,收集多年來他所祝福之人的書面聲明,解釋他是一位多麼出色、善良和慷慨的牧師——如何幫助他們度過困難時期,給他們提供很好的建議,或者他是一個特別有愛心的牧羊人。 所有這些証據都是為了在執事會或其他裁決機構的頭腦中造成認知失調。一個為神國做出如此多善事,或幫助過如此多人的牧者,怎麼會與在教會中虐待和霸凌會友是同類人呢?為了解決這種認知失調,人們默認這些指控不可能是真的。這是霸凌牧師翻轉劇本的另一種策略,讓人相信,他們才是值得信賴的人,而不是受害者。 大多數教會沒有意識到,事工成就和品格評價並不是牧師是否施虐的決定因素。事實上,任何做事工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基督教領袖都可以宣揚自己的成就,並找到因他的事工而蒙福的人。事實上,有多少當地牧師能夠與拉維·撒迦利亞這樣的人的成就並駕齊驅呢?或者比爾·海波斯?或者馬克·德裡斯科爾?然而他們都是虐待者。 正如第四章所指出的,施虐的牧師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通常是溫暖、關懷和可愛的。另一個是嚴厲、冷酷、殘酷。大多數人隻看到了霸凌牧師好的一面。因此,這樣的人可能被人大量吹捧,並不足為奇。但這不代表他沒有虐待行為。 打同情牌盡管屬靈虐待的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下一章將詳細討論這個主題),霸凌領袖的一個策略是:談論他們所遭受的痛苦。他們會不遺余力地描述,由於與指控者之間未解決的“沖突”,他們感到多麼痛苦。他們會講述自己如何失眠、焦慮不安,並對整個事件感到“深感悲痛”。 甚至薩魯曼也想談論“對我造成的傷害”。此舉旨在引起人們的注意,讓他們同情的不是受害者,而是施虐者。再說一遍,此目的是翻轉劇本。 為了博得更多同情,一些施虐的領袖會訴諸整個情況對他們的配偶或家庭的影響。他們可能會指出他們的妻子遭受了多少痛苦,或者他們的孩子是多麼心碎和幻滅。這種策略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我們會對受到丑聞傷害的家庭成員表示同情。通常,配偶和孩子並不知道牧師如何虐待他人(盡管有些配偶支持並捍衛丈夫的虐待行為,有時甚至參與他的欺騙)。事實上,一些教會法庭不太願意起訴這樣的牧師,因為他們為他的家人感到難過,他們“已經受夠苦了”。 但對家庭的同情不應減少追究施虐牧師責任,正是他的行為,而不是受害者的,給他自己的家人帶來了痛苦。他不應該責怪別人,而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結論 盡管屬靈虐待的案例多種多樣,但施虐的領導者常常遵循相同的組織良好的劇本來保護自己。本章的目的是描述和回應此劇本中的每一步,以便教會能夠更好地保護其會眾,特別是那些有勇氣站出來講述事實的受害者。 不幸的是,並非所有教會都理解我們討論的策略,因此許多受害者仍未受保護。他們不僅受到牧師的虐待,而且反過來,他們的教會也不相信或保護他們。他們遭受著兩次虐待,常常造成悲慘的后果。下一章將探討這些不同的影響,以便教會能夠更好地認識到,如果不追究霸凌牧師的責任,以及可能會造成的損害。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