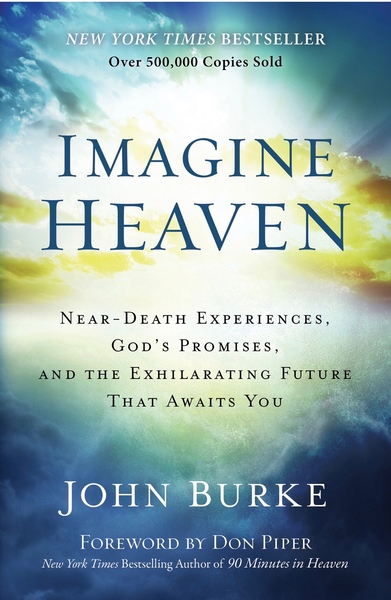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06/10 10:21:19瀏覽562|回應0|推薦0 | |
想象天堂摘錄24 約翰·伯克/白帆譯 第16 章 地獄是什麼樣呢?北肯塔基大學藝術教授霍華德·斯托姆在帶學生參觀巴黎博物館時,患了急性胃潰瘍,致使十二指腸穿孔。他當時並不知道,從穿孔那一刻起,他的預期壽命大約只有五個小時。那個周末,醫院只有一名外科醫生值班,他和妻子貝弗利不得不等著急救。十個小時后,一名護士通知他們,醫生已經回家了,他們必須等到第二天早上。雖然霍華德一直努力地讓自己活下去,但現在已希望渺茫。霍華德在一次獨家採訪中,與我分享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祈禱,從來沒有想過神。我認為死后沒有生命,所以,當我想到自己要死了……確實非常害怕,因為這意味著我的一切都將“結束”。我告訴妻子:“我們該說再見了。”我讓她告訴我的父母,我愛他們,告訴孩子,我愛他們,告訴我的朋友,我想念他們,我說:“最后,親親我吧!我們再見了。”她吻了我,跟我道別,我也跟她道別,她坐下來哭了,我從不知道一個人能哭成像個淚人那樣……看到她很痛苦,我覺得很難過,只想快點離開,盡早結束這一切…… 霍華德閉上眼睛,離開這個世界。他期待自己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他發現自己卻站在床邊。他睜開了眼睛。 我感覺比我在一生中任何時候都更有活力…… “為什麼我感覺這麼好?”我只是感受到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刻,然后沒了呼吸,現在,我就像超人一樣...我的視力、聽覺、味覺...我周邊的視野在擴展,我可以看到很遠的天際,不受任何限制。我是一名藝術家,所以非常了解視覺方面的事...。於是,我試著跟妻子說話,她躺在床的另一邊,雙手抱頭,彎著腰,但她沒有反應。所以,我開始對她大喊大叫,因為她沒理睬我。我喊著,叫著,甚至罵她,但她還是沒有任何反應。於是,我轉向弗勒林先生(隔壁病床上的病人,他對我們非常好),我對他也大喊大叫,我的臉離他只有幾英寸,他只是盯著我看,好像看不到我,當然,他的確看不到我。 此時,霍華德仍沒有意識到自己真的死了。雖然他認出自己毫無生氣的身體,但還是感覺自己還活著。他此時唯一的想法是,他到底有多需要做手術。 我聽到人們用英語叫我,有點客氣,你知道嗎?“霍華德,霍華德。過來,過來。”於是,我走到房間門口,走廊是灰色的,模模糊糊,有點像從老舊的黑白電視中出來的畫面……一些男男女女站在離門口燈光很遠的地方。我說:“我病了,需要做手術。我等了一整天都沒有醫生來。”他們說:“我們知道你的一切。快點,現在跟我們來。我們不能再等了。快來,快點!”我在想:“好吧。他們來,大概就是來帶我去看醫生。太好了!我需要做手術。” 當我離開房間的亮光,走進走廊時,那些人就圍著我,開始帶我往一個方向走。起初,我以為我在醫院裡,但是,當我們在這些人的簇擁下,走在灰暗的路上時,我意識到,這家醫院並沒這麼大,因為我們已經走了好幾英裡……隨著光線越來越暗,他們也越來越靠近我。剛開始,他們離我比較遠,我看不到他們。我所能看到的只是……短袖 V 字襯衫,沒有裝飾的休閑褲。他們看起來和醫院工作人員一模一樣…… 此時,我問他們:“我們要去哪裡?還要走多遠?...”,他們開始變得粗魯,對我說:“閉嘴!別問了!你會知道的!你不需要知道!繼續往前走!繼續!往前走!”我開始變得有些畏懼,漸漸地,我開始害怕,然后我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恐懼。此時,我們已經走了無數英裡,四處昏暗,我意識到,我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是那種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我想:“我受夠了”,下定決心:“我無法再忍受了!”我反抗說:“我不能再走啦”。他們回答說:“這由不得你,你必須走,繼續往前走!”我拒絕說:“我絕不走!”。於是,他們開始拉扯我、推揉我。高中時,我曾踢過美式足球,也參加過摔跤比賽,所以,我知道該怎麼打比賽...。我試圖拳打腳踢來抵擋他們。但他們還是拉扯我,而且他們有很多人...我從聲音和接觸的身體來判斷...他們大概有幾十個,幾百個...也許更多。他們所做的就是戲弄我,羞辱我。 起初,他們推我、踢我、擊打我。然后,他們開始咬我,用手爪的指甲挖我、撕我,將我的身體肌膚撕扯得血肉模糊,他們還放聲大笑,說許多粗話。他們變得越來越殘暴,更具侵略性…… 這時,霍華德在採訪中不得不停頓一下,以抵抗那些痛苦的回憶,他后來告訴我,他花了很多年試圖忘記那些記憶: 我不能再說下去,因為這太侮辱人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再談論這件事。從來沒有一部恐怖電影或一本書可以描述他們的殘忍,因為他們很殘暴……純粹是虐待狂……他們是那麼冷酷無情,對我毫無同情心或憐憫,他們使我尖叫、大喊和反擊,只是為了取樂。而且,我越沒有力量和能力反擊,他們對我就越不感興趣。最終,我被毀了…… 。我失去了一只眼睛,耳朵也被挖掉了,我躺在地板上。而且,我只想說,他們對我所做的事,以及帶給我情感痛苦,比身體上的痛更糟糕。我身體上的痛,是從頭疼到腳;是實實在在的、可怕的、劇烈的疼痛。若以 1 到 10 的等級來衡量,我的疼痛絕對是:10 分。但這與我內心的感受無法比擬……我已被拖入絕境。我的意思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之事都發生在我身上,而且沒有任何原因…… 在那個地方,我聽到了一個聲音,我認出那是我的聲音,並不是從喉嚨裡發出來的……很奇怪,我覺得那聲音是從我的胸腔裡蹦出來的,說:“向神禱告”,我想:“我不相信神。我不禱告。” 這個聲音堅定地說:“向神禱告”,我想:“我甚至不知道如何禱告。即使我想禱告,但也不會呀! ” 那聲音又說:“向..神...禱告!”我想:“小時候,我曾經去過主日學,我們學過禱告,那是什麼來著?” 霍華德努力回憶童年時的禱告,以及任何有神名字的東西,他極力拼湊起所有能回憶起的,最后拼成一個絕望的禱告,他大聲喊道: “是的,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在紫色的山峰上,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了主降臨的榮耀...在神之下的一個國家,神祝福美國。” 令我驚訝的是,那些殘忍無情的畜生被我破碎的禱告給激怒了,他們撕扯著我的生命體,好像我在他們身上潑了滾燙的油一樣。他們對我尖叫著:“沒有神!...沒有人能聽到你的聲音!現在,我們真要狠狠地揍你了。”他們用最淫穢的語言罵著,比地上任何褻瀆的話都要臟。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往后退... 此時,我更想禱告,因為這是我對他們能做的第一次反擊。我更大聲禱告,幾乎震耳欲聾。我還注意到,我越是不停地禱告,越是試圖表達任何與“神”有關的話,比如“榮耀,榮耀,哈利路亞!祂的真理繼續前進”,他們就越是往后退縮。 當那些小鬼們退后,霍華德絕望地躺在地上,思考著自己的處境。他感到完全孤獨,幾乎被摧毀,但在那恐怖、可怕的地方,他卻痛苦地活著,且意識敏銳。 所以,現在,我有永恆的時間——無限的時間——來思考我的處境...由於我對宗教或神學一無所知,我不得不用自己能想到的唯一方式來描述我的處境:化糞池系統...因為我活在垃圾堆中,所以我被沖進馬桶,掉進了化糞池...,我才意識到,這是可怕的:那些遇見我的人,與我臭味相投。現在,我不知道在這次遭遇前,自己是否在世上認識那些人...但他們是我精神上的兄弟姐妹。他們否認上帝,為自己而活,他們的生活就是操縱和控制他人。這是他們的動力和動機,是他們真正為之而活的一切。 我一生都致力於大老我的建造了,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紀念碑。我的家人、我的雕塑、我的繪畫……所有這些此刻都消失了,這些紀念碑還有什麼意義呢?我離永遠成為自我折磨的人不遠了。 當霍華德獨自躺在黑暗中,感覺自己正陷入絕望時,一首他幼時曾聽過的歌詞浮現在腦海。他只記得幾個詞,“耶穌愛我”,還有那首歌的曲調,深深地觸動了他心中的渴望,點燃了一絲希望的火花。 此刻間,這就是我擁有的一切。我一無所有,正竭盡全力……我想,耶穌為什麼要關心我?即使祂是真實的,但祂為什麼在乎我?祂一定恨我。我很后悔。我想,夠了!我受夠了!我什麼也沒有。我希望耶穌真的愛我……我對著黑暗大喊:“耶穌,救救我吧!”我一生中從未有過如此強烈的感受。 當我說出那句話時,我看到了一道光、一個小小的光點,迅速變得非常明亮,籠罩著我。我從光中看到:一只手掌和手臂,從那道美得不可思議的光中伸出……如此強烈,比太陽還要明亮……那手掌和手臂伸出來,觸摸著我。當我被觸摸時,在那道光芒中,我可以看到自己身上血跡斑斑,仿佛被殺死在路上,但那血跡開始消融,我破碎的身體被痊愈了。 對我來說,比身體上的治愈更重要的是,我經歷了一種遠遠超越語言能描述的愛,我完全無法表達這種愛,但我可以說,如果我把一生中所經歷的愛濃縮成一個瞬間,仍無法與我所感受到的愛之強度相提並論。從那一刻起,這份愛就是我生命的基石...。 那手臂擁抱我,治愈我,在我身后,祂把我抱起來,好像沒有費什麼力氣。祂只是輕輕地把我抱起來,緊緊地抱住我,讓我靠在祂的胸前。我就在祂的懷裡:我摟著祂,祂摟著我。我像個嬰兒一樣嚎啕大哭。我把頭埋在祂的胸口,流著口水、鼻涕。祂開始揉我的背,就像爸爸、媽媽抱著孩子一樣。我知道,我不知道我怎麼知道的,但我知道祂非常愛我,不管我當時是什麼樣子。耶穌確實愛我……我呼喚耶穌,祂就來救我。我哭了又哭……心中充滿了喜悅。 祂抱著我,往天上升去,一直往上升。我想看看,我們要去哪裡,我意識到,我們飛移得非常快,因為有五顏六色的光……光之生命從我們身邊飛速而過。而且,我只能通過祂的光芒——榮耀——看到我們正在飛離。一切都在以極快的速度前進,遠處是這個……巨大的光之中心,一個超出感知范圍的光之世界……比星系還要大……當我看向這巨大的光之中心 [我知道] ……那是神的家,那就是天堂。 地獄般的瀕死體驗當他望向太空遠處那座偉大的光之城時,霍華德說,他在耶穌和幾位天使的面前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我們將在下一章中探討這一點。霍華德奇跡般地復活了,幾年后,他放棄了大學教授和藝術系主任的職業,成為一名牧師。是什麼促使一位公開宣稱無神論的教授,放棄終身教授職位和一生的事業,編造了一個走訪地獄的故事呢?如果這是唯一的瀕死體驗故事,我們可以一筆勾銷他的說法,但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當瀕死體驗報告不斷增加時,很少有人站出來講述自己經歷過地獄般的瀕死體驗。事實上,穆迪大膽地表示,“沒有人描述過漫畫家筆下的天堂,珍珠門、黃金街道……也沒有畫出地獄的火焰和手持干叉的惡魔。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人死后的獎懲模式被拋棄和否定。” 但穆迪的聲明被過分強調,言辭過早了。 荷蘭研究員皮姆·范·洛梅爾博士指出,經歷過地獄般瀕死體驗的人,有時會發現自己被拉入越來越深的黑暗之中。“瀕死體驗在這種可怕的氛圍中結束……如此可怕的瀕死體驗通常會產生持久的情感創傷。”經歷過這種通常被稱為“地獄體驗”的瀕死體驗的確切人數尚不清楚,因為正如范·洛梅爾所注意到的,羞恥和內疚阻止人們分享這些可怕的經歷。 薩托裡指出,“[研究] 強調了負面的瀕死體驗與愉快的瀕死體驗一樣真實,並且可能在沒有麻醉劑的情況下發生”。有些研究沒有產生令人痛苦的瀕死體驗,但這可能與研究的實施方式有關。研究要求人們說出他們是否經歷過瀕死體驗,這會讓人們興奮地向他人講述一段美好經歷。另一方面,經歷過負面瀕死體驗的人可能會感到尷尬或羞愧,因此不太可能分享他們的故事。許多這樣的人向霍華德·斯托姆吐露心聲,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和他在一起,有一種同志情誼和安全感,因為他也經歷過負面的瀕死體驗。 斯托姆認為,這些負面的瀕死體驗故事並不罕見,但因羞恥感而不太可能常被分享。 地獄般的瀕死體驗頻率盡管如此,《瀕死體驗手冊》報告稱,有 12 項研究,涉及 1,369 名受試者,發現23% 的人“報告了從令人不安到恐懼或絕望的瀕死體驗”。洛林博士是第 3 章中的心臟病專家,他救活了一位經歷了多次地獄般經歷的患者,但患者事后無法回憶起這些經歷。洛林推測,這些經歷會產生如此大的創傷,以至於被壓抑在潛意識中,除非患者在復蘇后立即接受採訪,否則我們不應該指望會有這麼多的敘述出現。洛林引用了其他醫生的報告,記載了類似記憶阻塞反應。 一名十四歲女孩對自己的生命感到沮喪,並決定結束它。她吞下了一瓶阿司匹林。在醫院裡,醫生報告說,他對心臟驟停的她進行了搶救,在此期間,她不停地說:“媽媽,救救我!讓他們放開我!他們想傷害我!”醫生試圖為傷害她而道歉,但她說不是醫生在傷害她,“是他們,那些地獄裡的惡魔……他們不肯放開我……這太可怕了!”醫生說,“她又睡了一天,她媽媽大部分時間都抱著她。拔掉各種管子后,我讓她回憶一下發生了什麼。她記得吃了阿司匹林,但其他什麼都不記得了!在她的腦海裡,這些記憶可能仍被壓抑著……幾年后,她成為了一名宣教士。 同樣,在其他文化中,並不是所有的瀕死體驗都是愉快的。在印度,亞姆杜茨被認為是像天使一樣的“信使”。亞姆杜茨應該出現在垂死者的床邊,把他們帶到他們的主雅瑪拉吉 [死亡之神] 身邊。亞姆杜茨的出現取決於病人的業力。如果他積累了善行,就會出現一個令人愉快的亞姆杜茨,但如果他在一生中沒有很好地表現自己,就會出現一個可怕的亞姆杜茨。 一名印度教神職人員說,“有人站在那裡!他帶著一輛手推車,所以,他一定是個亞姆杜茨!他肯定是帶著別人一起去的。他在逗我,說他要帶我走!……請抱緊我,我不走。”他的痛苦加劇,最后死去了。 奧西斯和哈拉爾鬆報告說,“三分之一(34%)的印度人經歷了魂游向外的幻覺,他們拒絕承認 [害怕亞姆杜茨來帶走他們]。”研究人員將已記錄下的許多“地獄”描述,分為三類,我稱之為“虛空”、“人間地獄”和“深淵”。 虛空一些瀕死體驗者發現自己離開了自己的身體,要麼進入虛空,就像他們在外太空的某個地方,要麼在外面的黑暗中體驗到墜落的感覺。加裡是一位年輕的藝術家,在一個雪夜裡,汽車失控。他描述自己離開身體,看著冰冷的水灌滿汽車的情景。 我看到救護車來了,看到人們試圖幫助我,把我從車裡救出來,送到醫院。那時,我已經不再在我的身體裡了。我已經離開身體,可能在事故發生地以南一百或兩百英尺的地方,我感受到了那些試圖幫助我的人,他們的溫暖和善意。……也感受到所有善意的源頭,非常非常強大,我害怕它,就沒有接受它。我只是說“不”。我對此非常不確定,我感到不舒服,所以拒絕它。就在那一刻,我離開了地球。我能感覺到自己,看到自己,飛向高空,然后超越太陽系、銀河系,超越任何物質。……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我沒有感覺,沒有知覺,無法見到光,我感覺難以忍受,開始恐懼,開始驚慌失措、掙扎、祈禱,我用盡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努力,只想往回走。 有些人拒絕神的愛和光,或者像 A. J. 艾爾 一樣,他們覺得光明很痛苦,想抵抗它。有人只是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可怕的空虛之中;有人則經歷了一種外部黑暗,常常伴隨著一種墜落的感覺。我的朋友保羅·奧赫達死於可卡因過量,他發現自己突然清醒了,但處於一種從未預料到的境地。他向我解釋所發生的事情: 當我死的時候,我沒有看到光,卻看到了一條黑色的隧道,就像有人把我扔進了一片黑暗中,我正在自由落體,意識到自己不再興奮了。我身處一個不同的地方,有一種不同的時間感,但我正迅速陷入其中,我想,我是個好人,不應該來這裡。但什麼也無法阻止這種墜落,我意識到自己要下地獄了,出不來了。於是,我大喊道:“主啊,我不想去那個地方,請救救我。” 我沒有看到一張臉或一個身影,只是感覺到主在我身邊,祂在我的靈魂裡問道:“保羅,你對我給你的生命做了什麼?” 保羅看到了自己從出生到三十歲(他當時的年齡)的整個人生,神揭示了他內心隱藏的每一個秘密,除了他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對神說:“我意識到,我這一生什麼都沒做。我知道自己活該下地獄,但我知道,這不是我的命定。如果你給我機會,我會回去告訴別人,地獄是真的。” 他在醫院醒來,第一句話就是:“我看到了地獄,我不會再回去了。我想找到把自己從地獄裡拉出來的神。”幾年后,保羅最終離開了他創辦的一家利潤豐厚的企業,而去建立了一個教會,為奧斯汀的西班牙裔社區服務。保羅和許多人是否經歷過各種“黑暗的鎖鏈”(彼得后書 2:4)或聖經中警告的“無底深淵”呢(啟示錄 9:1 NLT)? 人間地獄像霍華德·斯托姆一樣,喬治·裡奇在第一章中觀察到了某種程度的人間地獄。喬治聲稱,耶穌帶他參觀了似乎是“地獄”的“層次”。祂向他展示了在地上城市工廠做工的人們,一個人站在另一個人旁邊對他大喊大叫。一群婦女站著抽煙,其中一個婦女在乞討香煙。當一個女人拿出一支煙點燃時,乞討的女人如餓狼般地過來搶,但她的手直接穿過,卻沒能搶到煙頭。然后,他看到一個男人走在街上,他已故的母親就在他身邊,追問他為什麼要娶瑪喬麗,告訴他要更好地照顧自己。已故的人永遠向活著的人隱藏不見了,但活著的人卻永遠忙於自己的事務。一句話沖擊著裡奇的心:“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他回憶道: 我從來都不擅長背誦聖經,但耶穌在登山寶訓中的那些話現在像電擊一樣涌入我的腦海。也許那些虛無縹緲的人——商人、乞討香煙的女人、那位母親——雖然他們再也無法與地上的人們溝通,但他們的心仍然在那裡。我呢?……在永恆裡,那些他們無法停止渴望的東西永遠與他們隔絕了……那肯定是一種地獄…… 但如果這是地獄,如果沒有希望,那為什麼[耶穌]會在我身邊?為什麼每次我轉向祂時,我的心都會歡喜雀躍?……無論我怎麼看,祂都是我真正關注的焦點。無論我看到什麼,都無法與祂相比。 這也是讓我困惑的另一件事。如果我能看到祂,為什麼其他人都看不到?……他們怎麼會看不到他們中間燃燒的愛與同情?他們怎麼會錯過比正午的太陽更近、更燦爛的祂呢? 除非…… 我第一次想到,十一歲時,我走向教堂的祭壇,那天是否發生了一件比我想象更為重要的事情。我是否真的像牧師說的那樣“重生”了——獲得了新的眼睛——不管我是否理解其中的含義?……“你的心在哪裡……”只要我一想到那個來到瑞其滿城市,我就看不到耶穌。也許,每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時,我們甚至會忽略祂。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