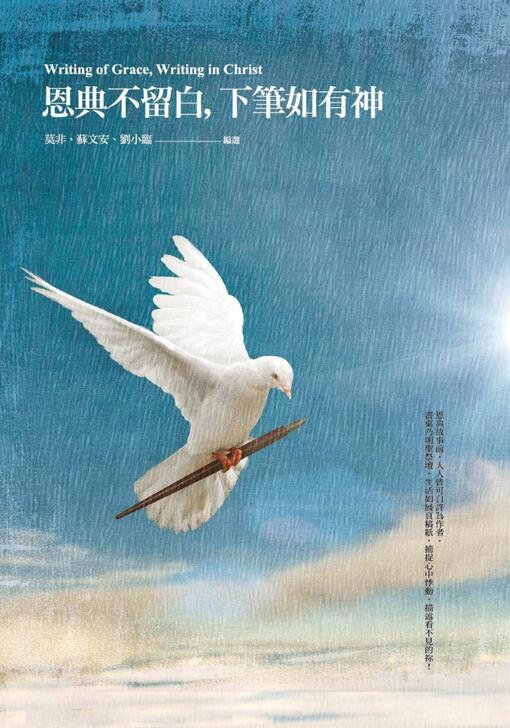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10/19 14:19:37瀏覽773|回應0|推薦4 | |
你渴望被尊重嗎?這是小說主人公一直的渴望,但從小他就沒得到過。千帆盡過後,在一個白雪皚皚的冬日,他終於迎來了心中所望。 獻詞 我尊敬任何一個獨立的靈魂。 ——德國哲學家 康得 與其說生活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不如說它是一個有待發掘的奧秘。這正是聖經的立場:生活不是我們一起用鐵鎚敲敲打打、動腦筋不斷修理的東西;生活是一份深不可測的禮物。 ——法國哲學家 嘉伯烈·馬塞(Gabriel Marcel) 引子 每個人都有自己微不足道的乳名,首先它屬於母親,或許永遠屬於她。我的母親無論何時何地,也不管我成年與否,從來只喚我一個字,而且是用她那濃濃的山東鄉音淋漓盡致地呼喚「方——」 小時候這呼喚常常從南到北地迴盪在生就了我的那條街上。 我不敢想像這呼喚對於母親意味著什麼,然而這微不足道的一個字卻喚在我心靈的最深處。雖然母親早已睡去,而那呼喚至今還迴腸九曲,滋味之濃百思不得窮盡。 綽號 我生在北方一條遠離大自然的淺街陋巷裡,左鄰右舍比鄰而居,擁擠在兩趟狹窄的平房、若干個小門之內。家家除去可供躺臥的土炕和不可或缺的爐灶之外,幾乎再無空間,誰家也甭想有什麼高貴的隱私;鄰里之間常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惡眼相看。 不知為什麼,我家那條街上很多人都有綽號,這或許是國人一種別有情調的幽默,非把好端端的人形容得豬狗不如而後快。綽號雖是送給某個人的,卻映照著所有相關的人。 我家斜對面住著的一家人被喚作「大褲襠」,可能是那條街上最窮的,不但家徒四壁,家庭主婦還患精神病,經常在街上拿著菜刀鬧起來。也許是裝出來嚇唬人的也未可知,因為他家常被鄰舍歧視欺負,若沒有點裝神弄鬼的伎倆,實在難以棲身立足。歪瓜裂棗的四五個孩子缺衣少食。「掌櫃的」(當時常這樣稱呼一家的戶主,大概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恭維稱謂)冬天穿一條粗布大棉褲,絕無內衣,是當時北方農民最傳統的服飾;肥大的棉褲腰足以裝進兩個人,往腰裡一折一挽,繫一條髒污的布腰帶,褲襠豈能不大?且冬夏鼻涕拉瞎(編注:東北方言,指人臉不乾淨的樣子)。也許是因生活的重負,愁苦和驚慌失措好像刻在他臉上,連笑也像哭。
他的孩子們也難逃厄運,如同那個年代的政治成分,綽號是要繼承的,一家人從小到大無論男孩女孩都被以此號稱呼,或被喚作「大褲襠」家的老幾——多年後人都沒了,這綽號還在人的「口碑」裡。 我家左鄰的小院子裡,住著以掌鞋為生的「張破鞋」,舉家與破鞋同居。難以想像,一間小屋裡,炕上地上擺滿了破鞋和掌鞋的家什,如何還能容納得下老婆孩子五六口人?「張破鞋」自己也穿著翻著「舌頭」沒有鞋帶,大概是抗美援朝時期的軍用破大頭鞋。一頭亂髮就像麻繩子,黯淡無光的眼角總有眵目糊(編注:東北方言,眼),謀生的職業成了盡人皆知的代號,卻沒人知道他姓甚名誰。 「張破鞋」卻另有一個至高的樂趣,就是拖著七扭八歪的破鞋去蹲棋攤兒。他好像剛從鞋堆裡逃出來,再也不想回去似的,夏日常與人對弈至深夜。當這盤棋他必死無疑的時候,便被人戲笑:「快回家,掌你的破鞋去吧。」但他好像在叫不醒的夢裡,只是看著殘局不動聲色。那專注淡然的樣子,好像使他忽然人格昇華,有一種令人刮目相看的尊嚴。大概那是他最享受的時刻,早已忘記「破鞋」與自己的任何關係。 兀自抗衡 當我長到能在街上跑,常被母親喚回的時候,那個似乎理當屬於我的綽號便臨到了我。母親幼年攀樹失足,窮鄉僻壤無醫無藥,以致右腿膝蓋處竟結出一個大大的如樹癤般的疤痕,令人觸目驚心。母親就是拖著這樣一條殘疾的腿把我拉扯大。在我心目中,並不認為那是跛,因為那是母親十分真切的一部分,便永遠融合在母親給兒子的美感之中不能更改。 這似乎是很簡單的分歧,但也因為這簡單的分歧,讓我一生不敢與人苟同,總是被迫另闢蹊徑,甚而與一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兀自抗衡。 那個臨到我的綽號,刺透了我兒時愛之所繫的全部——父姓母跛,冠在兒子頭上曰「李瘸子」。 夏天,一到傍晚,我家門前便跑滿了不知出於何種衝動,到處撒野的半大孩子。被喚作「二孬」和「狗丟兒」的孩子與我同齡,鬼頭鬼腦地呼嘯而來,看見母親在喚我,也學著母親的山東腔喚起我來,而且學著母親的跛行在我面前嬉戲而去,興奮異常。 這也許是無須大驚小怪的兒戲,卻是我幼稚心靈遭到的第一次重創,那一剎那宣告了我平靜如小溪,剛剛到來的金色童年戛然而止。 從此這個極具侮辱蔑視的綽號,在我的心裡就近乎水乳交融的無伴奏和聲,襯托在母親的呼喚裡,令我面對尚未開始的人生竟有一種他鄉異客的驚詫。 頭型 儘管我已經背上書包,上了似乎應該講體面的學堂,但到了該理髮的時候,仍是由母親像補補丁、洗蘿蔔一樣,用自家的大剪刀從容地為我理髮。於是我的頭上便滿了絕無規則,像梯田似的痕跡,頭頂成了無法交待的房蓋兒。每次,她用粗大的手所剃的,分明是我的自尊。而我越是委屈,母親竟越是擺弄著我的頭,看著我的樣子發笑;她又好像是在笑自己,儘管盡了最大的努力,還是糟糕得不可收拾。 然而母親這一舉動完全不顧惜我的體面,想都不想,就在我無法掩飾的頭上為我造型,而且忍心讓我硬著脖頸招搖過市,令我飽嘗了欲哭無淚的貧窮帶來的羞辱。
這別具一格的頭型所遭到的嘲笑,沉澱在我心裡,竟讓我漸漸領受了一種被迫的思維定式,成了母親自行其是、我行我素且自鳴得意之饋贈。 當時那強加於我的頭型,不僅在我頭上,還連同那綽號一起扭曲了我的心,於是我幼稚的心靈便開始了一場悖逆而漫長的跋涉。 木訥與羞慚 首先我沒有了活潑,成了一個訥於表達的孩子。 開學前一天,學校新刷的黃色院牆上貼出了招生榜,平日「人模狗樣」的孩子們此時伸長了脖頸,都變了樣子。我的大名被寫在上面,這是我第一次與我的大名相晤,非母親平日所喚,讓我感到一種朦朦朧朧的甦醒。 那天下著毛毛雨,天上有五顏六色的虹,我家那條街也有一種從未有過的祥和。下午去文具店買幾樣紙筆,竟無言地和隔著幾家的鄰居,平日只知道叫「大嘴兒」,那日方知叫「歐蘋」的女孩兒一起打一把雨傘。這微妙的不約而同,似乎為我敞開一個嶄新的天地,然而這嶄新的感覺卻很短暫。 儘管童心未泯,也不免心靈的蒼白,天真的年齡並不單純。不知繼承自何種優良傳統,所有男生都不屑於和女生說話,否則便是卑鄙或莫大的羞恥。 我儘管訥於言,也不免禍事臨頭。一天放學後,不知是哪個淘氣的同學揪了「大班長」的辮子;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她的家長竟找到我家來興師問罪,讓我有口難辯,羞辱不堪。 不是不想辯白,是辯白不出,嘴笨拙,又不會強詞奪理。話還沒出口,便囫圇咽下去自行消化了。母親也常說我的嘴像棉褲腰。 被揪辮子的「大班長」是班上唯一受過學齡前教育的女孩,居然會唱童謠:」小板凳呀排一排,小火車呀開起來,小朋友們坐上來,鳴鳴鳴,鳴......」唱得許多同學目瞪口呆。 或許她是因為天真快樂,總在老師面前蹦蹦跳跳,才引起一些以惡作劇為榮的窮孩子嫉恨;我似乎是更有甚者,看見與我隔絕的美麗活潑,便生出一種無名的仇視,尤其在蒙受了不白之冤之後。 一天放學回家,我心裡有一種少有的愉悅在蠢蠢欲動。忽然看見大班長的辮子竟在我眼前晃來晃去,讓我有一種非要上去揪一把而後快的衝動。我要以欺淩衝破欺淩,甚至不惜禍端臨頭,鋌而走險,上去就揪了一把。 果然,她眼睛裡透露出出乎意料的委屈和悲傷。我忽然領會了戲謔所給予「二孬」和「狗丟兒」的興奮,但瞬間這興奮就變成一種莫名的譴責和羞慚。 課堂 我心靈的扭曲已與母親呼喚中的期許相去甚遠,我所渴望的教育也超越了平靜的知識層面,似乎是一種命定的量身定做。 讀初中那年,化學物理的課本已經發到手裡,卻再沒有學習的機會。 一個反常的夜晚,學生被召到學校,打起彩旗,走出校門,遊行示威。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要停課、走上街頭鬧革命,卻被打扮成首肯和自願。
學校裡也天翻地覆。我非常尊敬的美術老師,忽然被揪上台批鬥,罪名是「一貫道」歷史反革命。頭兩天還看見他在台上情緒激昂、語無倫次地控訴走資派校長對他的歧視,並且聲嘶力竭地高喊:「堅決擁護文化大革命!」這會兒他自己竟成了灰溜溜的階級異己,再不是我熟悉的師長。他從此沉默,好像變了一個人。 我的學校坐落在松花江邊,這裡成了我們看熱鬧、消磨大好時光的去處。那天,幾個高我們兩級的同學忽然圍住一個因武鬥聞名的人,全校學生都喚他一個字——「亮」,那是他得意的暱稱。 狹路相逢,眾目睽睽之下從容毆鬥,仗打得似乎很有江湖義氣。頃刻間「亮」鼻孔竄血,但他沒說一句話。只見他鼻青臉腫,卻雙手抱拳,轉身而去;對方也不追趕,彼此心照不宣。似乎依據流行的「物競天擇」的理論學說,崇尚暴力、弱肉強食,並非是粗暴野蠻。因此輸贏都不失尊嚴。 這讓我幾乎弄不清眼前事發生在什麼年代,只奇怪多年的教育都難以改變人的觀念,但這流氓惡習卻無師自通、頃刻風行。 於是大街上經常遇見血淋淋的鬥毆,本是青春成熟的學生,表情卻兇煞冷漠;健壯碩大的身體,被棒子或鈍器狠狠地打,頹然倒地,並沒什麼是非理由。 老拐 生活在我的心弦上踏過,並非是出乎意料的節奏或旋律。或許是因為我的悖逆與兀自抗衡,24歲的我被關進一個滿洲國就存在的監獄裡,進去的人只有監號沒有名字。我的監號是1070,同監的犯人便送我一個綽號——「老拐」(編注:軍事通信中7讀「拐」)。 一個早晨,老拐被押上囚車。車上沒有座位,有也是荷槍實彈、居高臨下的押解人員的位置。我蹲在冰冷的車廂裡,背剪雙手,帶著手銬。囚車走在一條原來叫外國馬路的歐式大街上。車窗上都蒙著窗簾,與外界隔絕;幸而窗簾下有一條縫,我低著頭,看見了久違的城市和行人。車走在那特有的石頭馬路上,讓我如饑似渴地捕捉著無人理會的生活氣息,還斷續地聽見一些嘈雜悅耳的人間對話。 此時在我眼中,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建築物底端、台階,彷彿也釋放著記憶和生命,如同壯觀藝術作品的局部,喚起我無限的遐思。人的思想很奇怪,越是困厄羈絆,便越加活躍和澎湃。這是一座我所深愛的美麗城市,但此時我只配這樣窺視她。 我被押到一個至少能容納兩千人的俱樂部裡,要在這裡接受公審示眾。台下黑壓壓地擠滿了觀眾。我腳上兩隻棉靰鞡鞋沒有鞋帶,翻著舌頭;因為腰帶被解除,要用鞋帶代替,棉褲直往下墜。 兩個背著槍的民兵按著我的脖子,我低頭正好看見掛在自己胸前的大牌子,上書罪名——「反革命預謀集團主犯」。當時我尚未意識到這罪名的後果,只想抬起頭看看眼前的場面,否則好像對不起自己。 我佯作身體不自在,慢慢地直直腰。但見光線昏暗中,一張張陌生的臉漠然無表情,眼睛裡似乎都有一種期待,期待的也不過是這聳人聽聞的情景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我的頭又被狠狠地按下,於是聽到台下義憤填膺的高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可能每個人的心靈都有攝像功能,這一刹那永遠地攝在我心底深處。 兩年後,我被釋放,既非因刑滿,也非因無罪。親人都不知道我惹了什麼大禍,曾到處打聽我的下落。後來一個鄰居打聽到我是以反革命罪被抓,人們便都對我家敬而遠之。但總算是有了消息。 回到家之後,家裡讓我一定當面去感謝那位打聽到消息的鄰居。那時候我木訥得很,似乎尚在陰陽兩隔之間,因釋放的理由模棱兩可,好像隨時都可以重新收押。家裡準備好的禮物是用合作社最粗糙的黃紙包裝的,最廉價的點心和餅乾,但那已經是我家所能表達的最高禮節。 然而見面時,這位好心人竟目瞪口呆,眼睛裡充滿驚恐,好像那禮物絕非吉兆。當然禮物之微薄令人眨眼,更重要的是送禮的人如同禍水,誰願意有絲毫瓜葛呢?這讓我認識到,窘迫寒冷的心所表達的感謝也會令人毛骨悚然。 尊重 似乎所有門都向我關閉了,對於我來說,門並非指個人前途、青春理想或者生存就業,而是生命中的尊重。直到一個冰雪融化後路面泥濘的早春,我只身走進一所1936年建造的哥特式禮拜堂,屈膝受洗歸入基督。
當時沒有朋友在我身邊,我的親人也均不知曉,更無人向我祝賀。走出禮拜堂時沒有太陽,清冷的氛圍一如既往——淡然、真實、毫無色彩;但我內心卻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熱流,如蓬勃的春天湧進了我生命的空曠,悄然開始了勢不可擋的變化。 幸有一張照片記錄了這具非凡意義的時刻。所有剛接受洗禮的人合影留念,我擠在最後,勉強露出我的臉,前後左右幾乎均是沒有什麼文化的弟兄姊妹。我雖已近不惑之年,卻是最「年輕」的一個。 但幾乎每個人的表情都好像是軍人行進在隊伍當中,有一種凝重和肅穆。那是與神的羔羊為伍的行列,沒有勢力、沒有學歷、沒有身份地位的區分,完全在另一種取向和趨勢裡。從那一天起,我再沒有離開過教會。與其說那一刻我踏進了輝煌的生命殿堂,不如說那一天我如浪子般被天父抱在懷中! 此前一個白雪皚皚的冬日,我走進禮拜堂,那是我的第一個耶誕節。去到那裡的人都得到一份禮物——一塊用錫紙包著的蛋糕。 那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美麗的聖誕樹、天使的號角、讚美的歌聲讓我有種重新找到家的感覺,禁不住熱淚橫流。 我把禮物帶回家,妻子驚訝地問:「怎麼還有不花錢白白給東西的地方?」 然而這「一塊蛋糕」觸摸了我的生命。隨著對信仰的認識,我明白了一切都來自於祂,我們的生命也是祂的饋贈。上帝給我們的禮物不是一塊蛋糕所能涵蓋的,那禮物是祂自己! 那一天祂走近了我,那是我生命的第一次甦醒。 那是一次相遇,是祂在尋找我,且找到了我。我其實一直在祂的看顧之下,這是那禮物留給我的滋味,讓我因此瞥見永恆,且年日愈久愈清晰! 那恩典的滋味是一種明確的身份感,是我從未領受過的愛和尊重。 -END- 作者簡介 沐恩 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於1990年受洗歸主。曾發表《我的守望者》、《我的牧師——獻給那一代為主受苦的牧人》、《一封家書,傳承希望》等多篇文學作品。現仍在某基督教會傳講福音,委身事奉達三十年之久。 圖書推薦
《恩典不留白,下筆如有神》 -莫非 蘇文安 劉小臨著- 恩典故事前, 人人皆可 自許為作者, 書桌乃朝聖祭壇, 生活如展頁稿紙, 捕捉心中悸動, 描述看不見的你! 購買資訊: 台灣:橄欖華宣 https://www.cclm.com.tw/book/19314 北美:gcwmi622@gmail.com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