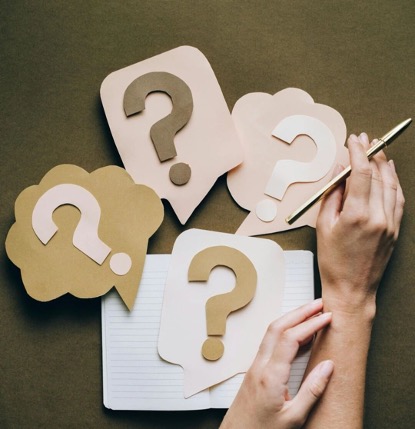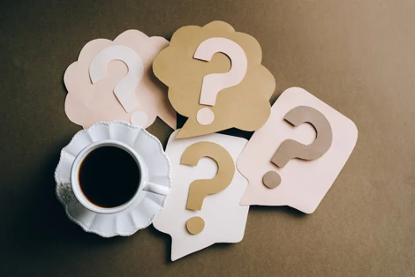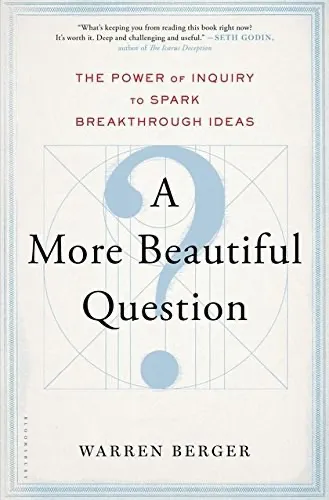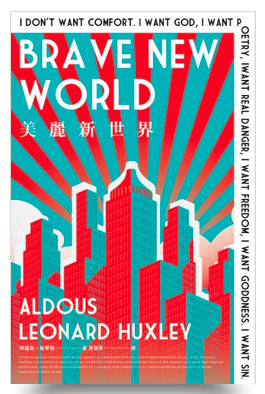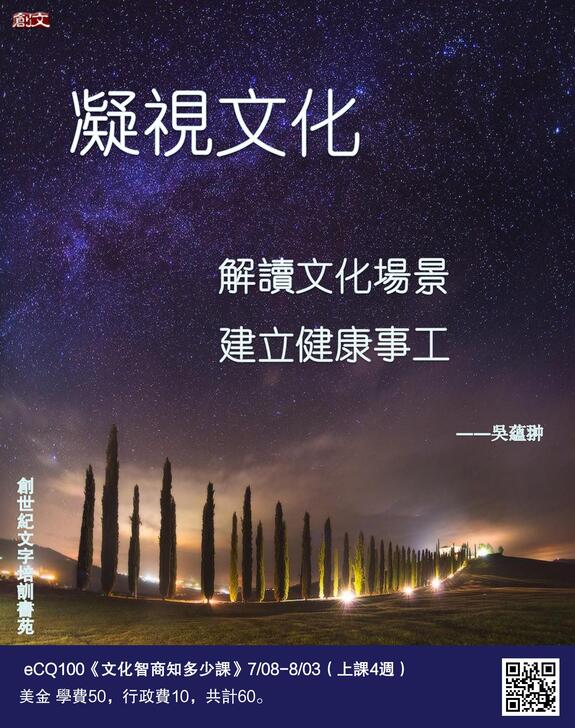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06/22 13:44:03瀏覽1346|回應0|推薦1 | |
有些作者提出問題,是為了給出答案,而有些作者卻是為了聆聽,帶人走向靈魂深處的渴望。你是一個喜歡探問的人嗎?在探問中你會有何發現呢? 解讀文化場景,建立健康事工。歡迎查看文末海報,瞭解eCQ100《文化智商知多少》。
還在拿筆寫作的日子裡時,每次畫上問號,都覺得她特別神奇。 ? 一個鉤子,加一個小點。 鉤子,肯定是要抓住什麼東西不放;放在一個小點上,仿彿在告訴人:對,很小很小,微不足道,但,我就是被鉤住了,放不下,抓不住;所以鉤子和小點之間一定有個距離,但他們又是一體的,彼此要把對方帶著走。 中學到了阿根廷,發現西班牙文的問句必須先放一個倒問號在前面,最後再以問號結束。沒問過老師原因是什麼,自己偷偷地詮釋著:有道理啊!很多議題的開端不都顯得那麼無法駕馭嗎?但是當我能好好把疑惑化為問句時,就成了自己主控,去抓住那個議題了。
問號,是個美麗符號。 我,是個向內的好奇寶寶。 童年尚未接觸到信仰,小小年紀,在大人當中仔細聽他們說話。那個年代的長輩不鼓勵孩子發問,「小孩子有耳無嘴」是他們常常發出的警告。被允許聽,卻不被允許發問,你猜怎著?還是孩子的我就邊聽,邊在心裡把問號像泡泡一樣,從一個小水滴,吹出五彩繽紛漫天小球。 對外,我很少拿問號追著人跑,但我的內在牆上,貼了充滿問號的壁紙。我喜歡問為什麼,更喜歡問如何。青春年華時去逛街,看著那些漂亮的衣服、包包、鞋子和飾物,周遭朋友都在驚歎、試穿、想像著穿戴在自己身上的美麗,我總在心裡想著:這衣服為什麼看起來特別好看?是顏色好?樣式好?還是因為街上很多人在穿類似款式,我就感覺它美麗? 如果我能買到一塊類似的布料,如何能做成那件衣服? 連逛傢俱店,我也會站在一張大書桌前發呆,想著,如果我找到電鋸,割得動木板,是不是也能拼做出這張看起來特別大氣的核桃木書桌?從哪裡開始? 出國第一年,在遙遠的阿根廷,頭50天,我們住在一棟99年的古屋裡。如同恐怖電影裡的房子,那棟古屋的天花板大概有二層樓高,每次抬頭,就看到錯綜的蜘蛛網。我總是趕緊低下頭,假裝什麼都沒看見,卻止不住頭腦裡一連串疑問: 九十幾年前坐在這裡的小女孩抬頭時會看到什麼?那些蜘蛛的祖先嗎? 這房子裡,有過怎樣的故事?有人吵架打架嗎?為什麼整棟房子像一隻舊盒子那樣,留下歲月,卻未曾留下人跡? 有機會參加婚禮,看到大門打開,西裝筆挺的父親牽著新娘走在紅毯上。有的會滿臉笑容,對兩旁站起來的親朋好友點頭致意;有的表情嚴肅,目光向前,彷彿要帶著女兒走向祭壇。我也會在內心偷偷地問:這些父親的感覺是什麼?在想什麼?他們到底想哭還是想笑?想感謝還是想揮拳揍人? 奇怪的是,我常常發問,卻不很積極找答案,或者,更準確地說,我挺習慣和問題共處,不急著把它們推開。 有時,我甚至覺得一個問題就是一個花苞,養著養著,就有可能綻放成一朵嬌豔的花。 經常,與我討論問題的是書本作者。書本打開,只要是從問題出發,讀起來就特別起勁兒。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有的作者準備的是一堆答案,非要讀者接受不可,讀完沒得到討論,只是上了一堂課。但有些作者往往能用文字引導我從自己的問題出發,去看到更寬闊的天地。 我要做哪一種作者呢?這個問題跟在我後面,像個要糖的孩子鍥而不捨。
從不同的書本裡,我展開探問,也學著不局限在是非題的範疇裡,一路黑白穿梭。讀對我更有啟發的書本,總是像剝洋蔥那樣,解開一層,裡面還有一層,讓人剝得淚眼婆娑。 不過,我也有把自己「問丟了」的時候。一本書讀太久,往往在讀完時已經忘了出發時在探問什麼,也可能,拎著一個問題進去,書讀完後,帶走的卻是一籮筐問題。 每個問題都是一座山,從這頭繞到那頭,上山很慢,很喘,一心想趕快登到山頂去看全景。下山很快,很有成就感,但要自我約束,別衝得太快,否則一路景致就拋在腦後帶不走了。 除了對作者發問,我也一次次打開日記,用文字探索人生叢林。在那裡我既是發問的人,也是討論的人,常常,還是回答的人。 當然,多半時候祂是我的座上賓,祂的同在,讓我安心追問。 有時候,我也會對自己的問題發問: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別人也會問類似的問題嗎?還是因為我的某種偏差的角度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 於是,問題如鏡,我在其中,得到了不少看清自己的機會。 很多問題乍看之下是一團糾纏在一起的毛線,對書寫的我,卻是一座又一座秘密花園,等著我走進去辨認奇花異草。 困境中,用文字在日記裡向祂發問,少了平常禱告時的情緒火花,我能夠靜下來,追根究底地問,不急不怕,因為祂不爭辯。阿爸的確會直接用祂的話回應,但更多時候,祂把答案化為生活的經歷,直接讓我活過了,就明白了。 祂是個會問問題的神。 對悖逆犯罪而躲起來的亞當夏娃,祂問:你在哪裡? 起初,我以為這句話的後面不是問號,而是驚嘆號。那是父親生氣時對孩子的質問,聲調可能是諷刺的,冰冷的,問號裡藏著一把刺刀。 後來成為人母,開始理解那可能是個雙面問題,既問了離開本位的孩子,也感歎著自問: 「唉,那個自己用全心全意去創造、愛護且信任的孩子,怎麼就走丟了呢?」 一個問題,剖開許多真相。 對那個因嫉妒而殺了弟弟的該隱,祂問:「你兄弟亞伯在哪裡?」 全知的神,為何不直接控訴這個殺人犯,並指出他企圖掩蓋的罪呢?我猜,祂想透過問題給該隱一個面對自己的機會,畢竟悔改這件事,不是別人定罪後的不得已,而是自己真心的看見、承認並渴望被饒恕。 耶穌也喜歡發問,儘管他的話語帶有權柄,令人折服,但祂更常把答案留給人自己去尋著。 那回,他經過一個地方,有兩個坐在路旁的瞎子大聲求他:「可憐可憐我們吧!」這肯定是引起了其他路人的注意,以致有人叫瞎子住嘴,結果,他們卻變本加厲,喊得更大聲。 一個已經用神蹟奇事醫治好許多人的「奇人」來了,誰看不出這兩位瞎子會要求什麼呢? 但祂卻停下腳步,與他們正視,問:「要我為你們做什麼呢?」
Christ Healing the Blind,El Greco 每次讀到這個問話,就想起自己那些在祂面前鬼哭神嚎的時刻。很多次,我想要的的確是幫助,卻不真正知道自己在求什麼,也不瞭解自己求的對象是誰。那種求,不過是像在溺水時隨便亂抓浮木。 乍聽之下,這是明知故問。 很多年間,我都看不懂祂的問題,直到把後面一句話放到圖畫中——「他們立刻能看見,就跟從了耶穌」。我才發現,啊!原來對瞎子當下的欠缺來說,也許能看見就是最重要的解套;然而對他們的生命來說,看見,並找到此生應該跟從的對象,才是終極的解決。 答案給人即時的滿足,問題似乎搗亂思緒,卻在塵埃落定時分,可能曝露靈魂深處的渴望。 年輕時寫文章,總想把自己知道的跟人分享,以為那些是自己擁有的最寶貴的知識和領悟,是自己確定的答案,應該讓更多人得著。 為了想要提供答案,寫作的過程就會有不小的壓力,要讓自己提出來的答案更完整,更有說服力,無法被質疑。 同時,我也被一個殘忍的聲音不停質問:你是誰?有什麼資格提供答案?誰要聽你的? 閱讀,歲月,經驗,祂用這三隻毛筆,在我的稿紙上齊筆揮灑出這話:讀者真需要答案嗎? 的確,我會帶著尋找答案的期待去開讀一篇文章、一本書,不過群書中,似乎那些充滿了答案的書,我都不太想讀第二遍。 現實人生,好答案有時會幫我走過眼前這一步,好問題卻給我走下去的方向,和走得更遠的動力。 尤其進入網路資訊時代後,每天都有讀不完的答案等在那裡。百度谷歌這些搜尋引擎帶我們去爬答案堆起來的大山,chatGPT直接把答案裝在盤子裡端到眼前,一盤不飽再來一盤。 我和chatGPT玩過多次寫作文的遊戲,給一個主題,加上幾個問題,丟給他發揮,眨個眼,兩千字文就四平八穩地出現在眼前。 表達太過論述性?沒問題,告訴他麻煩寫得有感情一點,我想讀散文,再眨個眼,又是另外一個語氣寫出來的文章。 卻無論如何包裝,裡頭都是答案。 像間倉庫,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給人「逛逛」的空間;像張畫得很滿的圖,刷足了畫者的存在感,卻讓觀畫者的想像力沒有駐足的角落。 在《一個更美的問題》(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這本書裡,作者華倫·伯格如此寫著:「我們手中擁有幾乎無窮的資訊資源——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沒有這樣的機會。而且我們擁有這種人際聯繫的即時性。將所有這些資訊和人際聯繫結合起來之後,人擁有的,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全球大腦。」
這樣的全球大腦,就像一個有愛因斯坦智商的天才,直到發問的那刻,裡面的資源都屬靜態,也不會帶來任何改變。 我喜歡這位作者提供的公式: 問題(Q)+行動(A)=創新(innovation) 問題(Q)—行動(A)=哲學(philosophy) 倘若作者寫的東西裡沒有給予提問的空間,沒有激發讀者更深提問的元素,也沒有鼓勵讀者或自己展開探索的行動,那麼這篇文章,只是落在讀者手上的一個花瓣,不是種在讀者心裡的一粒種子。 然而在引導讀者探問之前,作者自己必須先是個手捧問號的人。 一個作者會產生疑惑的議題,往往也會給予讀者最寶貴的閱讀價值。即使這代表著動筆之前,作者沒把握能到達何處;即使這一路思考、研究、收集資料的寫作過程,必須擁抱不確定性;即使在掙扎時,作者本身可能被更多問題五花大綁,這探問,並且邀請讀者一起走上探問之路,仍然是趟美好的成長旅程。 一位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和一位美國作家、記者兼廣播節目主持人,都喜歡問一些有趣的問題: 「學校老師和相撲選手有什麼類似的地方嗎?」 「毒販,為什麼還可以住在媽的家裡啊?」 他們是史蒂文· D·列維特(Steven D. Levitt)和史蒂芬· J·杜布納(Stephen J. Dubner)。兩位作者一起探問的過程中,把經濟理論帶入了各種現實生活的狀況,寫成了暢銷書《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幫助讀者接近人類行為和社會趨勢的真相,並且得以問出更多好問題。 看到人工智慧的產生,自駕車的普遍化,面對這些科技進步,你除了是個享用者,是否也曾發問? 若有,你的問題不孤單。多年前也有人問過:「技術進步似乎帶來了更好的生活,但,是否也將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 「科技會使人更強大還是更脆弱?」 「人在科技的加持下會得到方便,是否也因此失去了自由和獨特性?這樣的科技好處帶來的是幸福嗎?」 從這些問題裡,有人一鏟一鏟地挖到底處,發現躺在最底下的問題是: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 於是,他透過這些問題寫成了一部小說。 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是英國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就是源自上面這些探問。透過這小說人物內心的痛苦和掙扎,他嘗試讓讀者找尋出自己的答案,同時也邀請讀者為自己做更深的心靈探問。
《美麗新世界》,好讀出版社 著名基督徒作家楊腓力在一次演講裡曾說,神學他懂得不多,但有件事他是專業,就是質疑,尤其是對苦難的議題。 從自己原生家庭到記者生涯的所見所聞,每一個苦難的存在,都讓他對信仰產生許多的問題,他必須透過文字書寫給自己發問的機會。於是,每一本書都成了他一個探問的經歷,也將引導他走入下一段的探問之途。 布萊茲·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說:「人們通常比較容易被自己發現的理由說服,而不是被別人所給的理由征服。」 曾經,我帶著分享真理的熱情書寫,會抱著好東西非塞到對方口裡看到對方吞下的期待。但這些年,我開始學著自問: 「嘿,你到底是想寫一個正確答案,讓讀者知道你是對的?還是,你自己很想瞭解一些重要的生命課題,然後透過文字去探索,邀請讀者來關注,並對這些課題發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問題?」 「你發問,是為了回答?還是為了聆聽?」 已經很久沒用筆在紙上寫作了,但每次在鍵盤上敲打出問號時,仍然覺得這是個很神奇的符號。 不過,現在我看到的「?」,並不是小點上有個鉤子,而是一個耳朵。她每次出現,都對我再說一遍:能聽,才能產生好問題喔! 真的,作者懂得問,是因為懂得聆聽,也需要聆聽。 -END- 作者簡介 馬睿欣 電子工程學士,富樂學院碩士。一生鍾愛寫作。曾任《宇宙光》、《真愛》雜誌專欄作者,文章發表於兩岸雜誌報紙、自媒體號等。過去幾年主領「用心生活」線上群,透過文字去影響近萬名學員在不同人生階段(單身到成人子女的父母)的現實生活中認識真理,活出真理,享受真理。著有散文集《遊子足音》、《管教的智慧》、《理家理心》、《直面網路》、《書蟲落網有出路》(合著)、《養育模式大逆轉》。 課程推薦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