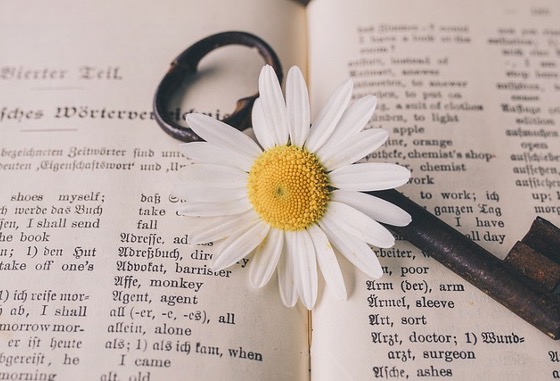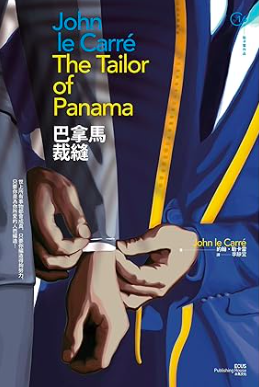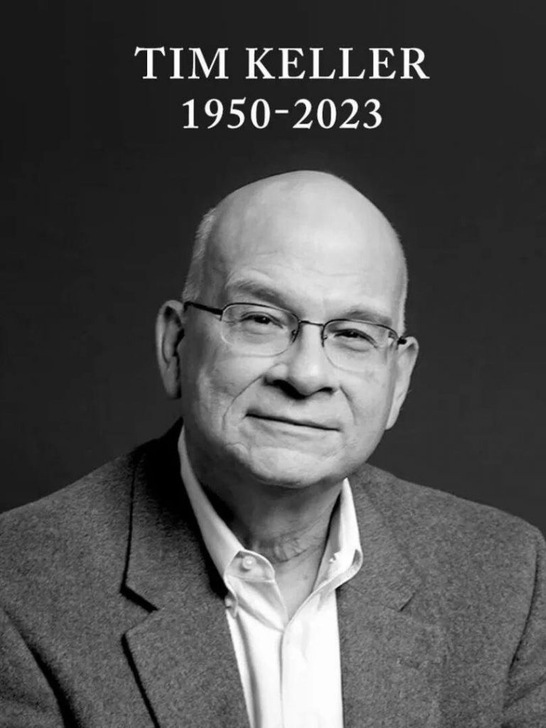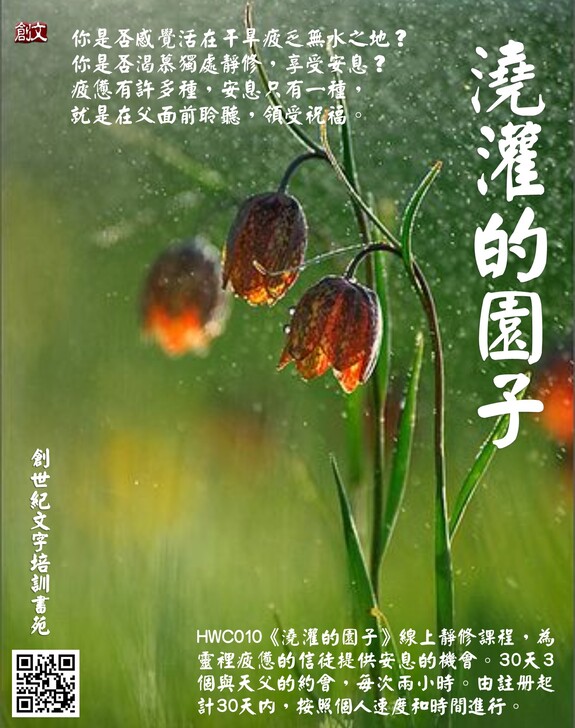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3/11/03 10:18:55瀏覽1143|回應0|推薦3 | |
翻譯家李靜宜說,翻譯一本文學書之前,首先是愛上那本書,進入那本書。那麼,翻譯與你我有什麼關係?我們是否也有自己要認真面對的「翻譯人生」呢? 獨處靜修,和祂約會,讓疲憊的心靈重新得力。歡迎查看文末海報,瞭解HWC010《澆灌的園子》。
從喜歡寫、習慣寫到委身寫作,文字路上,我一直認定自己是個母語的創作者。也就是說,我不是編者、不是閱讀推廣行銷者,不是多媒體工作者,也不會從事翻譯。 翻譯?這絕對不是我的杯。 雖然早早出國,有著學習不同語言的優勢,但我實在不是個很有天分的語言學生,常覺得自己的腦子被瓜分出四個空間來承載四種不同語言,而他們彼此把雙臂抱在胸前,噘著嘴互不溝通;我只能一次待在一個空間,思考和說寫那個空間的語言。所以每次特會時,看到那些即時口譯能在不同語言中自由來去,總是非常敬佩,然後對翻譯這差事更敬而遠之,完全有自知之明地,相信翻譯與我無關。 那年,終於有機會進入神學院,好好地把過去透過書本或是講台得知,在腦子裡飛來飛去,各家各派的理論學說抓到課堂上,在教授的指導下,正面相見。 說也奇怪,平時書寫的多半是散文,也不寫學術和論述辯證型的文章,卻對被認為「很硬」的理論有興趣,好像吃一盤炒出來的清脆蔬菜無法滿足,非得生啃幾口才覺得真正嚐到那蔬菜的原味。研究所選課,正當周遭華人同學談著那一堂應用性的課程多精彩,得到多少實操教導時,我默默地穿梭在一些冷門的理論課中間,一次次驚喜地發現:喔,原來是基於這樣的教義和學說! 那些年,我第一次有了對「翻譯」的另種認知:不是從一個語言轉成另外一個語言,而是把原則性、理論化的言詞轉成大眾能讀得明白的普通話。帶著一支筆的呼召去神學院受裝備的我,初次感覺透過文字去做這種「翻譯」的可能和需要。當時還默默禱告,希望能夠多讀幾年書,深入探索理論的深奧。 可惜還剩下半年就畢業時我懷了老大,一年後又懷上老二。在放下尿布拿起神學課本,拋下寫一半的論文,衝去抱起哭泣娃娃的轉換中,我匆促地告別了心中對神學理論所懷有的浪漫,老老實實地回到現實中過日子。
歲月拿塊布捲起三個娃兒,扛著就往前奔,我一路追得喘吁吁,不再去想翻譯的事兒,不再裝腔作勢地研究起跑姿勢怎麼擺,鍵盤拉出來就寫。只有生活中每次拾起一些比較理論性的書,或聽一些課,轉身回來面對現實中的挑戰,突然被點亮時,會渴望透過文字與人分享,不甘於自己一個人手足舞蹈,原地轉圈圈。 你讀過××寫的書嗎? 你聽過×××的理論嗎? 你知道很多年前×××已經探索過這個問題,他的答案是這樣的...... 在小組、姐妹群中如此問,偶而會有人認真地掏出小紙條:「再說一遍書名,我去找......」、「誰?我查查。」 更多時候,會得到這樣的反應:「喔,書買了,好艱深啊!實在沒那個專注力去研究。」 後來,還有更直接的回答:「你既然讀過了,直接講給我聽吧!」 一開始我不放棄,義正詞嚴地說:「書要自己讀,才會自己思考,自己得著。我講的都是二手貨。」 他們順服地點點頭,「憂憂愁愁地離開了」。 當時,我內心還有沒說完的話:「我不是天才,讀這些書也是花上代價,一遍不懂讀第二遍,一本不行讀第二本的好不好,想有所收穫哪有捷徑?」 生活會把人的心像團麵那樣搓揉,擀平,再搓揉,直到它「三光」:看不見麵粉,看不見硬塊,看不見水。 翻譯的念頭再次回來找我。 如果有一本值得讀的英文書,不懂英文的人無法讀,並非因笨或懶,那麼,讓他們有機會閱讀的最好辦法並不是叫他們重新學一個語言,而是找到一個好的翻譯本。我想起許多姊妹走在生活的困境中,愁眉苦臉地對我說:「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講理論?告訴我怎麼做好嗎?」把寫在那本永恆大書的真理,透過其歷史、文化背景和書寫的文體去理解,透過聖靈親自的引導去領悟,然後轉換成生活可以聽得懂的方式演繹出來。也許真理從原則到實踐,也是一個翻譯的過程? 過去對翻譯的印象就是頭腦夠靈活,語言有天分,寫作有紀律。 如果知道某位譯者自己能創作,卻願意花時間成就別人的優質作品,將其帶到更多讀者眼前,會覺得他們很了不起。因為對我來說,這是孩子自己生和去收養的差別。由於不是自己的領域,我很少關注譯者心聲。 在一個不小心點到的podcast訪談節目裡,那個譯者聊自己對翻譯的愛,卻震撼了我。 雖然不是外文系畢業,又擔任公職三十年,她卻因著對書的熱愛,產生把它們翻譯成中文與更多人分享的渴望。為此,不但多年斜槓度日,白天在公務機關工作,晚上在家翻譯小說;退休後,還在出版業低迷的季節,為了把心愛的外國推理小說引進華人世界,與友人開了一家出版社。 《追風箏的人》中文譯者,已經翻譯了八十多本書的翻譯家李靜宜說,翻譯一本文學書之前,首先是愛上那本書,進入那本書,花時間與那本書的人物相處,去體驗裡面每一個角色的喜怒哀樂。簡單一句話,就是「入戲」。 原來翻譯不是語言的交換,在怎麼說給讀者明白之前,譯者自己不但理智上要明白,情感上也要感受得到,心境上更要對文字背後的理念能有所領悟。 她遇到最難翻譯的小說,就是《巴拿馬裁縫》的作者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作品。剛開始,她只是覺得這位作者用字艱深,要讀懂字面意思就很困難;直到人生來到某個歲數,有了某些經歷,她才終於領悟到勒卡雷筆下所講述的人性糾葛。只有在現實生活的經歷中明白了,自己真正讀懂了,領會了,才能夠精準地選擇語言和敘述方式,去講述給中文讀者聽。 先愛,先讀懂,先體悟要翻譯的書,然後才選擇你要使用的語言。李靜宜說:「用他們的邏輯去理解、思考,才能忠實呈現其口吻,推敲出角色接下來的抉擇與行動。」 我聽著,恍然大悟:啊!真理落實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那道成肉身的呼召裡,對「道」的熱愛,明白,和體悟,也必須走在前面,引領我去選擇自己要如何使用每一天去翻譯所信。 然而對譯者來說,語言的選擇仍非常重要。除了懂兩種語言,還要照顧到不懂的受眾,他們需要的,是説明自己明白的表達方式,所以太執著於語言交換的精準度,而失去流暢易讀性,以致產生「翻譯腔」,是李靜宜看到的不成熟譯者最容易犯的毛病。 我想起自己當年從一個沒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家庭走入青少年團契時,就對這種翻譯腔既羨慕又困惑。 羡慕,因為他們懂得另一種我不懂的語言;困惑,因為他們講的字我都懂,就是湊起來艱深無比,讓我似懂非懂。 而且自己還不敢問「你剛剛說的是什麼意思?」就怕露餡兒,顯出自己不但不會外語,連自己的語言都掌握不好。 踏入信仰之後,我也曾經興奮地想成為未信父母的真理翻譯者,發現自己的翻譯腔一點不輸他人。 這個翻譯腔,有時候是因為懂得不夠徹底,所以直接抄用辭典書面語。我總是很氣,明明講得那麼清楚了,你們為什麼就是不明白,不接受?哪一個字你們聽不懂呢? 有一回,在廚房做飯時,我又用翻譯腔跟媽媽講了一些見證故事,正講得熱血沸騰,她悠悠地望著爐火,突然回了句:你們都是聖人,我很平凡。 當場我愣住,原來自己的翻譯這麼離譜?讓人不但沒聽懂,還聽錯。 漸漸,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自己在不信的家人朋友當中的角色,就是一個譯者。每一個讀那本永恆大書的人,都在用自己落地的生活去翻譯大書,幫助周遭沒讀過或讀不懂的人明白。但我的翻譯語言是說出來的話,也是做出來的行動,是自己的生活見證,也是我與受眾的關係。每一個人都有他能讀懂的語言,我不能把英文書翻成西班牙文給華人讀。 在文字工人的體驗旅程中,我更多地認識了天國語言和地上語言之間的翻譯使命,發現除了應當理解原文和其作者,也需要對另一方的讀者有誠懇的理解和珍惜。 約翰·伊納祖(John D. Inazu)以在法律和宗教領域的工作而聞名。他是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法學院的傑出法學和宗教學教授,長年在地上的法律與天國的法則這兩個領域之間來回對話。他也認為自己真正的工作就是翻譯。 最近,我讀了他和提摩太·凱勒牧師一起策劃編出的書——「Uncommon Ground-Living Faithfully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非凡之地——在多樣世界中忠誠生活》,ChatGPT翻譯)。 凱勒牧師被主接走之後,有不少文章和採訪回顧他的一生,其中一項,是他樂於和非基督徒知識份子對話。在面對信仰理念的差異時,凱勒牧師的方式不是找出對方弱點切入,而是找到雙方的共同之處開啟對話。 帶著這樣的理念,在書中,他和伊納祖教授邀請十位不同領域的菁英加入,分享他們如何在自己的領域裡活出信仰,找出自己領域範圍內和不同信仰之人的共同之處,並從那裡出發去做有聲無聲的福音傳遞。 伊納祖教授在此書裡寫了一章,取名為《譯者》(The Translator),裡面談到自己跨在世俗高等教育學府和基督信仰中間,既是法律教授,又是基督的事奉者,常常覺得自己做的就是翻譯工作,若能在諸多差異中找到雙方的共處之地,不但能建立雙方的共同興趣,更能拉近彼此的關係。 他還提到一個優秀律師會熟知的法則:自己論點的成功取決於瞭解對方的論點精華。而這些屬於對方的優質論點絕對不是一些誇張的表現,它們代表著對方觀點當中最慷慨和複雜的思想闡述。把對方的論點妖魔化並不能幫助律師說服對方,只有讓對方看到自己認識他們的優點,才能找到進行溝通的共處之地。 他深信,身為世界和教會之間的翻譯者,代表著對真理的熟悉領悟,也代表著對世界論點的深入瞭解;和大學教授同儕學生做好朋友,就像和教會裡的人做好朋友一樣重要。
在文字創作的喜悅裡,我也身處兩個國度,承受著這樣一個翻譯使命。無論是透過怎樣的文體書寫,我將是站在兩個國度中間的譯者。 翻譯家李靜宜對原文書籍的入戲,讓她不只讀懂原文語言,也讀懂作者為什麼會這樣說故事;對自己人生經驗的認真體悟,更讓她經歷了那些故事怎樣和自己的故事之間有了交集。她最近一本書《為你,千千萬萬遍:靜靜讀一本書的翻譯筆記》裡,就記載了她如何愛上了自己所翻譯的書,又如何在自己的現實裡,繼續與那些書的內容深刻對話。 文字工人的創作也是從愛上那本大書起步。一遍一遍地讀,都是生肉,等著現實來煮熟。而伊納祖教授和凱勒牧師提醒我,對受眾的尊重和理解,與他們建立生活上的連結,開展真摯的友誼關係,會讓我懂得選擇怎樣的語言去闡述我所理解體認的原文故事。 前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長理查·莫爾(Richard Mouw)在為《非凡之地——在多樣世界中忠誠生活》寫書評的時候如此說: 「要熱愛去跟意見不合的人互動,這對許多堅守基督信仰的人來說並不容易。提摩太·凱勒和約翰·伊納祖不僅做到這一點,成為榜樣,而且在這本精彩的書中,還聚集了智慧的對話夥伴,提供了急需的建議,為如何培養謙卑、忍耐和寬容的屬靈美德提供了必要的忠告。這些美德對於如何去愛多元化文化的鄰居實在太重要了。」 謙卑、忍耐和寬容,正是凱勒牧師所提出來的,所有真理翻譯者的必備條件;當他們離開書桌,進入現實與人互動時,生命,就成了周遭人最容易讀懂的稿子。 於是,作者有時用筆或敲鍵盤寫成文字書,卻在每一天,用自己的生活,讀成給周遭人聽的有聲書。 於是,在文字工人的寫作呼召裡,也有一個從愛上帝到愛鄰舍的翻譯人生要認真地活。 —END— 作者簡介 馬睿欣 電子工程學士,富樂神學院神學碩士。一生鍾愛寫作。曾任《宇宙光雜誌》、《真愛》雜誌專欄作者,文章發表於兩岸北美雜誌報紙、公眾號等。過去幾年主領「用心生活」微信群透過文字去影響近學員在不同人生階段(單身到成人子女的父母)的現實生活中認識真理,活出真理,享受真理。著有散文集《遊子足音》、《管教的智慧》、《理家理心》、《直面網路》、《書蟲落網有出路》(合著)、《養育模式大逆轉》。 課程推薦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