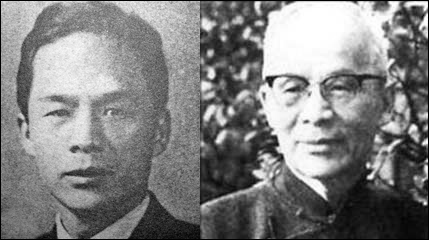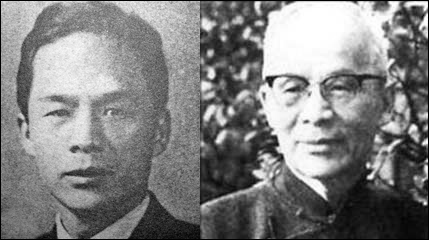
胡蘭成是爭議性的人物;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學上亦然。胡自負才華,自命風流,而又與世間格格不入。他曾自比《白蛇傳》裡的白蛇娘娘,「她在瑤池群仙班裡不合格,來到人間做媳婦又落地,我大約亦帶幾分妖氣」(《今生今世》)。戰後他亡命天涯道路,在溫州化名結識大儒劉景晨,亦自譬為妖仙白娘娘,「來到人世的貴人身邊避過了雷霆之劫」。近年或由於張愛玲,朱天文之故,議論胡蘭成者日多,而論者亦每謂其有妖氣。
王徳威(〈從〈狂人日記〉到《荒人手記》─論朱天文,兼及胡蘭成與張愛玲〉)直指其行文「嫵媚妖嬈」。胡之所以給人妖氣的感覺,應該是綜合其人格與文字的。說他「妖」,可以指他的才氣謀略。比如魯迅抱怨《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描寫太超過,說羅貫中 「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胡蘭成為汪精衛策士,便素有「小諸葛」之稱。他寫《今生今世》,文才斐然; 晚年殷殷指導朱天文天心姊妹及「三三」諸青年,自成門派。朱天文《巫言》出書之後接受電視節目〈鏗鏘三人行〉訪問,主持人竇文濤提到朱的「巫氣」與胡的「妖氣」, 聰明的朱天文以「智慧老人」來形容胡蘭成:「他就是會讓妳覺得妳總是要有妳最好的部分…召喚出來」。 把術士的符咒招引和教育家的諄諄善誘等同起來,這是對妖氣的最優雅的詮釋了。
然而大致而言,妖氣是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像電影Fatal Attraction中的女主角一樣,美色和激情之中隱藏殺機。胡蘭成的風姿文采便有同樣的吸引力,王德威說它「甜膩嫵媚」,但你耽享之餘,似乎總會覺得有種莫名的不安。我們且來看胡蘭成自己是怎樣描述妖氣的:
- 我曾為小倉遊龜先生講說此童謠,想她可以作畫。我的構想是暑夜的天空畫一顆熒惑星放著光芒,天邊一道殺氣,隱約見胡騎的影子,畫面的一角是一妖氣女子白身仰臥星光下,眼皮搽煙藍,胭脂嘴唇,指甲搨紅,肩背後長長的披髮,在同一星光下,井邊空地上是幾個小兒圍著一個緋衣小兒在唱那首童謠,畫面上下一派兵氣妖氣與那小兒眼睛裡的真實。(〈中國文學的作者〉)
這裡胡蘭成明明白白的把妖氣具象化為一個「白身仰臥星光下,眼皮搽煙藍,胭脂嘴唇,指甲搨紅,肩背後長長的披髮」的致命女郎(femme fatale)。我們可以感到胡蘭成深受這個意象─或許是他想像中的白娘娘? ─的吸引,我們也深受這段文字的吸引,但不知怎的,我們感覺其中似乎有些不妥。這種感覺並不完全是因為文中提到與妖氣並存的殺氣與兵氣,而是我們亟想知道: 怎樣的男人,會有這樣對妖氣的詭異想像。
我認為胡蘭成的妖氣近乎《紅樓夢》中賈寶玉的邪氣。《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對賈雨村演說賈寶玉的乖僻性格:
- 那年周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
這話引起賈雨村“罕然厲色”地長篇大論賈寶玉一派人物:
- 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盪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盪,或被雲催,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胡蘭成的賈寶玉性格,可以進一步從他喜愛脂粉的癖性和多愛不忍的痴氣與獃氣獲得印證。
胡蘭成的脂粉氣
張愛玲在《小團圓》中這樣說邵之雍(胡蘭成): 「他正面比較橫寬,有點女人氣,而且是個市井的潑辣的女人。」事實是,胡蘭成不但不諱言喜歡脂粉,還常自比女人。除了上述白蛇娘娘和妖氣白身女子外,下面這些都是證據:
- 冬天,我們全家和幾位文友約了胡老師去山仔后空軍招待所洗温泉。走路上聞到香味,大家找著,說起每人喜歡聞什麼香,母親是聞到香水就頭暈,問胡老師呢?不會暈,喜歡女人身上的粉香,大家都笑起来。(朱天文〈優曇波羅之書〉)
- 歸途乘電車,於羽村驛見一好女子,及乘上了電車,她立在我面前,二人都無坐席,我遂得細看她。她大約還只有十八九,不出二十歲。夏天著淺白色衫裙,赤腳穿皮絛結的無鞋幫紅鞋,胸襟珊瑚別針。平常我愛和服,對女人的時裝多有意見,焉知時新兩字竟有這樣好。她搽的手指甲與足趾甲桃紅色。眼皮搽淺淺的煙藍。搽指甲油與搽眼皮真乃女子的嚴格考試,女子每天的化妝是創作。她臉上薄薄敷有香粉,可比是新篁初解籜時。(《今生今世》)
- 一枝使我想起日本神社的巫女,白衣如雪色,一條大紅的裙子攔腰系在衣衫外面,非常鮮潔的顏色,臉上隻是正經與安詳,而因是年輕女子的緣故,雖然素面,亦似聞得見脂粉的清香。… 早飯后好洗碗盞,一枝梳妝,我在旁邊看她。問起昨天買的脂粉,她笑道:“昨天下午,我就試擦了,無人自己對鏡一生懸命的學習,為要使你歡喜,說出來都難為情。”… 即如此刻我看她梳妝,只覺雖是人世的大憂患,到了她這裡亦像小小的口紅,粉盒,梳子,夾發針,無一不好。(《今生今世》)
- 如此我想起了每回我給你寫信為何。聖賢之學即是人生的蘭花,生在崎嶇險難之處。我可比是那婦女,你在路上遇見我,我抽蘭花贈你,告訴你蘭花生處路難行。(《意有未盡:胡蘭成書信集》)
- 聊齋裡有〈封十三娘〉,她徒以懈逅女友,不覺愛之至,為之代謀婚姻。幾至己身亦堕入情障。我向來沒有與人結詩社或談道論學,徒以懈逅君毅先生,亦不覺愛之至耳。以此幾乎堕入論學的葛藤裡去。可是又有你這個小後生,這段情障恐怕難以拔出了。(《意有未盡:胡蘭成書信集》)
- 我有一種習慣,也能以男子的眼光去看好的女子,也能以女子的眼睛去看好的男子。我自己好像是沒有一定的性別的。對於好的朋友,我幾乎同時兼有一種兄弟姊妹和師生的感情,這種感情說得好可以說是流光掩映。(《天下事猶未晚:胡蘭成致唐君毅書》)
而胡蘭成的女人論,更與賈寶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有異曲同工之妙:
- 原來最早開了悟識的是女人,至今亦還是女人比男人善感,女人比男人曉得選顏色,也比男人會歌舞。以前我以為女人的美是男人造就她的,後來才知道女人的美完全是女人自己所創造的。高等動物皆是雌不及雄美,惟人能女比男美,此是女人最易接近神(女人最易感知神,故古時是女人主祭,日本伊勢神官以皇女為齋主),所以能有這樣美了。套一句今人的句法:女人,你的名字是文明。西遊記孫悟空叫觀音菩薩“汝七佛之師”,女人是教了男人文明。(《今日何日兮》)
胡蘭成的癡氣與獃氣
除了脂粉氣,最近一些新出土的資料清楚地顯示出胡蘭成的癡氣與獃氣。先說癡氣。
胡蘭成在1960-1977年間寫給香港新亞書院學生黎華標的七十封信。這些信出土後,朱天文看了,稱羨不已,說它們「簡直是…情書」。朱天文受寵於胡,至於寫〈黃金盟誓之書〉,都嫉妒如此,可見胡用情之深並不限於小女生。胡說過他自己「好像是沒有一定性別的」。「對於好的朋友,我幾乎同時兼有一種兄弟姊妹和師生的感情」。他對天文天心姊妹的用心是癡,對青年黎華標的用心,何嘗就不是癡?這就像《紅樓夢》裡,賈寶玉對於大觀園中諸姊妹丫環固然用心,對一些他所喜歡的男人也是如此。這點胡蘭成深知。他寫信給朱天文稱讚《淡江記》開了女子的新境地,因為朱「像賈寶玉的見一個愛一個」:
- 賈寶玉亦愛男人,如北靜王,蔣玉函,柳湘蓮。妳亦愛女子,…妳這樣汎愛,而各各愛到徹底…妳卻又是人在光天化日裡,不落色境。(〈照眼的好〉)
胡蘭成初與黎華標通信,接到黎寄來的照片,便把與幾個日本朋友看了,因不知能否幫助他到日本留學,輾轉思維,有如詩經裡的「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這樣的男人對男人的癡氣,朱天文禁不住酸溜溜地引張愛玲自傳小說《小團圓》中邵之雍─胡蘭成─的警句:
- 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都要發生」。(朱天文〈願未央〉)
總之,賈寶玉的癡氣,就是對於欣賞喜歡之人,不論其身分地位性別,用心得無微不至,甚至於甘為廝僕。胡蘭成對朱天文朱天心用心教導,口燥唇乾;對黎華標長期魚雁,契而不捨,其用心直可比王寶釧十八年苦守寒窯;所以我說他是有賈寶玉癡氣之人。
獃氣與癡氣相近,卻又不同。癡氣是對所喜之人的執著,獃氣則是對所好之人事物的無厘頭的稱頌。用朱天文的話,癡氣是「不喊停」,獃氣是「唯一級」,是「半點不怕的像一名賭徒把口袋裡的錢全部拿出來悉數押上」 (朱天文〈願未央〉)。《今生今世》裡張愛玲對胡蘭成說: 「你是人家有好處容易你感激,但難得你滿足」。「難得滿足」是痴氣,「容易感激」便是獃氣。
胡蘭成自己承認有賈寶玉的獃氣,這不須我多言,只看他寫給黎華標的信寄可:
- 你的這些地方,使我感動,這種感動可以《論語》裡的一節來表達。《論語》〈憲問第十四〉:「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此節書我是前些時為某某旬刊寫《論語》隨喜(連載,凡寫了一百多則,每則短不過數百字),才知其好。南宮适所說,亦不過是尚德不尚力的常言,但他是真心真意來說的,這就不同了,而且見得新鮮的了。當下孔子聽了,竟是只顧尋味,不曾回答。《今生今世》裡有張愛玲與我說《水滸》裡寫玄女娘娘是「寶貌妙目,正大金容」,當下我竟聽住了,尋味至於忘了神,要到第二天才與她說:「你的就是正大金容。」而且把那上句又忘了,又問了一遍,才曉得是寶貌妙目四字。「孔子不答」,便亦是這種呆氣。(賈寶玉見了寶釵褪香串給他時,露出的手腕,生得那樣好法,他竟看得呆了,林黛玉也頑皮,甩手帕到他眼上,嚇了他一跳,那呆氣的可愛乃至可敬,便亦在此。)… 顏子的不違如愚,與孔子之於南宮适之言,是如張愛玲所說的:「見了他,她的心變得很低,低到塵埃裡,從塵埃裡開出花來。」 … 我與張愛玲是前世一劫,除她之外,我是絕不與人說學問論文章的了。如今又遇見了你,也許我與你是前世兄弟吧?兄弟亦是五百年冤家。(《意有未盡:胡蘭成書信集》)
看了胡蘭成這段自白,我才完全了解他對小女生天文天心的讚語─把《擊壤歌》的飛揚說是像李白的詩,把《青青子衿》的激烈說是「古琴彈出來的,…像大海之水,滿蓄著震蕩,…所以能哀而不傷」之類。賈寶玉看晴雯撕扇子「嗤嗤」幾聲,便在傍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他聽劉姥姥講故事,講到大雪天外頭柴草響,講到「有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個小姑娘兒,梳著溜油兒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子裙兒…」被打斷了,他就「心中只惦記著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獃氣就是把撕扇和抽柴都可以執著想成是美極的音聲意像。 人謂胡蘭成的文字妖妍嫵媚,朱天文則說他多煽動語,我想講的就是把小善小佳極大化絕對化的本事。熱戀中的胡蘭成對「民國女子」張愛玲固然如此,「智慧老人」胡蘭成對黎華標朱天文朱天心等徒輩亦何嘗不然? 說胡蘭成有賈寶玉的獃氣,是比說他嫵媚要更肯定他的人格的。
胡蘭成在致黎華標信中提到朱天心〈綠竹引〉說: 「讀之使人思之不盡,…覺得寒子的美,美到了感動人,為了她我可以什麼都願意做」。又說
- 你信裡對女學生的態度,使我想起我在溫州教書時。我又想起小時的想頭,假使我所知的女人落難,我必定救她,又假使所知的女人成了殘廢,我亦必照常愛她敬她,乃至在路上見跛足的或乞丐的婦人,我都設想我可以娶她為妻,愛敬之念日新。此是年青人的感情,如大海水,願意填補地上的不平。亦因有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學生,皆映輝成為鮮潤的了,而要說是仁字,這亦即是你的仁了。
這種無厘頭的感情與其說是癡氣,不如說是獃氣。至於隨便看到什麼事物就說「亦是好的」就純是獃氣了,不免為寫《小團圓》時的張愛玲所駭笑,乃至於怕她死了他自有一番解釋,認為「也很好」,就又一團祥和之氣起來。
胡蘭成的獃氣,形之於文,就是所謂的胡腔,其影響至於三三諸人,特別是少女朱天文。《淡江記》裡頭多的是這種腔調。胡蘭成代序〈照眼的好〉便點出了許多例子:
- 這時候的太陽,芒花和塵埃,有著楚辭裡南天之下的洪荒草昧。
- 如果女孩兒必得出嫁,我就嫁給今天這陽光裡的風日,再無反顧。
-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我只是向中華民族的江山華年私語,他才是我千古懷想不盡的戀人。
賈寶玉被女人一虧便要作和尚去,胡蘭成起了想頭便要娶路人為妻,《淡江記》「像賈寶玉的見一個愛一個」的陽光少女動不動就要「心都碎了」。這些都是獃氣。
本文把胡蘭成和賈寶玉作性格上的類比,希望有助於我們了解他的所謂「妖氣」和他行文的嫵媚風格。
(完稿於2013年9月1日)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