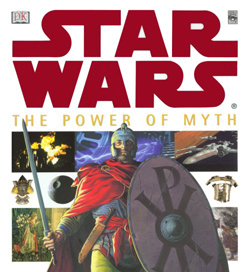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11/10 15:36:08瀏覽2492|回應0|推薦3 | |
文學是當代社會的神話,它所顯現的真實是社會關係的真實。即使是浪漫主義的抒情詩、現代主義的心理小說、意識流的作品,我們都可以從它的內容和形式當中檢視出社會的質素。神話不是個人的告解,更不是個人經驗或心理意象的陳述,它是人們在調整自己的欲望、行為與外在環境的關係時,所產生的種種集體經驗和感受的意象表現。藉著神話和儀式中的繁複而生動的符號,原始部落社會向它的族人傳達了亙古以來的訊息,這訊息在現實的社會結構中,常常是一種「禁忌」:因為它是一個矛盾、一個對立、一個衝突或一個歧義,因此它無法用語言或行動或其它在社會結構中有地位的符號系統來尋求明確的表現。神話是集體的夢,集體潛意識願望在這夢中才能達成。在現實社會結構的框限之下,人們某些深邃的意念無法獲得適當的伸張,它隱伏在制度和相應於這制度的約俗的符號系統的陰暗間隙。它同時是神聖的和污穢的、是想望的和禁制的,社會結構只能容許它在神話結構中得到虛妄的滿足,並在儀式過程中得到自我欺瞞的救贖。原始社會這兩中相關的符號系統,在歷史社會中變形為文字、藝術和宗教。
誠然神話與文學之最顯著的不同,在於我們從不知道神話的作者是誰,而一般相信它是社會集體的作品,甚至於我們可以認定它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創作」。人類學者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說:「不是人們在神話中思想,而是神話在人們無意識的心靈之中運作。」(註1)人們所能做的,只是選取他環境中的素材做為符碼,而任由神話的邏輯藉著這些符碼的排列組合來顯現它自己。文學作品雖然有一定的作者,但是神話的這種超越特性並未從它身上消失。任何個人都是活在社會中的人,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社會集體所分享的傳達工具。作者不但從他的時代環境中取得種種意象、概念和素材,更在他作品的形式、風格和調子中反映出了社會的影響。作者可以依照個人的造形意欲來陳述事件的發展而建構情節,甚至於建構在表面上完全與時代和社會無關的閉鎖的心理過程,但是如果我們打破作品之時間性或敘述性的展開順序,而去尋求那隱藏在符碼背面及符碼之間關係背面的結構和意義,我們終將得到所期望的社會質素,這質素表現了社會結構所無法解決矛盾和不許可言說的禁忌。 但是神話與文學仍有一項最基本的差別。神話所要尋求解決的矛盾,依照李維史陀的說法,不論它是宇宙關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或者是社會制度本身的矛盾,歸根究底都可以總結為一項大矛盾,那就是「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矛盾。在圖騰、神話和儀式的世界裏,各種不同的符碼將屬於「自然」的範疇和屬於「文化」的範疇層層疊疊地交錯在一起,原始人如是地以為藉此他們便「了解」了從自然狀態到文化狀態之間的過渡,也因之可以接受這過度的事實和由之帶來的衝突和痛苦。文學既然是神話在歷史社會中的變形,則我們透過「二元對立」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分析方法,從文學作品中檢視出來的衝突或矛盾,必然不會再是那史前「無歷史社會」的初萌的文化狀態和蒙昧的自然狀態之間的衝突或矛盾,而必須是存在於歷史不同階段的相續社會結構之間、在此結構所對應的文化狀態或符號系統之間的衝突或矛盾。換言之,文學作品的意義闡釋,將可以從社會結構的變動,以及人們在此變動中的迷惘、困惑、不安、焦慮和尋求解決矛盾及價值衝突的掙扎或努力來作為入門的途徑。
這種途徑,和馬克思主義又何關係?馬克斯區分社會的上層構造和下層構造,認為意識型態是社會關係的「鏡像」,「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反之,卻是人們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充當意識迷妄的揭示者,他藉著批判政治經濟學來批判所有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造成社會結構的變動,成文歷史個階段中這種變動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反映在歷代的宗教、文字、政治及其它的符號系統之中。他說: 「研究這些變動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那可以由自然科學精確決定的、生產之經濟條件所引起的物質變動,和那些人們由之意識到這衝突,企圖作戰到底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學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型態的各種形式,好好區別開來。正如我們對每一個人的評價不能根據那人自己對自己的意見一樣,我們也不能根據一個時代本身的意識來批判這改形的時代。相反地,我們必須以物質生活的矛盾、以存在於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來解釋時代的意識。」(註2) 於是,透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歷史辯證法的分析,不但宗教的神聖形像要被揭穿,更進一步地,「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探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註3)由此可以推論:對文學的批判就變成對社會的批判。 文學之於馬克思一如神話之於李維史陀:它們都是社會結構變動所由生的矛盾的反應和企圖解決這矛盾的努力,雖則這反映是經由集體無意識在人們心靈運作而這解決的努力是出之於妄想形式的。結構人類學研究神話和辯證唯物論研究文學使用著相同的方法,只是前者對象的基礎是無歷史社會而後者則是成文歷史的社會。神話世界所對應的社會是奠基於女人交易的親房關係和圖騰制度,而文學世界所對應的社會結構則是奠基於財貨交易的生產關係和階級制度。因此,民俗學者和經濟學者在對原始社會和歷史社會的批判上扮演著類似的角色。這一點,恩格斯早在一八八四年研究摩爾根 (Lewis Henry Morgan) 「古代社會」一書的著作中就已經提到了。恩格斯認為歷史的決定要素歸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可以分為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人類自身的生產兩種,在史前的社會中勞動不發達所以氏族的系帶支配了社會結構,在這基礎之上建立了摩爾恩所謂的古代社會;而當物質生產力發達起來,氏族的系代因著社會階級的形成而斷裂,取而代之的是以領土和財產為基礎的近世社會的社會結構(註4)。人類學者的研究填補了歷史唯物論者在成文歷史以前人類社會生活領域研究的空白,但也因之動搖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做為社會批判或文學批判之普通法則的效力:商品和商品價值的分析只是在近世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工商社會的批判中佔著優勢的地位,他們並不能代表所有人文活動的真實,僅僅以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來從事文學批判和社會批判是不足夠的,尤其是在我們把文學作為當代社會的神話這一認識之下。事實上,馬克思的學說在結構主義和符號運作理論的影響之下已經得到了新的解釋,這解釋與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有密切的關連。
設想在一場儀式中擺設在祭壇上的雕刻的木頭,或者觀察拉斯考克(Lascaux)洞穴中刻劃或彩繪在岩壁表面的形像,我們不能想像這些原始藝術是用來作為賺取剩餘價值的商品而不是原始人界定實在的最初嘗試(註5)。在工商社會中,供桌上的祖先牌位和客廳裏的裝飾壁畫是以金錢的代價購來,由之讓資本家和商人得到了再投資再生產的資本累積所須的剩餘價值,很可能因之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拉遠和階級鬥爭;雖然如此,我們卻不能抹殺人們在供奉、崇拜的儀式中所獲得的心靈平靜和欣賞藝術作品所帶來的情緒滿足。我們甚至可以承認馬克斯所說「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或者如庸俗的唯物論者所說藝術是有閒階級的高尚玩意,但我們卻不能否定一項事實,那就是:不論如何解釋價值結構的兩個部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商品這一概念本身有一定的限制。 事實上,經濟決定論只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斯的解釋。從沙特 (Jean Paul Sartre) 開始,人類的實踐行動 (Praxis) 或有目的行動變成歷史的中心也即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心(註6)。馬克思主義解釋文化現象最顯著的特色在於「自然」和「社會」之連續不斷的變形,在於人們與他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斷相互適應的過程。人類的實踐行動本質上是把一種人文秩序介入原屬自然的世界,最初這種實踐行動藉著財貨之生產和分配的社會過程來達成,但是在這社會結構之上的符號和意義的領域-也即文化領域有其創造性和再生產性的功能(註7)。可以說: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環境的時候建立了一定的社會結構,在這結構之上產生了相對應的符號系統和意義、價值系統,但在同時,人們的行為和相互關係也受到這文化系統的影響,而使得自然環境和社會結構發生再度的變形。在這種理論之下,生產財貨的活動和創用符號的活動有著對等的地位,而社會結構充作二者的媒介。如果我們如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般推廣符號的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認為財貨或商品,在其從自然的範疇過渡到文化範疇的過程中,由於人文形式的介入,也只是一種特殊的符號。符號在不同的社會結構有不同的價值:在原始社會中,符示血緣關係的圖騰符號也許是最有價值的,而在資本主義的工商社會中,商品符號的價值以金錢的形式表現出來,達到了一種空前的程度。
在社會結構中有地位的,在符號系統中便有其意義和價值;在社會結構中沒有地位或失去其地位的,便沒有明確的符號來符示它或者它的符號將逐漸湮沒在其它有價值的符號之間,這就構成了前面所說的「禁忌」。在原始社會中,禁忌擁有一種危險的「馬那」 (mana) 的魔力,觸犯他的人將受到嚴重的懲罰(註8),這是因為原始禁忌牽涉到從自然狀態到文化狀態的神祕過渡。人們在初離混沌的社會結構中對過去的狀態懷著一種依戀和恐懼的矛盾感情,這矛盾感情表現在如圖騰崇拜、圖騰禁忌和屠殺圖騰慶典等許多神話和儀式當中。神話和儀式因此有別於社會其它的符號系統,他們並不是直接地符示社會結構,不是以符號的價值和意義來作為社會地位的指標;相反地,它們符示社會結構的陰暗面,將那與現實社會結構衝突、矛盾而無法宣示的一面隱藏在它們自己的結構中。原始人的無意識心靈因此獲得平衡,錯綜複雜的情緒因此得到宣抒。文學的美學價值亦根基於此,歷史社會中一定階段的社會結構必然蘊含了前一階段某些價值的失落,乃至於某些屬於自然範疇的永恆價值的失落,這些失落的價值便變成當代社會的禁忌,而文學則繼承了神話的功能,使人們在一個分化、層化的社會結構中獲得超昇:從破碎、疏離中追尋完整,而使衝突、激擾的情緒得以靜滌。 文學因此不只是商品;商品只能明確地符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而文學則隱隱地符示了任何社會結構所欠缺的東西。商品由於它所包藏的剩餘價值將促使社會結構更趨向於分化碎裂,而文學則由於其靜滌功能使得人們的心靈平息和諧。在工商社會中,商品幾乎成了這個社會結構唯一有意義、有價值的符號系統,受到人們的膜拜和無比的尊崇,而不能成為商品的東西或者低價值的商品便隱伏在社會的陰暗角落,逐漸為人所漠視遺忘,這個時代的文學,便負有無比重大的責任來履行它的符示任務。 但是如果把文學的功能限制於它的美學功能,則文學便淪為馬克斯所說的宗教,而月讀和寫作淪為這這宗教的儀式:被社會結構所物化的人們在其中嘆息和宣洩感情,因此在儀式之後便滿足地重返原來的社會結構。如此,文學將和神話一樣,只能虛妄地解決現實的矛盾。 神話由於不是有意識的創作,因此必須透過繁瑣的「解碼」程序才能有意識地了解它的意義,雖則原始人在無意識中已能感受到神話的功能。在歷史社會中,神話之自律自足的「無意識」已為歷史之自律自足的「無意識」所取代:歷史過程所造成的社會結構變動在個別作家的作品中無意識地被符示出來,所以馬克斯說:「人們創造歷史,但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創造它」(註9)。但這句話另一個隱含的語意是:馬克思主義自視為一種無意識的歷史過程之意識的表現;在歷史發展之最深刻需要的時候,時代的無意識透過革命群眾而意識地表現出來(註10)。這樣的時代中,文學和藝術必須從繼承自神話的無意識性中覺醒過來,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說: 「這種藝術需要新的自覺意識,它特別要與神祕主義-不論是明白的神祕主義或是裝扮為浪漫主義的神祕主義-對立起來,......新的藝術要反對悲觀主義、反對懷疑主義以及其它種種精神頹喪的形態,它是現實主義的、活潑的級生動的集體主義的,它充滿了對未來之無限開創性的信念。」(註11)
在人類的實踐行動中,藉著符號的使用,人們把自己和自然隔離開來,形成了人文世界。神話是這樣的一種符號形式:原始人在其社會結構中,把某些根植於其自然本能的希望和恐懼,用一種特殊的組織方式,變形成為神話意象而符示出來(註12)。神話因之是一種自然的召喚,它不斷地從社會其它符號形式的間隙和禁忌中勾惹著人們對於混沌狀態的追憶。神話也因之是一種非理性的力量,當其它理性力量衰弱時,它即捲土重來,君臨著人類的文化和社會生活(註13) 。文學和藝術,如果只是如佛萊(Roger Fry)所說「由某些極其深沉、極其曖昧而且無限普遍化了的種種追憶之覺醒中取得其力量」,只是「喚起了被生活之各種不同情緒遺留在精神上的種種殘餘痕跡,但卻不致於喚起真實的經驗」(註14),則他將永遠只是當代社會的神話,教人們從理性中退縮,在幻覺中逃避真實世界的痛苦。 實踐行動不是一種消極的過程而是一種積極的過程,不是一種被決定的過程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再生產的過程。原始人最初採集食物、生產財貨、繁衍種族固然是因為自然本能的需要,但是一旦以人類的方式規定了自然界的秩序,自然即失去了它的當下本然的面目:人類注定只能不斷發揮生產和創造的理性力量來尋求「完整性」的重敘,而不是從現實社會結構的矛盾和衝突中尋求非理性幻覺的慰藉。 文學,甚至現實主義文學,因之必須發揮理性符號形式之引導性的功能,而不能僅僅沉迷於對於逝去價值的懷念和對於現實苦難的反映。文學必須超越神話;如果說「哲學家只能多方解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註15)是對哲學的一種譏諷的話,那麼,如何免於同樣的譏諷正是文學必須記取的教訓。沙特說:「為時代而寫作並不是要消極地反映時代,而是要去持續或改造時代,以此超越它走向未來。」(註16) 附註
(1979年完稿於台北) |
|
| (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