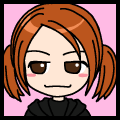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9/08/12 15:30:11瀏覽632|回應1|推薦18 | |
午後一點半,開了冰箱,只看見一鍋兩天前煮好的瓠瓜湯。取出冰透的生菜沙拉,拌了一點優格權充午餐(或者說下午茶)。並非有意進行這樣的「輕食計畫」,在攝氏35度的房間裡,我滾燙的胃嚴重排拒除了這樣清爽的「低卡路里食物」之外的食品,雖然認識我的人都清楚,我比較需要補充高熱量食物。 翻翻行事曆,才想起距離上次到公司已是三個星期前的事了。看著還不到盡頭的低迷景氣,倦怠像瘟疫在生活中快速擴散,不停趁危襲擊茫然的心智。所有用品已打包運進父親購置的新居,屋內忽然顯現出家徒四壁的樣貌,廚房除了冰箱,一無長物,只剩年久失修的屋頂每逢雨季就滴滴答答把屋裡下成個具體而微的熱帶雨林,蟲蟻鳥獸紛紛現形,唯有酷暑,小傢伙們四面八方竄逃了,才能圖個清靜。 再開冰箱拿了鮮奶,壓縮機嘎嘎叫個不停,天氣實在太熱了。七歲起在此落腳,度過二十幾個顛簸的溽暑,怎麼偏偏就是這個夏季特別難耐? 緩慢踱回房間,燠塵在盛開的烈日下擾擾攘攘,揮之不去。 以為只有記憶裡,台北城柏油路滾燙熔化的溫度才讓自己暈眩不安,南行的熱浪從未擊倒過我,我是屬於夏季的,驕陽的女孩,憶童稚時,吹電風扇就感冒天寒就頭痛吃冰也腹瀉的難養 ,忽然在踏入成人世界後,因為一種入境隨俗的逼迫而莫名痊癒;只是,對熱的遲鈍已然成為一種無法阻止的體質,枝藤蔓生,糾結不開,也造成肉身對感官在某種程度上的過於敏感,季節更迭的大好大壞,都使我無法拒絕,甚至失去承受這個世界的能力與抵抗力。 汗水浸透外衣,皮膚的殷紅斑塊如江河潰堤成災。醫生謹慎審視著這片反覆被侵城掠地的版圖:「汗疹又復發了喔?開個藥膏擦就可以,記得盡量保持身體乾爽,多處在陰涼的地方,會癢的話不要抓容易留疤。下禮拜回來複診。上次的過敏退了吧?毛囊炎的問題跟櫃檯買X牌的藥膏定時擦就可以。」 向晚出了診所,回家的路上繞阿繞,胃酸的警告讓我去7-11買了奶酥麵包與冰咖啡。 當一個人感到餓的時候,絕無餘力思考所謂的永恆宿命;宿命,是給活著的人拿來說嘴的東西,對於極度飢餓人,一塊麵包已是極美的救贖。確實肚子餓,卻完全食不下嚥,甚至有超過一天未進食,只喝一杯鮮奶的紀錄。一切都是因為器官感知的失調導致,不是不明白,卻無能為力,感覺到身體的衰弱的同時,思維卻愈趨明朗,很矛盾。我確知我的衰弱,但無法阻止衰弱在體內肆虐崩毀。也就在這無能為力因而罹患夏日憂鬱的時日裡,我默默地瘦了下來。 友人叨念著我的身體狀況,關切我的吃食。貢丸兩顆、燙高麗菜一碟,馬鈴薯沙拉一小碗。 「連吃個東西都要走極簡路線,難怪老是這樣瘦巴巴的呀。」 他又如何能相信,我的食慾與食量與生俱來,只是隨天候時而改善時而惡化,像無法痊癒又不致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可能得花一輩子的時間與它纏鬥?雖然我從有意識開始就不停催眠自己必須正常進食而且從來沒有成功過,也一直盡力尋求調養之法,總也無解,也逐漸疲倦,最終接受並與它共存。 繼續惡化,我的皮膚我的胃我的心,但我仍舊寧願將所有的一切停留在沸騰的夏季。比起嚴寒的冬季(現今似乎已少那樣難以忍受的冷),汗涔涔的世界仍是我更加願意去接近甚或投身而入的,熱度難免使我焦躁,沁骨的冷才是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颱風迫近的關係,夜終於涼如水,體表肆虐的斑塊開始有著緩緩消退的意圖。穿上薄外套走到陽台,溫度計難得停在攝氏29度。輾轉入睡,直到夜半的狂風暴雨將我吵醒,起身關了窗,隱約感到什麼不安。早晨,頭痛得幾乎無法起身,下腹翻將起來,我在床上蜷曲了半晌,全無半點食慾,跟著風雨中的台灣一樣陷在天旋地轉的困境裡,災情慘重。 「妳阿天生沒口福,天氣太熱吃不下,現在生理期又著涼,什麼時候才能好好吃頓飯呢?」母親心疼地抱怨。我想,我只能安慰自己仍然平安,比起風災中流離失所的人民,這點不適根本微不足道。涼颼颼的早晨,心卻開始沸騰,感到平凡的生活其實是最珍貴且神聖的。 這樣半放逐的日子,是該有另一種鬆散但不失健全的生活方式。父親在樓下叫喚,我迅速起身,為父親備了藥、泡了牛奶,給自己倒杯柳橙汁,打開昨夜尚未讀完的書(它像是某種緩解劑),彷彿憂鬱與不適只是一種展示苦悶的顯影。爾後我將會在反覆發作、痊癒的過程中,培育出某種對付惡性情緒的抗體。 這些日子以來,這樣的循環成為我精神的砥柱,恆定不變,直至新生活開啟之前,皆應如是。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