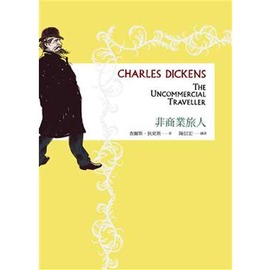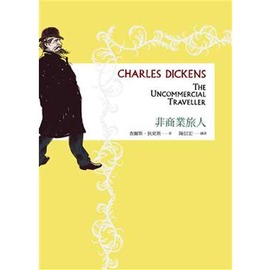
幾年前,我因為心中煩惱,一時無法入眠,而連續幾晚整夜漫步於街道上。我若是躺在床上對抗此一失眠的狀況,恐怕得花上很長一段時間才克服得了;但由於我在躺下之後隨即起床、出門漫步,直到日出才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結果很快就治癒了這個毛病。
在那幾夜裡,我完成了業餘流浪經驗的教育。我主要的目的在於度過漫漫長夜,這樣的努力使得我和那些每夜都必須奮力追求此一目標的人士建立了同病相憐的關係。
那時是三月,天氣潮溼、陰鬱又寒冷。由於日出的時間不會早於五點半,因此在午夜十二點半——也就是我開始與夜晚奮鬥的時候——感覺上距離天亮仍有很長一段時間。
大城市的忙碌躁動,以及其入睡之前的喧鬧翻騰,是我們這些流浪漢在入夜之初所能夠獲得的其中一項娛樂。這樣的現象大約持續兩個小時。隨著深夜酒館熄燈歇業,侍者將最後一批喧嘩不休的醉鬼攆到街上之後,我們就不免喪失許多同伴。在這之後,便只有零零散散的車輛與行人陪伴我們。我們若是運氣夠好,也許會聽到警察呼叫支援,並且看見一場幹架;但整體而言,這樣的餘興節目極為罕見。除了在赫馬基特(Haymarket)——倫敦秩序最混亂的地區——以及自治市(Borough)的肯特街,還有舊肯特路的其中一個路段之外,夜晚的平靜其實很少遭到襲擾。
然而,倫敦卻彷彿模仿著其中個別的市民一樣,在入睡之際仍不免偶爾騷動一下。就在一切歸於平靜之後,若是有一輛馬車隆隆駛過,接著必定又會有五、六輛跟在後面。我們這些流浪漢甚至也觀察到,醉酒的人對彼此似乎像磁鐵一樣具有吸引力,所以只要看到一名醉漢蹣跚著徘徊於一家商店前,即可知道再過不到五分鐘,必定會有另一名醉漢拖著腳步過來,兩人也許一見如故,也可能扭打起來。
在種種醉漢當中,除了手臂細瘦、臉龐臃腫、有著鉛色嘴唇的琴酒酒鬼最為常見之外,若是看到另一種較為罕見的類型,也就是外表比較體面的醉漢,那麼這人身上多半穿著骯髒的喪服。夜裡在街道上看見的景象其實與白天一樣。平民百姓若是無意間繼承了一筆財產,通常也不免無意間沾上一點小酒。
這些細碎的活動終究不免歇止——包括某些賣派餅或熱馬鈴薯賣到深夜的小販——然後倫敦就會真正陷入沉睡當中。這時候,流浪漢最渴望的即是同伴,哪怕只是一抹燈光、一絲動靜、任何一點還有人尚未上床就寢的跡象——甚至,只是醒著也可以,因為流浪漢的眼睛也會四處尋找窗戶裡的燈光。
在輕輕灑落的雨中,流浪漢仍會在街上持續不斷地走,眼中所見唯有盤雜交錯、看不到盡頭的街道。不過,偶爾也會在街角看到兩名警察站著交談,或是一名警官或督察督導著部下。
在一種極為罕見但仍不免偶爾發生的情況下,流浪漢也會在夜裡看到身前不遠處的門口探出一顆頭來;一旦走過去,則會發現原來是有個人直挺挺地隱身在門口的陰影內,顯然已打算對社會毫無貢獻。
由於某種好奇的心態,同時也保持著符合當下情景的死寂靜默,流浪漢與這名男士會從頭到腳仔細打量對方,然後什麼話也不說地分開,彼此懷著猜忌。滴,滴,滴,壁架與屋簷不斷滴落雨水,水管與排水口也一再濺出水來。不久之後,流浪漢的身影就會投映在通往滑鐵盧橋的石板路上,原因是他寧可花半便士的錢,以便有個機會能夠和通行費收費員說聲「晚安」,並且瞥一眼他取暖的火堆。
一堆旺火、一件厚實的大衣和一條溫暖的羊毛圍巾,只要看到通行費收費員,就能夠看到這些令人感到舒服的物品;此外,他那充滿生氣的模樣更是絕佳的同伴。只見他將半便士的零錢叮鈴噹啷地撒落在他那張金屬桌子上,彷彿悍然蔑視這充滿了哀愁思緒的夜,也毫不在乎黎明的來臨。
站在橋口,其實需要一點鼓勵,因為橋上看起來極為陰森。在那幾個夜晚,那個遭到謀殺分屍的受害者還未被人用繩子吊著從欄杆外垂下;當時他還活著,想必也睡得很平靜,沒有受到任何不祥的噩夢侵擾。
然而,泰晤士河的河水看起來頗為恐怖,岸邊的建築物都籠罩在陰暗當中,映照於水上的光線看似來自水下深處,彷彿是自殺者的鬼魂持著燈光,標示著他們的落水地點。狂野的月亮和雲朵躁動不安,像是良心不安的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一樣,而且整個倫敦的龐大陰影也彷彿沉重地壓在河上。
滑鐵盧橋距離兩座大戲院只有幾百步之遙,因此接下來遇到的就是這兩座戲院。猶如乾涸的大井一樣的戲院,其內部在夜裡一片肅穆漆黑,顯得寂寥不已:一排排的臉龐早已消失,燈光也已熄滅,座位空無一人。在這樣的時刻,戲院裡恐怕只有約利克(Yorick)的頭骨還認得自己。在我的一次夜間漫步裡,教堂尖塔上響起凌晨四時的鐘聲,迴盪在三月的風雨之中。
當時我正行經其中一座有如荒漠的戲院旁,而走了進去。我手上提著一個光線微弱的燈籠,循著我熟悉的路徑摸索到了舞台上,跟前的樂池如同瘟疫盛行時期挖掘的萬人塚。我望向樂池前方那個龐大陰鬱的洞穴,水晶燈和其他的一切一樣毫無聲息。在瀰漫著霧氣的空間裡,唯一可見的是一層層的燭淚。我腳下踩著的舞台,在我上次造訪戲院的時候,曾有那不勒斯的農民在這裡舞動於葡萄樹間,完全無視起火的山可能將他們吞噬。
現在,舞台的地板上只有一條粗大如蛇的消防水管,彷彿充滿戒備地等待著那狡詐如蛇的火焰,只要一見到火舌冒出,就會立即加以撲擊。一個有如鬼魂般的守夜人,手上拿著一根枯瘦的蠟燭,在遙遠的上層包廂出沒了一會兒便即消失。我朝著舞台裡端走去,對著拉起的布幕舉起燈籠——這時布幕看起來不再是綠色,而是像黑檀木一樣黑——我覺得眼前一片陰暗,彷彿身在地窖裡,只隱隱看得到舞台後方堆著一團猶如船難殘骸般的帆布與繩索。我覺得自己就像個身在深海底部的潛水夫一樣。
在凌晨時分,街道上杳無人跡,這時行經新門監獄(Newgate Prison)可以為人提供一些省思的材料,同時也可摸摸那粗糙的石壁,想想那些正在睡夢中的囚犯,再從守衛室那設有尖刺的邊門上朝內眺望,窺見獄吏的火光與燈光映照在白牆上。在這種時刻,也頗適合徘徊於那道陰森的欠債人之門旁邊——這道門關閉得異常緊密,是許多人迎向死神的通道。
過去,許多鄉下人禁不起誘惑而蓄意使用面值一鎊的偽鈔,結果數以百計不幸的男男女女——其中許多都頗為無辜——就這麼告別了這個殘酷無情又反覆無常的世界,而且那邊那座聖墓教堂(Church of Saint Sepulchre)的高塔就聳立在他們眼前!在過了許久之後的今天,銀行大廳在夜裡會不會縈繞著過去那些銀行主管心懷愧疚的魂魄,還是就像老貝利街上這片沒落的刑場一樣寂靜?
接著,順道可達的下一個景點是英格蘭銀行,可以讓人憑弔美好的昔日以及哀嘆當前這個墮落的時代。於是,我就這麼走,在我的流浪行程中造訪這座銀行,思索一下裡面收藏的財寶;我同樣也會造訪在那裡過夜的衛兵,在火堆前向他們點頭致意。
接下來,我走向比靈斯門(Billingsgate),希望遇到市場的人,但終究發現時間還是太早。於是,我穿越倫敦橋,走到薩里那一側的河畔,穿梭於釀酒廠的巨大建築之間。釀酒廠裡面頗為忙碌;濃烈的酒味、穀物的氣味、豐腴的拉車馬匹在馬槽前躁動不停的聲響,實在是寂寥中絕佳的同伴。
它們的陪伴讓我感到神清氣爽,因此我又打起精神再次出發,把我面前那座王座法院(King’s Bench)的老監獄設定為下一個目標,並且決心在走到牆邊的時候,好好思考一下可憐的賀瑞斯.肯曲(Horace Kinch),以及發生在人身上的乾腐病。
發生在人身上的乾腐病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疾病,而且初期很難診斷。這種疾病導致賀瑞斯.肯曲被帶進王座法院的老監獄,並導致他被人抬著出來。他相貌俊美,正當盛年,富有又聰明,而且受到眾多朋友的喜愛。他娶了個門當戶對的妻子,也生了健康又可愛的子女。
然而,如同某些外表亮麗的房屋或船隻,他也染上了乾腐病。在人身上,乾腐病最早的外顯症狀就是四處遊蕩的傾向;毫無理由地身在街角;看到他的時候總是忙著要到什麼地方去;到處遊走,卻沒有一個地方是自己的目的地;鎮日無所事事,只是一直覺得自己明天或後天有什麼事情要做,卻又說不出具體的事項。旁觀者一旦注意到這種症狀,通常會與過去的模糊印象聯想在一起,以為是患者生活過得太勤苦了一點。
旁觀者還來不及仔細思考,懷疑對方罹患了「乾腐病」這種可怕的疾病,就會注意到患者的外表開始出現每下愈況的情形:一種邋遢頹唐的模樣,不是因為貧窮,不是因為塵土,不是因為喝醉酒,也不是因為健康不良,而只是單純因為乾腐病。接下來,患者身上會出現酒味,而且是在上午時分;接著對金錢顯得漫不在乎;接著是身上隨時都帶著濃重的酒味;接著對一切事物都顯得漫不在乎;然後是四肢顫抖、精神不濟、情緒低落,乃至整個人的崩潰。乾腐病在人身上就和在木材上一樣,發展速度快得難以計算。
一旦發現一塊木板染上了乾腐病,整座建築就都不得倖免。不幸的賀瑞斯.肯曲就是如此,而在不久之前以一小筆錢下葬。認識他的人說:「這麼富有,社會地位這麼高,前途又這麼光明——只可惜,稍微染上了一點乾腐病!」但話才說完,看!他就已經徹底遭到乾腐病所吞沒,化成了一堆塵土。
在那幾個流浪的夜晚,那道死寂的牆壁總是讓我聯想起這起眾所周知的事件。接著,我選擇的下一個遊蕩地點是伯利恆醫院。之所以這麼選擇,一個原因是這所醫院位於我前往西敏的路途中,另一個原因則是我的腦袋裡有個夜間奇想,最適合望著這所醫院的牆壁與圓頂思考。
這個奇想就是:神智正常的人一旦進入睡夢中,和瘋子是不是就沒有兩樣了?在這所醫院之外的我們,每晚做夢的時候,不是都與醫院裡的那些人處於相仿的狀況下嗎?正如他們每天都置身於瘋狂的妄想當中,我們每晚不是也荒謬地幻想著自己悠遊酬酢於帝王后妃與王公貴族之間?我們每晚不是也都把各種事件、人物、時間與地點混雜在一起,就和那些病患一樣嗎?我們有時候不是也對自己睡眠中的胡思亂想感到困擾,而氣急敗壞地想為那些怪異的念頭找出解釋或藉口,就像那些病患有時候對自己清醒之時的幻象也是如此?我上次身在這麼一所醫院裡,曾有一名病患對我說:「先生,我經常可以飛。」
我慚愧地心想,其實我也可以——在夜裡。那次也有一名女子對我說:「維多利亞女王經常過來和我一同進餐,女王陛下和我都穿著睡袍一起吃桃子和通心粉,王夫殿下還身穿陸軍元帥的制服騎馬前來陪伴我們。」聽到這句話我也不禁臉紅,因為我記得自己也曾舉辦宴會招待王室貴族(在夜裡),在桌上擺設豐盛不已的菜餚,而且我在那些華貴的場合上也表現得極為得體。我心想,那知曉一切的大師,既然將睡眠稱為每天人生中的死亡,不曉得是不是也會將夢稱為每天理智中的瘋狂?
這時候,我已將醫院拋在身後,再次走向泰晤士河,才一會兒就踏上了西敏橋,讓我這雙流浪漢的眼盡情欣賞國會大廈的外牆——這個巨大體系發展完美,這我知道,也是周遭各國與後代仰慕的對象,這點我毫無疑問;但這個組織若能偶爾受到鞭策而好好運作,也許會更好一點。
轉進國會大廈旁的舊宮庭院(Old Palace Yard),這座立法殿堂陪伴了我一刻鐘,低語聲暗示裡面還有不少人醒著,對不幸的陳情者而言,凌晨時分在這個地方更是顯得悲慘而恐怖。西敏寺也是個陰鬱但怡人的同伴,一樣陪伴了我一刻鐘;其陰暗的拱廊與梁柱之間埋葬了許多名人,而且每個世紀的人物都比先前更加引人驚嘆。在那幾個夜晚的流浪漫步中——我甚至也造訪了不少墓地,其中都有看守人定時巡邏,還必須扳動指針,以記錄他們巡邏的時間——我不禁肅然想到這麼一座古老的大城當中有多少死者,而且他們若是在活人安睡的時候全被喚醒,那麼所有的街衢巷道必然擠得水洩不通。不僅如此,這支幽靈大軍還會瀰漫到城市之外的丘陵與谷地,再繼續向外延伸,天曉得範圍會有多廣。
在死寂的夜裡,每當教堂鐘聲響起,流浪漢也許會誤將其當成同伴而予以歡迎。不過,隨著音波的振動向外傳出——在那種時候可以清晰感覺得到這樣的音波傳遞——不停朝著無盡的空間擴散而去,流浪漢就會意識到先前的認知錯誤,而發現寂寞感其實會因此而更加深沉。
我離開西敏寺後轉向北方,在三點鐘響之際來到聖馬丁教堂。突然間,一個差點被我踩到的東西從我跟前揚起,同時隨著鐘聲發出一道流浪漢的孤獨嘶吼,我從來不曾聽過那樣的聲音。就這樣,我們站著面對面,對彼此都心懷恐懼。
那個人看起來像是個二十歲的年輕人,蓄著兩道濃眉和一道髭鬚,身上披著一團鬆垮垮的破爛衣衫,用一隻手抓著。他全身不停顫抖,牙齒格格作響,一面瞪視著我——不論他認為我是迫害者、惡魔、鬼魂,還是什麼東西——一面張開他那不斷呻吟的嘴巴,彷彿想要咬我,猶如一條充滿憂懼的狗兒。我有意拿些錢給這個醜陋的人物,於是伸出手要他稍安勿躁——因為他往後退縮著,一面呻吟,一面作勢張口咬人——然後將手搭在他的肩上。就在這時候,他卻身子一扭閃了開去,就像《新約聖經》裡的那個少年人,只剩下那團破爛衣衫在我手中。
在開市日的早晨,柯芬園市場總是絕佳的同伴。一大車一大車的甘藍菜,底下睡著農夫的老少員工,還有來自菜園鄰里的精悍狗兒在旁看守,感覺上就像派對一樣熱鬧。不過,我在倫敦的夜裡見過最醜惡的景象,就是在這個地方遊蕩的兒童。他們睡在菜籃裡,爭搶殘骨碎肉,只要看到能偷的東西就撲上去,潛行於板車與推車底下,閃躲著警察。他們的赤腳隨時都在廣場的人行道上踏得劈啪作響。面對這樣的情景,迫使人不得不比較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果菜與那些小野人的腐敗狀況,也不禁得到一個痛苦而不自然的結論:果菜受到大幅的改善與精心的照顧,那些小野人卻完全無人看管(倒是無時無刻一再遭到追捕)。
柯芬園市場在清晨就有咖啡可以喝,所以又為流浪漢提供了另一個同伴——更令人欣喜的是,還是個溫熱的同伴。在這裡也可以吃到用料紮實的吐司:儘管在咖啡館的內室裡,一頭亂髮的老闆還沒把外套穿上,而且仍然睡眼惺忪,因此每端出一份吐司和咖啡,就會返回隔間後面,陷入一片此起彼落的打呼聲裡,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一天清晨,我在弓街附近的這麼一家咖啡館裡,端著我的流浪漢咖啡坐在座位上,思索著接下來該往哪裡去。突然間,一個男人走了進來。他身穿黃褐色高領長大衣,腳上蹬著鞋子,還有一頂帽子。儘管他的帽子外表看來毫無異樣,他卻從中抽出了一大塊冷肉布丁。那塊肉布丁非常大,塞滿了整個帽子,還把帽子的內裡也拖了出來。
這個神祕人顯然人人都知道他的布丁,因為他一進來,睡眼惺忪的老闆就為他送上了一大杯熱茶、一小塊麵包,還有一把大刀以及叉子和盤子。他獨自坐在包廂裡,把布丁放在桌面上,但沒有切,而是把刀子高高舉起,然後一把刺進布丁裡,彷彿那塊布丁是他的死敵一樣;接著,他把刀子抽出來,在袖子上擦了擦,再以手指撕裂布丁,全部送進嘴裡。
我一直忘不了這個身懷布丁的男人,他是我在流浪旅程中見過最如鬼似魅的人物。我到那家咖啡館只有兩次,但兩次都看到他悄無聲息地走進來(看起來像是剛下床,而且立刻又要回到床上),拿出布丁,一刀刺下,抹淨刀面,然後把布丁全部吃光。
摘錄自 衛城出版《非商業旅人》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