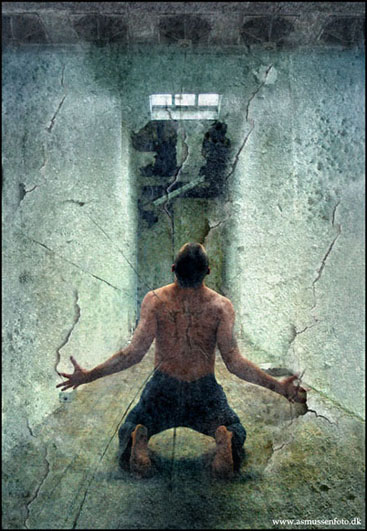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7/02/10 21:15:07瀏覽1084|回應1|推薦16 | |
一個有酒有煙的夜晚
短篇小說 [下] 「然後就開始了你的江湖路?」 「嗯,未成年也關不了多久,出來後大家都知道我狠,跟著我,就越混越大。混得大,想來挑戰你的人就多,那你就得更狠更凶。 那麼多年過去,不管江湖上的地位,不管混得多大帶了多少人,當我面對一個做出讓我憎恨事情的人時,我還是會有那麼感覺,就是不解,不解你為什麼能夠做出這樣的事,我想痛罵他無恥、卑鄙,但我沒有時間沒有機會,通常這樣想的時候我的刀就砍下去了。」 「 無論如何,在江湖上你興哥還是有很好的名聲呀,警方也對你很禮遇。」 「我不知道,到了後來,我常想,尤其進來後這段時間裡更想知道,我為什麼殺人,而且有些人事後想想好像也罪不至死。我有一種感覺,就是我在跟他述說、溝通或是譴責。我殺人,因為我說不清楚,我無法用言語完整形容出我要對他表達的意義所以我殺他,所以,我在對他表達。」 「這樣的話,就是你覺得用『語言』表達是件很累的事,所以,你殺人?」我問。 「這段時間裏,我努力回想過去,在紙上寫著,自問自答。我忽然覺得人與人溝通的問題才是世界上一切事的根本問題。純善與純惡的人、的事很少,大多衝突都是我們對語言溝通感到疲憊,認定別人不會真的了解你的真實感覺與你要表達的東西。才會用一種無理,只講求『直覺』的行動,就是暴力。 其實人都是排斥語言溝通的,怎麼不會?那只是一種不得不的辦法而已。我們念書,學習,其實都只是要我們接受用語言與其它人溝通,也學習更好的語言溝通方式。沒念過書,沒知識的人的人都用非常粗暴的語言與其他人互動,如果可以他們跟本不想用語言。」 「這倒很有趣,聽聽似乎還滿是一番道理的,興哥,你覺得我們其實都是不想說話的?」 「不是全部也是很大程度吧,說話只是不得不的手段,只是要達成其他更重要的事的手段。你看,活著的幾件最重要的事須要不停說話嗎?相愛的人做愛、接吻、會覺得那一切什麼都不必說了。吃飯、睡覺,也沒必要說話、甚至大小便也不須要的。生命必須的事都是不須言語。 還有,我們不想說話,其實我們更不想聽別人說話,所以有時我們說話只是不想聽到其他人說話罷了。 唉…..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很疲倦,到了後來,每一天的每一個日子都在與語言戰鬥,我變得更為暴躁,對敵人更殘忍,因為我對所有人之間溝通的方式更煩惱茫然了,我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告訴自己與旁人,我的真正想法與做法。我變得很孤僻,非常沉默,而當一個殘酷的人變得沉默時,身邊所有人都會開始害怕,不知道這恐怖的寧靜是不是為了自己,暴力變得無法預測。我的人也不敢靠近我,以致於後來被自己人出賣…… 倒是進來後,我能靜下來好好想想,好好把想不透糾葛在一起的東西寫下來,覺得清楚了不少,說話變得不那麼可怕了……算了,我也搞不懂我在講啥肖,你就當我酒醉胡亂講吧!來,乾了。」
鋼杯碰擊的聲音混頓不乾脆,興哥皺著眉喝下酒,長嘆一聲,把煙屁股向窗戶彈去,卻因窗戶太高沒成,碰到牆彈了回來。
「興哥,其實,人為什麼要用毒呢?就是因為不想與人溝通。 用毒之後,整個人不再有理智什麼的,與世界之間所有一切都失去關係,自我就是一切,是無限大的,世界是依照自己的規則組成的。我覺得那個時刻可以說是在與自己做愛、擁抱。 那種感覺真的像與另一面的自己對話,那個陰暗,渾沌不清的自己平時在潛意識裡翻雲覆雨,主導了我們許許多多的好惡與對事物的反應,這時終於具體地,站在你前面,對你述說你與現實之間真正的位置,但你是聽不懂的,只能體會,但是你在那個高潮的過程裡卻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任何誨澀無以名狀的東西原來都與你自己有對應關係。但是你已經了解的人事物卻往往不是那回事,它們時常只是與其他人事物的攪在一起,它們的樣子只是你的幻影,只是你的虛構,你跟本從來未曾認識它們。」 「呵呵……這樣的毒好像成了心靈解藥,看清楚一切事件的真實面。」 「那又如何,既使它真的能讓人如此清楚的看清楚,人也不可能活得如此純粹而且真實。」 「所以,會用毒成癮的人是否只是想活得純粹,什麼都不須要溝通,也不必努力爭取,只要那單純的快感?」 「是吧,可是那種快感終是短暫的,不久後還是要回來面對被毒侵蝕後更苦澀的人生。」我說。 「如果可以時間倒流,你會不會不搞毒品了。」興哥問。 「很難說,如果…….重點是時間就是無法倒流,我們無法去確認如果我們做什麼或者我們不做什麼會比較好或者比較不好。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時間能夠倒流,讓我們家的生意不要倒了就得了吧!」 興哥笑笑,喝了一大口酒,說:「如果可以重來,我想當個作家,寫作的人,寫文章寫小說都好。我用文字清清楚楚表答我想的意思,有條理的,有內容的,我不須要不停地用薄弱的語言去讓人了解我真正的憤怒、狂歡或恐懼。要攻擊我反對我的,也請你用文字,否則我看不見。做一個作家或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寂寞人吧!」 「興哥,很意外你會這樣想,你真的很特別,去認真思考活著的這回事。」 「我只是被自己撒下的迷障困住的笨蛋而已,在躲藏的段時間裡,有次在電視上看到一部電影,是說一個有名的性變態,他總是寫,不停地寫,寫什麼?就寫性變態,他好像是個貴族,就是因為他的特殊興趣加上總是寫那種東西就被逮捕,在監獄關到生蝨母 (註六)。」 「你說的那個人叫『薩德』,是法國貴族。」 「嗯,薩德。 關他,他寫得更兇,更異端,沒收他的筆,他就用手沾糞便寫在紙上!我不知道。他非常勇敢到我不能想像的地步,這人到底有多少的想法要告訴這個世界?是不是它想告訴世人,你們都以為我是從地獄來的,其實你們才是活在自造的地獄!我所有的偏激都是天堂的福音!」興哥用手撥劃著自己的平頭,似乎上面還有頭髮似的。 「他一定是個寂寞而少言的人。」
多年以後我去台中鄉下辦事,特地去找他的老家,想看看他。一如所言,我關了九年後假釋。他在我們喝酒後一年被槍決了。 我開車跟在興哥堂弟的摩托車後面,在荒山的小路上慢慢拔高,許久,到了一個山村旁孤嶺,有著一個不大的墳群。 「小心,很難走。」他堂弟說。 我們攀過泥濘陡峭的丘陵,越過了墓地到了陵線上緣才找到他的墳,孤獨地躺在一片小空地上。 「他自己選的,在通的時候有一次回來跟我爸說,以後,如果有個萬一,他要葬在這裡。」他說完拿出塑膠袋裡的菜擺定,捻香而拜,唸了一段話後回頭問我,是否還記得回去的路,得到確定,他就翻下山去走了。 我為他點了一支煙,倒了杯酒,坐在墓旁邊。看著青斗石碑上刻著的他的名子,想著他說過的話。 「到了最後,你還是選擇遠離人群啊。」我對他說。 心中泛起一些情緒,不免沉沁在回憶中,坐了許久,一隻體型很大的灰鳥停在最近的樹梢上,用尖瑞而奇異的聲音鳴不停地叫著,回蕩在空悠的山谷中。 「人終究是無法真的溝通的,對吧?」 怪鳥倏然安靜,飛入山谷中。
台北 景美 2007/2/3 維沅
註一、「難回中原」:江湖話,比喻很難出獄回社會上混了。 註二、「通」:通輯。 註三、「賊頭」:指警察,江湖輕蔑警察是有牌流氓,故名。 註四、「貓鼠」:老鼠。 註五、南北二路:指江胡。 註六、關到生蝨母:比喻在監獄裡關了非常久。
[ 下 ]
|
|
| ( 創作|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