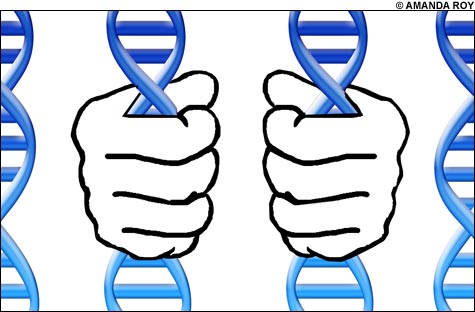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11/04 05:56:23瀏覽1178|回應1|推薦13 | |
一個朋友A寫信告訴我,她要將她那拍攝的剛過逝父親的二十多卷帶子,整理並再寫成一本書,然後給它取名叫《父親的生命之旅》。
我忽然想起年初有個朋友B告訴我,她去歐洲旅遊夜宿法國亞維儂時,竟然夢見了已經去逝十幾年的父親;B回台灣之後說她的歐洲之旅因此整個變了調:「我感覺我好像從來不曾了解我的家人,我還覺得我喜歡旅遊也許並不是自我放逐或流浪,而只是對家庭的失落所致。」
「我跟我父親一點也不親。」B打電話給我時,人已經到了阿爾,坐在梵谷的夜間咖啡廳。 「他很少帶妳一起去旅遊?」我把話跟著B的路線走。 「ㄟ,有可能,這我倒是從沒想到過;老爸的旅遊都是因為做生意到處跑,不方便帶我跟媽一起吧?」B說她儘量長話短說,那裡(咖啡廳)的人(主要是遊客)實在太多了。 「我想最主要是,老爸都沒教我什麼;」B說到這裡電話就斷線了。
時隔一個多小時,B又打電話來;在這中間,B最後那句話倒引我思想良多── 父親怎麼教小孩?有沒有,什麼是父母才能教而其他人都教不來的? 跟學校老師(&同學)的教與學,差別究竟在哪裡?什麼是父母教不來的? 我們究竟是怎被塑造出來(今天的模樣或德性)的? 我們又是怎麼搞清楚,自己現在是什麼模樣?
「我曾經看過我朋友,她在一家雜誌社工作,每次照片刊出來,她那喜歡畫畫的老爸一定打電話來,跟她討論這次她拍的如何,有沒有進步,什麼地方比誰的哪張拍的好,照片被編排的位置如何又如何;有次我在旁邊聽了聽眼淚就忍不住掉了下來。」B說,鼻音都出來了。 [B的這位攝影朋友,在此記為B’]
我大致能體會到她的「父女情深與『家庭知識論』(這名詞是我自創的)」的心情與深切感受。 以前在報社時有個坐在我右前方的男同事C,他老爸也是如此。 每次他們父子講電話,時間雖都不長,但是只要C有上班,他老爸一定會來電;他們父子兩人的對話每每教我聽到目瞪口呆──我從不知道父子關係可以如此,如此輕鬆自然就進入一個可以稱之為是內心世界的地帶。 話說回頭到那位《父親的生命之旅》的朋友A。 先,一個簡單的概念是,主題或標題或修正為,像「父親的生命“牽引”我的使命」之類的命題,我認為這樣的命題較接近「事實」──意思是,標題中再怎麼生命之旅,主體都有兩個人:父親與女兒。
理由跟科學家做實驗是一樣的,不同的科學家做同一種實驗,因為主體的不同而對客體(例如某種粒子的運動),產生不同的影響,而得出各異其趣的實驗「方向或新假設」。 同理,因為「這個時候的我」,所發現的「父親的生命」,跟之前的我以及別人所得出來的都是不一樣的。 簡單說,沒有「我」(A),父親不可能獲得呈現;沒有父親,「我」不可能在這個「空前的路」(這字眼很真實,真實到經常令自家人感受不到這種「幅度」或「壯舉」)獲得展現。
不簡單地說,或說更接近事實地說,因為「我」,已逝的父親「至今還活著」。 生命的展現有各種形式,肉身雖死,但因為女兒(「我」)的「使命之旅」,亡父在影像/文字的世界獲得另一種生命的開展,以至女兒(「我」)同時在影像/文字與現實(為了拍攝/書寫所採取的各種行動)雙重世界中,「復活」了父親與自己、以及過去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對話的可能與活力。
是的,復活,是在這種更接近事實變動與發展的主軸中,「我」經由創作之路而能更深入到,父親的生命變轉之旅以及自己的生命因此的變轉之旅。 因為生命的變轉,亡父在「另一種現實世界」中復活。 因為生命的變轉,女兒在「父親的另一種生命形態」中,體認到個人生命史已經陳腐入土的部份再度甦醒過來──很詭異的是,正是要借由這種「甦醒」,亡父才能更生動地在「另一種現實世界」中復活。
道理用說的不是太困難:就因為發現到自己死而復生的部份,並讓它再度(因為這個事件)運轉起來,亡父因此得以復活的栩栩如生。 復活,是雙重的,是互為主體性的。
當然,無可置疑的是,標題或書名等可以再根據這個方向,修得更動人或更感人或更意象化些──這可以讓更多讀者也獲得某種「復活」的機會與機率。 當然,這必也關係到發行商與出版商;市場的活絡來到了某種程度,一定會再影響這條復活之路的短與長。
經由A、B’、C這三個朋友的親子關係與『家庭知識論』之間的經驗(A的紀錄片,B’的照片,C新聞報導文章),所歸納而得的「個人知識」(P.K.)[註]的結論是:父女/父子可以情深以至於如何,雙方共同認可並因此持續談論的「媒介」,是不得不然的。 這個「共識媒介」,就是「家庭知識論」的DNA。
這種(文化)DNA,正是讓生理DNA繼續發展(&同時也是深情地「挖掘」)的關鍵秘碼。 經由這個關鍵秘碼,A、B’、C三人不僅維繫了生理上的DNA的綿延,而且還開創出了自己的文化DNA──從許多親子之間疏離乃至冰冷甚至反目的關係看來,「文化」DNA之功最基本(basic)與最美妙的,或不在出人頭地以至於何,而在於它從心理層面「自然」──這字眼在此出現令人心醉不已!──且徹底地「復活」了生理DNA。# [註]請參見
|
|
| ( 休閒生活|旅人手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