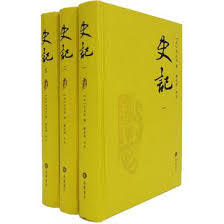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0/11/05 02:36:30瀏覽2210|回應2|推薦15 | |
|
說真的,從我自書中識得西安和北平這兩個地名起,我怎麼看就怎麼彆扭。是誰把原本世人皆知的長安和北京不用,卻另取個俗名頂替,到底是何居心? 後來才知是明太祖朱元璋自打下天下,定都南京後,於開國第二年就將大都(今之北京)改名為北平府,把長安也改名西安府。其後,朱元璋的四子明成祖朱棣趕走了他的姪子建文帝,也就是朱元璋的孫子,將都城從南京遷到北平,並將北平改為北京。滿清入關後,也在北京定都,於是,明、清兩代達500年之久,北京依舊是中國的政治中心。 到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後,代之而起的蔣介石也玩這無聊的政治遊戲。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中國的首都遷到南京。北京遂被改名為北平特別市。1930年6月,北平被降格為河北省省轄市,同年12月復升為院轄市。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被日軍佔領,其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此成立,又將北平改名為北京。 1945年,日本宣布向同盟國投降,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同年,國民政府再把北京改回北平。國共內戰後,蔣介石敗走台灣,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同時把北平正式更回為北京。這些手握政權的人弄得北京顛三倒四的,我看了都嫌累。說白了就是這些人滿腦子的帝王意識在作祟,他們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故意矮化這兩個歷史悠久的古都。 古今中外,無論是那個國家或大都市的名稱,都是由歷史文化點點滴滴所累積成的豐碑。名稱就是無形資產。在世界古都中,像雅典、羅馬、開羅,從未改名過,惟獨中國的帝王們卻樂此不疲。 把長安古都更名為西安。統治階層只圖“西部安寧”,於是“長治久安”的長安,便被降格成西安了。長安文化囊括周文化、秦文化、漢文化、唐文化。西安的價值在長安。長安的優勢在古都,古都的優勢在漢唐,漢唐的象徵就是長安。長安的歷史定位和歷史價值,西安無論如何是替代不了的。試想,當讀過世界歷史與地理的外國遊客們到中國想一睹長安和北京的風采,他們如何得知西安就是長安,北平就是北京呢? 最後搞明白了,還都覺得莫名其妙,為什麼中國人要這樣子做? 長安改叫西安後,西邊就真的“安寧”了嗎? “不”,答案是否定的。遠的從明朝末年來說,就有三位陜西人,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餓得起來造反。到了1644年,也是朱家王朝最後一年,農民軍起義領袖闖王李自成在西安稱大順皇帝,他以閃電般的速度和摧枯拉朽的攻勢進佔了北京城,逼得崇禎帝朱由檢上煤山自己給吊死在樹上,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就這麼給端了。 我們把視野拉近來說,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兵諫蔣抗日並迫其停止對內勦共,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事。陜西延安是中國共產黨在1935年至1948年的根據地,也被視為「革命聖地」。最後在短短四年的國共內戰,蔣介石連南京都保不住,只得退守台灣。北平這塊貌似新的招牌就硬被中國共產黨給拆了下來,換上了北京這塊老字號。 從書本得來的知識,我喜歡西安遠勝於北京。海峽兩岸分治時,我只能在心裡比較,到夢裏去神遊。所幸老天睜開了眼,蔣和毛倆人,一個蒙主寵召,另一個去馬克思那兒報到,人為的障礙給掃除了,小老百姓才得以跨過海峽走上一遭。 到過北京和西安這兩個古都後,更証實了我的看法不虛。北京除了保留幾個古蹟外,拆了的城牆全被建築物和幾環公路覆蓋,幾乎全給現代化了。 孔廟在東城區國子監街,當進入孔廟那塊地,我是走一步心情就往下沉一下。廟裏年久失修,滿目蕭然。大成殿為孔廟的正殿,裏面燈火不足。孔子像尚能看清楚,兩旁分立的七十二賢就只能見到一身黑,身上還積攢著一層不薄的灰塵。我處在這情境裏,感極而悲,有一種哭不出來的哀傷。幾年都過去了,每想到此事,心裏就難過一陣子。孔廟比之雍和宮和東嶽廟實在太寒傖了,難怪兩者的遊客無法相比,一個是三三兩兩,另兩個則是香火鼎盛。雖然孔廟被訂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遊客還得花錢買門票才能入內,北京市就這麼糟蹋孔廟! 當年大陸搞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批孔運動就是造孽! 年久失修的北京孔廟 離開孔廟,我步入國子監街,往地鐵方向走去。同側十餘公尺遠,有一人頭戴著帽子,身著舊軍衣蹲在那兒,面前放著一個已生銹的小鐵碗。剛拐入這街進孔廟前,我是走在街對面,老遠已瞅見這人,這會兒我就直朝著他走過去。當快要接近他時,原本低著頭的他,臉抬起來朝著我看,卻沒吱一點聲。剎那間,我的心像是被電擊似的,那是一張近乎有一半的臉被毀容,扭曲不正的五官使得他很難做出表情。細看他露出雙臂的皮膚,他應該還是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我忙掏出口袋所有的零票和硬幣,約有三十幾元人民幣,彎下背腰,把手中的錢輕輕的放入小鐵碗裏。我不忍心回頭再看那張令我心痛的臉,我更不敢往這個孩子的身上去想------。北京之行帶給我的心情是古井不波。 西安像大陸的許多古城一樣有鐘樓、鼓樓。西安的鐘鼓樓就在城內的中心處,鐘樓的所在地是一大圓環,大圓環的東西南北向分作四條大街,自鐘樓往四面遠眺,整個市區排列如棋局,小具盛唐時的規模。鐘鼓樓周遭是西安城最繁華熱鬧之處,到了西安,我落腳在鐘鼓樓附近的一家旅館。
玄奘像 西安的市容給人的感覺是乾淨清爽。這回我是懷著一顆朝聖的心來這兒,因為有兩位我心儀和神交已久的古人,漢朝司馬遷和唐朝玄奘,曾在這兒成就了自己。「秦時明月,漢時關。」,能足踏昔之長安,讓我的心靈感受到與司馬遷和玄奘先後同處一地,精神上生出無比的震撼和快感,我實在無法用文字表達萬一。 一週的西安之行,天天處在心情亢奮的狀態。西安大小飯館的菜餚都非常油膩,號稱什麼第一碗和第一餃的餐館,我都品嚐過,還是離不開一個“油” 字。打從第三天起, 我就竄進小巷換吃各類不同的麵條,既便宜又好吃。
西安市井 西安是11個朝代的都城。它的城牆位於西安市城區,是明朝初年在唐長安城皇城的基礎上建造的。後來又經過多次修補,是中國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古城牆。西安城牆為東西向長方形,東牆長2590米,西牆長2631米,南牆長3441米,北牆長3241米。城內面積約12平方公里,約為唐長安城的七分之一。 我在城牆上入口處租了一輛腳踏車,隨即在城牆上快意地繞行了一圈,心中的激情忘了被一路顛簸不舒服的屁股。歇息時,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曾在亮度不足的小書出租店裏,坐在小長板凳上,一邊聚精會神地看著錢夢龍繪的《西遊記》漫畫所帶來的樂趣,另一邊又得提防著隨時被一臉嚴肅的老爸逮到的不安。其實《西遊記》裏敘述的唐三藏與歷史課本裏的唐僧玄奘完全是兩碼事。 站立在城牆高處,遠望四周,我遙想起玄奘這位孜孜不倦的學問僧。他為了解決多年對佛學的疑惑,決心探本求源,大膽地冒險西行到印度取經。當時,唐朝剛建立沒幾年,為了防止突厥犯境,所以封閉了玉門關。玄奘只好偷渡出境,經過幾次險些喪命的艱險旅程才到達目的地。他在印度周遊了大小幾十國並在那爛陀寺潛心研習佛經並學得五種印度語言,最後取得了三藏法師的稱號。據史冊所載,只有精通五十部經、律、論的僧人才有資格稱「三藏」,當時全印度僅有九人頂得起這個稱號。
玄奘西行取經像
十四年後,玄奘學有所成,決心回國。當走到新疆和闐時,他上表給朝廷,表達了多年前私自出關的歉意,盼能得到朝廷的諒解。那時是貞觀十九年,大唐聲威已達西域。令玄奘意想不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不僅親自給他回了信,還安排從和闐到長安一路的官員沿途接送。玄奘返回首都長安那天,宰相房玄齡受唐太宗(在洛陽)之命率重要官員到城門外迎接,城裏的百姓們也幾乎傾城而出,排成長隊,夾道歡迎這位自西天取經歸來的大法師。數日後,觀看法物展示的民眾多如過江之鯽。 雖然玄奘拒絕了太宗的要求“還俗做官”,但他答應太宗主持編譯館。自此之後,太宗與其子高宗李治為玄奘的譯經工作,提供了一切所需的條件。玄奘自己譯出了從印度帶來的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經中的七十三部一千多卷,既精確又信、達、雅,現在我們誦唸的《觀世音般若經》就是他譯的。他創建了法相唯識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座高峰。
歸國第二年,玄奘奉太宗的詔命完成《大唐西域記》一書。當時,太宗懷有開拓疆域之志,亟需了解西域及其附近各地的風情,所以初見玄奘面時,便囑他將親睹耳聞,修成傳記。該書由玄奘口述,弟子辯機書撰而成,它記述玄奘遊歷西域和印度途中所經國家和城邑的見聞,不僅範圍廣泛,並且材料豐富,除了關於佛教聖跡和神話傳說的記載外,還包括許多各地政治、歷史、地理、物產、民族、習尚的資料。《大唐西域記》問世後,影響極大,致使一些同類著作相形見絀,今皆不傳,唯獨它流傳下來。這固然由其書內容豐富所決定,文采優美亦為其重要因素。《大唐西域記》堪稱中國歷史上的經典遊記。 二十年後,玄奘圓寂。安葬在長安城東的白鹿原那一天,方圓幾百里內,有十幾萬人自動自發地趕來哀悼。當晚,尚有萬餘人夜宿墓側,不忍離去。五年後,玄奘遷葬樊州。遷葬那天,又是多人送葬,情景有如當年初葬時之隆重。 《慈恩傳》是玄奘的兩位弟子慧立和彥宗將他的生平和西行編纂成書行世。慧立將日常聽取而又未見於《大唐西域記》的玄奘取經事蹟寫成前五卷,其後彥宗又把玄奘歸國後譯經的過程及逝世後的情形寫成後五卷,兩者合一而成一完整的玄奘傳記。小說《西遊記》的構思就是源自這三本書。 玄奘不過一凡胎,唐朝百姓們為何對玄奘自西歸來,一開始就散發出如此多的熱情? 為何有如此多的民眾去送葬? 作為帝王,李世民父子為何既高規格地禮遇玄奘又高調地敬重他呢? 經過一番思考,我的理解是 (1) 他一生奮鬥僅為了追求一個目標,喫而不捨的苦幹到底,必要時不惜拿性命做孤注一擲。(2) 他堅強的信念和克服諸種阻礙的毅力不是一般常人所具備的,最終他鞠躬盡瘁地實踐了自己的理想。(3) 人們都在追逐自己的理想,但是人們往往在追逐的過程中,難耐煎熬而放棄。人們拿玄奘和自己對比,都會由衷的欽仰他的為人,敬佩他的精神,更拜服他的造詣。作為一個捨身求法的高僧,玄奘身心力行的信仰之路自始至終為傳承者所敬仰。
高二上國文課,唸到《報任安書》這一課時, 我才稍為認識作者司馬遷。這篇文章既長又深奧,為了升學壓力, 我也就沒空去細嚼慢嚥這篇文情並茂的文章。經過了幾十年的紅塵打滾,斷斷續續地看完了【史記】後,我才不由自主地懷著一顆虔誠恭敬的心去接觸司馬遷,這位一生充滿悲劇的色彩、最被古今稱頌的史學家和散文學家。他撰寫的【史記】被認為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最初,他寫的是對父親的承諾,到後來他寫的卻是自己的血淚。 有關他的自述,流傳於世的只有三篇:《史記‧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悲士不遇賦》。經詳閱這三文, 再加上自己多年培養的史識,才得以進一步瞭解司馬遷一生的遭遇, 一歩一歩地走入他的內心深處,其中《報任安書》尤顯重要。 司馬遷十四歲時就從師熟讀許多經典,到了二十二歲,足跡幾乎踏遍整個中國山川大地,此後就隨父司馬談一直住在長安。從《報任安書》中得知,烙在司馬遷身上的悲劇與兩個叫少卿的人有關聯,一是李陵(字少卿),另一是任安(字少卿) 。前者僅是同朝為官並無私誼,後者倒是與他頗有交情的老朋友。「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是王昌齡寫《出塞》詩裏的後兩句,飛將就是漢朝名將李廣,李陵是他的孫子。 司馬遷二十八歲任郎中時,是年大漢出征匈奴。大將軍衛青遵武帝所囑,不使前將軍李廣直接與匈奴單宇交鋒,卻令他東行至某地限期相會,再合兵圍擊匈奴。因東道迂遠,更乏水草,李廣迷途失道而誤期,衛青問罪,李廣憤激而自戕。李廣三子李敢面質衛青其父死之因未果,雙方起衝突,李敢憤而動手傷及衛青,衛青自認理虧未敢張揚。霍去病(衛青之外甥)得悉此事,陰記胸中,伺機報復。 一天, 武帝至甘泉宮遊獵,去病從行,敢亦相隨。行獵中,去病於後用箭射死敢,帝袒護去病,只說是敢被鹿觸斃。君王專制時代,李氏家族對皇親國戚的惡行只能忍氣吞聲。司馬遷俱悉此事。 八年後,司馬談去世。臨終前,他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願望交付兒子,司馬遷流著淚說:「兒子雖然不才,願將先人所積存下來的重要史料,全部加以編撰,不敢缺略。」。逾二年,遷三十八歲繼父職為太史令,自此立志寫【史記】。 遷四十七歲,武帝遣貳師將軍,也是寵妾李夫人之兄李廣利率騎兵三萬人北征匈奴,帝令騎都尉李陵隨軍監督輜重,陵入朝自請率步兵五千人為偏師策應,帝許之。深入敵境後,陵遇匈奴八萬大兵,幾番苦戰,陵因寡不敵眾且後無援兵,終因矢盡糧絕,戰敗被俘而降匈奴。陵不殉節而死,實有損大漢天威,消息傳到長安,帝異常震怒,收李陵一家大小入獄,朝臣亦紛紛附和並斥責陵不忠。遷看不慣那些平日安享富貴、遇事諾諾的群臣,對在外拼命涉險的將領毫無同情心。李氏祖孫三代,一門忠烈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遷遂以一士諤諤仗義為陵辯白,認為陵以少敵多當屬英雄豪傑之行,其投降是假。帝認為遷污衊詆毀功少的李廣利才為陵開脫,同時也隱然地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帝更是大怒,將遷投入牢獄,以「誣罔」的罪名判處死刑。當時的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一種是「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另一種是處以腐刑(閹割)。這時,即使與遷平時有交情的或是有點正義感的朝臣都陌然以對,當然也包括了日後在獄中向他求救的任安。由於無足資可贖身免一死,遷本欲自殺,但想起允諾父親的遺願未了,遂決心屈辱地下蠶室,接受腐刑,隱忍苟活。當時整個司馬家族為了免遭牽連誅九族, 把司馬姓拆開,將司改為同姓,馬改為馮姓,這是專制時代老百姓不得不採取的自救措施吧! 第二年,傳陵為匈奴練兵,帝盛怒族滅李陵全家,後帝乃知為誤傳。陵獲悉老母和妻兒被屠戮悲傷不禁,遂斷絕了他“欲得其當而報於漢”的歸路。是年遷作《悲士不遇賦》,抒發了自己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心路歷程。 李陵於降匈奴後,曾替匈奴勸降蘇武,武的凛然正氣為陵所折服,武返漢後,也曾勸陵歸漢,《答蘇武書》當是二人往來信件之一。陵在信中敘述了自己客居胡地的悲凉,談到老母、妻兒為武帝殺戮的悲憤,更詳述了自己率五千步兵對抗匈奴八萬大軍的艱難,也訴說其投降變節是假,日後圖謀戰機以報漢帝是真的良苦用心。其心之切,其情之哀令人感嘆。但書尾,李陵對投降之事並未言悔,反倒勸蘇武“勿復勸陵”。陵之不言悔,决不僅止於老母、妻子被戮,更有祖父李廣與三叔李敢無辜枉死之恨。所以,李陵在降匈奴前,當時的心情是極端複雜的。李廣與李陵祖孫二人同為抗擊匈奴的猛將,一死一降。一個帶着千古遺憾,告别人世,另一個則客死胡地,悵惘一生。雖結果迥異,但命運何其相似!正如行伍出身的辛棄疾在《賀新郎》這首詞裏道出:「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 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就是慨歎李陵的境遇。 遷四十九歲出獄後,改任中書令,這是宦官做的工作。六年後,與太子劉據結怨的武帝寵臣江充誣告太子於宮中搞蠱術。帝命江充與按道侯韓說等入宮追查。太子得知後甚懼,聽從少傅石德之計,派人詐稱為武帝侍臣,將江充等人捕殺。江充助手蘇文逃至帝處控訴太子,帝居甘泉宫(在長安西北約150 公里之雲陽甘泉山)急派侍臣速召太子,然侍臣又恐為太子所誅,竟躲至他處避匿多日,乃回報武帝說「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武帝大怒,遂令丞相劉屈氂率兵平亂。太子被逼糾集眾人數萬,令任安(北軍使者護軍)發兵,安雖受節但按兵不動。太子舉兵與丞相軍激戰五日,死者數萬人。長安城民眾以為太子謀反,不予支持,太子勢孤力弱而兵敗逃亡,最後被迫自殺。 帝滅太子全家,並逼死太子生母衛子夫皇后。次年,帝心疑巫蠱之事,後查知此乃一冤案。帝方悟知太子劉據本無反心,下令族滅江充家。以「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處腰斬。」。因此受牽連而死者,前後達數萬人,史稱「巫蠱之禍」。 任安繫於獄中時,曾寫信勸司馬遷多「推賢進士」(其實是希望司馬遷搭救他),遷接到安來書後,心中甚是為難。他知武帝因誤殺太子,心中怨恨悲痛不已,意在為子報仇。若有人敢強諫,必定是捋虎鬚、觸逆鱗,自取其禍。因自己隱忍苟活的願望未竟,故他不願意重蹈「李陵之禍」。這倒不是厚李陵而薄任安,論交情,他與陵「無私交,素非相善」,而他與安則是老友。所以司馬遷的內心是非常痛苦。八年前,他為李少卿仗義執言,落得「身殘處穢」的下場;現在一位故交老友任少卿來信向他求援,他卻動彈不得。他遂寫了一悲憤抑鬱、蕩氣迴腸、感人至深、流傳千古的長信《報任安書》,真誠坦率地剖白,充滿感情地敘述自己不幸的遭遇,把任安有死無救的事實和自己見死不救的苦衷和盤托出,使安知曉結果並諒解自己切身的痛苦。 其實任安按兵不動的決定是正確的,如此一來可讓他的士兵不參與王室之戰,避免無謂的犧牲。當時,帝遠在甘泉宫(距長安約150 公里),太子則身居長安。安任京城禁衛軍指揮官,在這個節骨眼上,他根本不知該聽誰的命令。他又怎麼敢公然與武帝派來的丞相軍交戰呢! 事後証明,武帝已老令智昏,在氣頭上誰都殺,以任安「老吏坐觀成敗」僅是忿怒下為了要殺他找的藉口罷了。任安非死不可,誰也救不了他。誰要出來為他說話,那可要頂著誅九族的禍。「李陵事件」根本無法與「巫蠱之禍」相比。 遷以刑後餘生的全部精力,貢獻於他的著作。他在《報任安書》的末尾提到,文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史記】已完成了。此後,遷的事蹟就不明,卒年也不詳。 【史記】是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私書,也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所記上起傳說中之黃帝,下至漢武帝,總結了中國三千年歷史的發展。司馬遷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他寫了兩份,以防不測。遷有一女,嫁給安平敬侯楊敞,生楊忠和楊惲,楊忠是「關西孔子」楊震的曾祖父。到了漢宣帝時,遷的外孫楊惲將它傳佈,【史記】才得以流行於世。我想【史記】應當是遷密托給女兒,再經她的兒子才得以公諸於世。
太史公 司馬遷在家中撰寫【史記】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一片竹片叫做簡,把字寫在竹片上,把許多竹簡編連到一處,就叫做冊。一部書往往需要用很多的竹簡寫成,因為一片竹簡寫不了多少字。我不敢想像司馬遷是怎麼把兩份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史記】,一字一字地用毛筆墨書在竹片上,再一片一片地串聯成冊。這需要耗費他多少精力和財力! 以他區區下大夫不豐的俸祿,其艱難和浩繁可想而知。司馬遷白天有公務,夜晚還得在昏暗的孤燈下振筆直書,他的老妻肯定幫他做了不少的事。寫完了【史記】,人也該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了。每思及此,我總是不禁鼻酸。在當時,他只是個小人物,沒人會傳他的名。後人能認識他,都是來自他自己的傳世文章。日後,班固寫的【漢書】,其內的司馬遷傳也都是引用他的三篇傳世之文。 我一生最推崇【史記】,因為司馬遷能突顯人物在歷史進程裡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他之前的史家對於歷史事物的解釋,都是停留在受著自然力量、神權、天命等的支配。到了【史記】,司馬遷強調了人物在歷史上的巨大意義。他敘述人物,並不限於王侯將相,而遍及於社會各階層。在【史記】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活躍在歷史舞台上的各式各樣的人物,遷都藉同情的筆端,使他們放射出耀眼的光輝。他給帝王、將、相立傳,更給酷吏、刺客、遊俠等列傳。今天大家經常掛在嘴上的“多元社會”,司馬遷早在【史記】裏就舖墊好了平台,只可惜後人的悟性太低。 兩千多年來人們在稱美讚歎之餘,又有誰會認真地思考「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呢! 難怪世人樂而不疲地在不同的時空下,重複地扮演著「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野台戲。這倒使我懷疑 "人類是走不出迷宮的白老鼠"。 司馬遷在《伯夷列傳》裏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這是個“天問”的命題,儘管司馬遷熟讀【周易】、老子及莊子的著作,他還是心有疑怨而無解。就是兩千多年後的今日,它還是老天留給人們的疑問。如果佛教早些傳來中土,不知司馬遷能否接受「三世輪迴」而釋懷? 離開西安的前一天恰好是個星期日,早上走訪過碑林後,吃過午飯就大睡了一覺,醒來已是五點多鐘。趁著天色未黑,就順便到最熱鬧的鐘鼓樓廣場看看。出了旅館,我朝著遠處聚著一堆人群走去。那兒有三位未成年女孩正在表演雜耍,圍觀的群眾大約有六七十人,以年輕人居多。大女孩大概十五六歲,中的約十歲,小的一看就知道還沒上小學。三人衣著有些髒,想必是在地上翻滾所致。她們雖面無表情,卻是一臉淳樸的素面, 三人不發一言地賣力演出。最小的還得屈著身子鑽進比她的身子還小的竹簍裏再鑽出來,有幾個動作真有點不忍心觀看。表演畢,觀眾們個個拔腳就走,只有三四人趨前把小錢投入小竹筒裏。我把捏在手上的二十元票子趕忙地邊走邊換了一張五十元券輕輕地塞進小筒。 隨後,我蹓了一會兒,就近找了一家麵館打發肚子。飯畢,一路走來,兩邊賣熟食的店裏招滿了有說有笑的年輕人,正開懷地吃著喝著。走了約莫十來分鐘,我又見到先前賣藝的三位女孩,她們已移到另一處,在微弱的路燈下圍地表演。此刻正是吃晚飯的時候,天也大半黑了,僅有不到十個觀眾駐足在那兒圍觀。這幾個孩子肯定還餓著肚子吧! 這次她們能掙到多少賞錢呢?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往旅館的方向走去。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