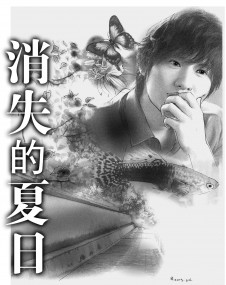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06/30 12:44:03瀏覽1524|回應3|推薦99 | |
我始終記得那些年的夏天,特別是在孔子廟後方的林徑裡獵捕蟲魚的往事。 如果時間的最初是一面蛛網,那麼,我們的未來早已被算計好了,蟄居在八卦矩陣的某一條絲路或某一處截角裡頭,同比例被縮放變換;如果有「過去」的話,我們未來的日日夜夜早已成為過去,過去式與未來式匯流成一片,如同阿瑪迪斯的音樂擴展的方式…。 美麗的蝴蝶總能帶我掙出無聊的日子,思緒一下子飛升到天空遨遊一番。其實並不是每一種蝴蝶都能像鳳蝶或樺斑蝶那般賞心悅目(好像是撲著香粉的小女孩),比如橄欖樹林底下停歇的枯葉蝶(旁邊也散立著幾塊明末、清代的古墓碑),神似枯手合十施法的黑女巫,羽翅上睜著一對會吸走靈魂的幻眼,就不得不令人敬而遠之了。 我來到小徑,可以暫時擺脫爸媽冷戰的低氣壓和煩人的功課。 穿過兩行日式陳舊的陸軍醫院營舍之後,坡路上蜿蜒的小徑可以深入植物園,正是羊腸小徑的寫照。裡邊果真有一戶畜牧山羊的人家,牧羊人一清早就驅趕羊群出獸閘,沿途飽食嫩草,日落時分才繞返家園,許多小路便是由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土狗踩踏了千萬遍不意形成的。我明白要從哪一處茂密的長草撥開爬進去(那兒正是文明世界與荒野的分界),便可以尋見祕道,再平行越過了一處老墓園和監獄農場,抵達那一片遼闊、無人煙的青翠草原。每逢夏季,我都要鑽進穿出玩好幾趟,去探訪我的森林好朋友們:幾株老芒果樹和一條山溪。溪水從後方的山巒汨汨湧出(自然也滲流過了老樹們牢密的根鬚),然後匯集,繞經孔子廟、繼續往下流進中山公園內。我摸熟了小溪每一處的迴轉和水深,像小帆船航行一樣,循著溪道從上游往下巡禮,沿途翻掀石頭覓尋青蛙、長臂溪蝦和毛蟹的蹤跡。還有一種身長僅兩、三公分,俗稱「九魽仔」(「大吻蝦虎」)的洄游性魚類,當時我都把名字的台語發音聽成是「狗柑仔」(或狗公仔),因為幼魚的身體有淡橘色斑紋像「柑橘皮」的色澤,胸腹下長有吸盤會一跳一跳地前進,又套上了一顆醜呆的鬥牛犬般的頭顱所使然。「狗柑仔」的一生歷經了海洋生涯,也跑來溪流交配產卵,連牠也困惑自己到底是該屬於淡水魚還是鹹水魚了。 我也常去捉「神仙魚」,那時候我們管它叫做「孔雀魚」。有些孔雀魚的尾鰭特長如柔逸的輕紗,美得不像現實世界,點綴著橘紅、靛藍或是螢黃色的彩斑,孔雀開屏般炫目。孔雀魚群聚的地方很奇特,竟是公園外頭啟明路旁一條筆直的大排水溝裡(當我第一次聽到「啟明」的路名時,便由字詞聯想:從那邊山頂透出全市第一道晨曦時將是什麼樣的光景?)大水溝上方陡斜的坡地是「啟明新村」,眷村裡的廢水、糞水全排進大水溝。大肚魚和孔雀魚佔據了此地生態的大宗,數量驚人。銀灰色的大肚魚除了腹部鼓脹、沒有彩紋之外,跟孔雀魚長得極相似,一度我都以為大腹便便的大肚魚是雌性的孔雀魚呢,隨時保持著待產的狀態,何況彼此幼魚的樣貌根本難分軒輊。 由於孔雀魚很漂亮,而且水族館裡頭還沒有販售,更誘使我跳進排水溝去捕捉,幸好公園的溪水也注入這裡,水質混合起來算是清澈的。不過,魚隻的反應很敏捷,數量雖多卻不容易撈捕得到,頂多逮到幾條掉隊的大肚魚。路過的孩童偶爾也會跳進來打撈,總跟不上魚群竄溜的奇快速度。漸漸地,我觀察到魚群會慣性地挨著溝壁泅走,便預先在下游拿石塊鎮住塑膠袋口,再從上游驅趕,魚兒果真一一鑽入袋子裡,每次迅速拎起袋子便輕易逮到十幾條,最後揀下色澤最豔麗的孔雀魚,其餘的則放生。每當有別的孩童好奇窺看時,我便改以徒手捕捉,不希望我的撇步被他們偷學走。 而蝶翼和孔雀魚的尾鰭是多麼美妙的吻合啊!(像是嘉年華會亮麗的面具、佩飾)有段時間我堅信牠們是同一種生物,只是分屬於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空中或水中的差別而已。 捕來的魚蝦、毛蟹、青蛙和蝌蚪全養在家裡三樓頂的蓄水塔(蝌蚪之中有些後來卻變成了癩皮的蟾蜍)。蓄水塔因抽水馬達故障而荒廢了很久,正好供我養魚之用,不過,必須從二樓提水上去補充,那段日子我便很巴望下雨天的到來,好省掉辛苦提水的功夫。(為了防止青蛙逃出來,水位不能高。有一回在酷暑裡忘記添水,不久,水泥池底便剩下曝乾的苔藻裂片和褪白的魚屍、蝦米了。) 拿「罕見」的孔雀魚可以跟同學交換到昂貴的黑劍魚,一對劍魚在水族館裡標售可是要價三、四十塊錢呢。 看來,荒廢的蓄水塔正是我賺得零用金的寶庫。等於說,我在樓頂陽台為自己蓋了一座私人的植物園,星期天除外,隨時都可以鑽進去玩耍。 擒回家的蝴蝶、蜻蜓、牛屎龜(獨角仙)和虎頭蜂則製成標本,拿大頭針釘在空的高麗人蔘木盒裡,當針尖欲刺穿牠們軀殼的瞬間,總湧上一股華麗的生命將被死亡之釜劈裂的戰慄滋味。那時,我幻想著自己是一名在非洲大草原上狩獵珍禽猛獸的英雄獵人。不時還會跑去中央噴水池附近觀覽標本展,主題有時候是昆蟲,有時則是螃蟹或貝殼,興起我計畫在植物園活捉從史前倖存下來的小型恐龍而成為名人;而潛入更荒僻的窟洞內狩獵的成果,只尋到一些貝類碎殼,卻沾惹了一身的蛛絲和毛蟲,弄得皮膚刺痛紅腫回家挨了父親的罵。(這恐怕是從斯文豪氏攀木蜥蜴和蛇鰻怪誕的模樣所衍生的聯想吧。) 熱衷獵集奇物異種的「標本」很像是渴望獲取「勳章」:贏得人生戰利品或獎狀的儀式行為。生物間有一種以武力擴張地域和疆界的本能,古代的帝王看著領土日漸拓展應會產生莫名的滿足感吧,而全部的山川、平原的版塊總合,正是由被分封的將領、功臣們所披掛的無數勳章綵帶拼綴成就的。 在日據時代便闢成的植物園裡,密佈著高聳的原始林木,枝幹上纏吊著粗肥的攀藤,使得迂繞的小徑顯得黝暗潮濕。裡頭,阿瑪迪斯撫慰人心的〈安魂曲〉正迴響著──由我心海所播送出來。我聽說古早的時候……:日軍來台接收時,圍剿反抗軍的最後一處據點,便是鄒族戰士所浴血困守的這一片黑森林。林蔭間遊蕩的涼風所引起的孤寂感,總讓人倒抽一口冷氣。(一旁八景之一的「林場風清」碑石,也會點頭同意我這項說法吧!) 獵補蟲魚之前,我例行會收集乾枝椏來烤地瓜(但我始終沒有耐性堆疊土窯,而是直接在土坑內點燃炭火),最後再將燒燙的焦皮揭掉,淺嚐表層香甜的藷肉即可,未熟透的地瓜心就拋進溪裡餵魚。所以得先到東市場挑選迷你的地瓜才行。等木炭燒紅了、白煙瀰漫之際,就覆土掩蓋,枯候地瓜燜熟的難熬時刻,便去灌肚猴(蟋蟀)或溜進冰凉的溪裡玩耍。在暑天,把脚丫子泡在水中真有說不出來的暢快。此外,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在溪邊撿獲巴西橡膠樹的果實,油亮的外殼小巧玲瓏卻很堅硬,繪著奇異的棕褐色斑紋,搖動起來,核仁便喀拉喀拉地滾動,我們都管它叫做「燒籽」,因為在水泥地上快速摩擦之後會變得很「燒燙」所致(我總覺得像是在摩娑一盞可以許願的阿拉丁神燈)。我拿燒籽可以跟友伴交換到好東西,通常是一把玻璃彈珠或是尪仔標之類。 兒童新得到一件玩具,就像成人新閱讀了一本小說,腦海隨著虛構的情節深入歷險,搬演命運之鏡裡與己身相彷的悲喜形影,直到玩具殘舊到隱失在不知哪一回的搬家途中為止。 每個星期天的早晨我總是循著這樣的程序消磨掉美好時光。近午時分,便鑽出森林來到山麓的公園兒童遊樂場,掏給賣烤魷魚的老闆娘三枚銅板,從她的黑棉布袋裡摸出一只麻將大小的木牌子(那副棉布袋彷彿是魔術師的道具襪子),再對照數字,從木板劃定的方格位置上換取一截魷魚干,蹲在烘爐旁,用竹筷挾入花瓜罐子裡浸攪醬汁,鋪在網架上燒烤起來,待炭火熾熱爆響、濃香四溢時,便入口嚼盡。 看來,我除了喜歡抓魚,也偏愛嘗這一款海底的魷「魚」滋味。 接近難捨的尾聲時(父親規定了出遊的上限時間),走到鄰旁的市立圖書館兒童閱覽室安靜讀些故事書、繪本。正午,便和姊姊妹妹各買一袋含碎冰的沙士汽水(摻放著一匙起泡用的小蘇打),頂著南國艷陽,邊啜吸、邊步行二十來分鐘的路程返家吃飯。 而那些昆蟲標本在若干時日之後,當我重新拉開盒蓋察看時,隨即嗅見一股嗆鼻的異臭衝上腦門(不由憶起:行經陸軍醫院旁,從病房內傷兵的肢體上所飄溢出來的消毒藥水味);原來,蟻群早已領先我一步悄悄來掃蕩過了,徒留下被時光吮淨的空洞軀殼和支解的脆裂翅翼。便趕緊將粉屑清光全倒進垃圾桶裡…。 「 山仔頂」,嘉義市東區近郊那一處高隆起的丘陵地──我昔日漫遊的獵場入口,如今已被拓平為寬闊的運動遊樂區,這一片感傷的「荒野」領地,現在已不再專屬於我一人獨有了,但是在我的心底則已昇華成了朝聖者的永恆秘境;留在腦海裡不時反覆紀念著:彼時在蔚藍的天空下、斑斕蔓生的馬櫻丹花香叢中,高舉捕蝶網,正揮汗奔逐翩翩的巍顫飛影…,揚起塵土、然後消失在小徑盡頭的印記。
2013/07/08 19:08
Dear 也思~ 消失的夏日(musikaho):
特前來恭喜您所發表「消失的夏日」一文,已經登上聯合新聞網首頁,生活消費|貼心下午茶,歡迎有空前往觀看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