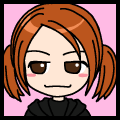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0/08/04 21:42:39瀏覽1587|回應0|推薦19 | |

閱讀文學作品時,史實的功過已非讀者需要針砭的重心,對我來說,書寫人物時,要緊的是穿透所要書寫的人物內心,以他們的視野呈現對某些事件的心聲與感知。歷史僅僅是一條鋼索,不是梁柱。即使模擬,有人性有感情才是重要。 本書穿插的敘述者,從宋慶齡晚年的生活秘書(也幾乎是知己)S的女兒珍珍開始,與宋慶齡、孫中山的思維迂迴穿梭,文字步調並不急促,卻很明白地將男人女人,舊時代新環境那樣截然不同的生命追求一塊一塊比對出來。 「當年他愛這個人嗎?那是多麼久以前的事了。但不管怎麼說,他必須承認,她再不可能碰到一個人像孫文,有這麼多改變世界的夢想。」(頁156) 關於女人。或許女人,愛的正是男人的企圖心,年齡或其他因素在情感酵素之外顯得微不足道,她未曾看清楚,也不願意看清楚的,只是「丈夫那隻覆著老人斑的手」。於是在丈夫辭世後的日子裡,她在精神上執著於與丈夫持有同樣精神的鄧演達─「她再度旅歐,愛上了馬鈴薯做的薄餅、喜歡聽基調異常悲哀的德國民歌,還有,她在遙遙地追隨她心裡充滿英雄意志的男人」(頁175)。 相較於與孫中山的婚姻,因為貼近而使兩人回到人間的老夫少妻生活,對鄧演達的執著來自於無法得到與最終失去的美好形象。「也是婚後才知道的,丈夫是很好的老師沒錯:但除了做革命導師的熱忱,丈夫卻有點粗疏、有點急躁、有點心不在焉」。對於鄧演達,身為一個迎著新時代風口,經歷多少驚濤駭浪的女人,卻只覺得「有可能超越死亡的只有愛情」。對丈夫的仰慕到對鄧氏的心靈追隨, 追求的只是一種精神層面的高度。那麼S呢?對他的依賴,是否只是因為他做到了前半生所有男人無法做到的部分─忠實地傾聽、陪伴? 關於男人,我想不是因為女性書寫而將男性單純化,而是男人的生活重心始終不在感情,故對孫中山先生來說,再豐沛的感情畢竟沒有多餘的武力困住雄心。「一生中,其實他無數次疏忽了身邊的女人……有時候,先生也為自己的粗心大意十分自責,旋即卻又原諒了自己,總以為往後多的是時間,還可以慢慢彌補」。(頁130)這裡以珍珍的角度敘述,倒是十分客觀。甚至閒居上海的時日,孫氏還是迎著不絕的訪客,燃燒著對時局的憂火,與像是局外人似的妻子也就這麼相敬如賓地過著,那樣如暮的身軀,失去青年時的火花,只餘伴著妻子入眠的溫存。 關於旁觀者,珍珍,藉由她遠嫁海外的距離感,透出於一種相當疏離的回憶模式,不知是否想藉由這個視角讓讀者認為,通篇並非全為感情壓制理性,中立的事實面貌才由此揭出?不過閱讀時,雖有一股同情的氛圍在文字裡流竄,珍珍總還是在外圍徘徊。要追求中心人物的真諦,除了孫、宋二人之外,恐怕只能問親近的革命同志、鄧演達、甚至S。 《行道天涯》其實是一本不用太瞭解史實也能讀懂的故事,但假若瞭解史實的讀者,對於革命之外的情感體驗必然更深入一層;平路書寫的意義,本來就意圖一種大人物的縮寫與大環境的細緻感情,不是要寫傳記,更非杜撰羅曼史,就是單純的寫「革命與愛情故事」,不需將其嚴肅化。就該還給血肉之軀的愛慾嗔癡、喜怒孤寂這個高度,平路達到了,辛苦但平穩地達到了。 |
|
| (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