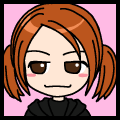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0/03/07 15:47:27瀏覽1070|回應0|推薦7 | |
此次深入閱讀梁寒衣小姐的作品集後,一直在思考要如何透過「非專業評論」的文字去啟蒙甚至開發讀者。開始撰寫關於書籍的讀後感以來,深深覺得推薦一本好書並不難,難的是要用何種形式去推薦它,這取決於閱讀群眾的範圍、水平及類型;有時候,評論者並不期待社會價值所設定的讀者群會因書籍評論而產生短暫的交集,如郭強生在《在文學徬徨的年代》所言,他只是藉由他所瞭解的文學理論解決一些創作者關心的主題而已。 因此,至於這些作品的價值是否能因此錦上添花, 就要交給文學年代與文學環境去驗證,而非受出版市場波動或讀者潮流所左右。畢竟,「通俗」與「文學」小說的界線,普羅大眾與文學評論者的判別基礎早已出現根深蒂固的分水嶺,當一個所謂「通俗」的讀者先入為主地排拒「純文學」作品的晦澀,或「純文學」讀者對於「通俗」小說的不屑一顧,都只是人為主觀的認知,並不能撼動作品本身對文學史的影響力。 所以我並不想多用一般讀者難以接近的文學理論,並且我也無此能力對梁寒衣的作品多做抽象的剖析,就小說整體性而言,去拆解她的作品跟抽刀斷水是同等無謂的行為。只是大部分時候,創作必須要兼顧內在與外在,內在是讀者對作品的理解高度,外在則是作者透過創作傳達出來的作品面貌。而寫作的目的,即是要由內而外,透過創作的過程透露對這個時代的期待與困惑,尋求讀者的共鳴。 但梁寒衣創作的目的,只是單純為了「表達」,而這樣的「表達」,儼然傾盡她所有生命裡的精神力量與高度創作養分,這已脫離了是否需要評論與推薦的爭議,我建議讀者的閱讀焦點反而應該放在作品中傳達的意義與現實精神的聯結性,會比思考分類這是什麼類型的作品來得更具意義。 不過我認為她並非毫無期待與困惑,只是她不以此侷限自己,因為這個世界的一切虛實,她都在生活的修行過程裡取得定見,關於生與死,繁華與頹落,神與人甚至靈魂,神話與諸佛,她的創作不是許多疑問,而是一個早已底定的答案。 【讀者入門】從〈殺死和尚〉到〈蓮澤〉 先讀【現代】小說集後再讀【寓言】小說集,有種苦盡甘來的感覺,這純粹以一位普通讀者對作品的第一印象而言,無關作品的深度。應該說,「寓言」本 身就是隱喻的外衣,利用故事,以幽默或反諷的方式包覆思維哲理,你可以只看故事本身,也可以脫掉外衣去看故事內裡的素顏,這是寓言有趣也容易接近的理由。相較之下,在「專業讀者」的眼裡,【現代】小說集裡的創作整體上便顯得比較比較冷冽(對於現實的殘酷,只是反映。而不是隱喻)。 「有生必有死,這是一體兩面,如何了解生也了解死,而把握這裡頭無限的生,生命可以做很多事,這就是無限的生」─梁寒衣曾經這樣表達她對生死的看法。雖然能夠如此透徹的表達生命的意義,但創作最重要的是讓思維與創作走在同一條軌道上。 於是梁寒衣用不同的創作形式,達成相同的創作初衷,如〈殺死和尚〉與〈蓮澤〉,在一冷一熱、一動一靜之間燃起的動念與反思,實際上都共同指向對生命初始的看法,作品集內的創作大多亦同,即寫死的慾念,但意在言外的是生命的價值,特別是梁寒衣隱居靜思沉澱的生活方式,是影響創作最大也最珍貴的中心元素。 當然如〈生命列車〉、〈蛆‧幽靈與月光〉對生死交接的感官描繪或許比較能深刻的震撼讀者,而〈赫!我是一條龍〉的黑色幽默亦展現了難得的小說親和力,最貼近我心中所認知的作者風格原典,仍非上述,更非希臘神話或佛經小說,而是比較具有心靈掙扎性的文字。 這也是在此特別提出〈殺死和尚〉與〈蓮澤〉的原因,這兩篇主題都與精神的頓悟相關,但創作形式也恰好貼近「入世」的精神,同時排除了大部分創作因用字較一般作品艱僻或引經據典造成的讀者閱讀障礙。創作本是入世的行為,梁寒衣既選擇走入人群宣揚佛義,當然也能用比較入世的方式創作小說,但不代表因此喪失創作的本質。 所以我不認為一般讀者不能以此作為她作品閱讀的入門,雖然她的創作也有較為直接指涉現實與心理的,如〈白蔦蘿與紅蔦蘿〉、〈迂迴鐵道上的公主〉等。作品內涵的多層次,讀者選擇自己能理解的部分也未嘗不可。這也顯示了一個現象:某些優秀作品的「曲高和寡」不見得是作者的關係,也有可能是一般讀者並不具備完整鑑賞作品層次的能力,以及缺乏專業作品導讀者的緣故,這個問題在梁寒衣的創作裡尤其特別需要被重視。 梁寒衣與她的作品,都是不滅的傳奇,在終日巨浪翻湧的浩瀚書海中,普羅大眾不知其名是常態,有緣接觸(如我),則是無比幸運;當然,如果因小說集的出版而讓文學界再添一筆雋永的刻痕。是我與未來眾多讀者都樂見的。
|
|
| (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