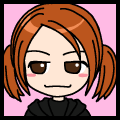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0/01/03 11:54:37瀏覽1880|回應0|推薦9 | |
傳說,是人類最初靈性的原型,故事,則將傳說賦予完整人性;而在蔣勳《新編傳說》裡,傳說的神秘性、故事的生動性,都在文學的最終價值裡展現出來。 蔣勳先生將十年前出版的《傳說》再新增四篇〈莎樂美、約翰與耶穌〉、〈嵇康與廣陵散〉、〈借花獻佛〉、〈宿命之子─約拿單〉後,重新改版的《新編傳說》讓傳說與故事揉合成雅俗共讀的動人作品。以〈莎樂美、約翰與耶穌〉及〈嵇康與廣陵散〉來說,在繁浩的美麗與絕望的谷底,我們卻能同時從中直視苦難的真相。 這便是文學作品傳達出的故事張力罷。 【 嵇康的手指穿梭過牢獄的鐵柵和恣肆的春天的桃花之間。冷冷的鐵,和嫵媚如血的桃花,在燦爛與殘酷之間,在生與死之間 】 在史書裡,嵇康本來便是頗具傳奇性美感的人物代表,在〈嵇康與廣陵散〉裡描繪的意象,著重於用生死映照對人生理念的堅持與釋然。竹林七賢之一的名聲、為了被誣告的友人呂安作證因而身陷囹圄的真性情,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生死的疆界邊緣游走時,人生的起點與終點都被下結論的剎那,那樣悲愴的淒涼,卻是讓讀者最震撼的,連三千太學生亦無法挽回的,澎湃壯烈的琴曲,如此悲劇之美,竟猝然結束於與老獄卒最後的對話裡。 至於〈莎樂美、約翰與耶穌〉,那已是超越善惡交相煎的人性層次,拔脫到神性與人性的跌宕浮沉。近代的寫實主義,目的是要警惕我們切莫逃避人生的種種困境;傳說的神喻意義,卻是處處提醒我們記取人類在太初誕生時最純淨無暇的性格,瞭解一切要承受的悲劇重量是人類智慧發展不可擺脫的考驗。 「我是為美麗而來的,歷史需要美麗來毀滅聖徒。」書中描繪莎樂美這樣的自語,表達出美麗孕育出的慾望也能夠轉化成毀滅的深淵。此處約翰的刻苦自省、耶穌的孤獨傳道,與嵇康的狂放路途並不相同,卻都肇因於他們堅持的信仰精神,最終面臨生死時也就同時綻放了相等高度的人性價值。 也由於神話傳說故事所有飽含的、被讀者深深吸吮的文學營養,仍舊切不斷愛與生死的紐帶。因此,無論再怎麼去蕪存菁,留存下來的、被反覆傳頌的,枝繁葉茂攀藤結果的,仍然是對生命本質的智識或恐懼。所有闡釋神話傳說與歷史故事的人漸漸了解,情境美則美矣,重點在於如何表現原本隱晦未明的真諦。 蔣勳先生說,相較於十年前的《傳說》眷戀美(確實具有美的一致性),新增的四篇較為趨近於中年蒼老的心境;在這樣的前提下,蔣勳《新編傳說》裡改寫的中外傳說故事,我仍舊在字裡行間看見另一個面向的美的價值。 蒼涼使人浸淫在悲哀的氛圍裡,蒼老卻仍保有灶上爐火惇惇的餘溫。如果我們對遠藤周作在《深河》裡的日本神父身上揭示的永生意義感同身受,就能清楚瞭解,捨身飼虎與割肉貿鴿的傳說,或許並非刻意地地成為教化信徒的某種神性圭臬,只是我們未必能贊同與理解那樣提升性靈層次的肉體拋棄方式,卻能將〈廣陵散〉隨著稽康的含冤而亡而隨之湮沒的嘆息通過閱讀的眼睛直達心底最深處的,某個最脆弱最柔軟的地方。 如何表現這些傳說典型,文學表達傳說的方式與角度不同,讀者接收訊息的波長也就隨之震盪。雖然十分激賞也驚艷〈屈原的最後一天〉的死亡情懷,竟悠然如平民百姓的寧靜午后,我仍然流連在嵇康仰著頭,叛逆的手指就著鐵窗欄杆對廣陵散最後一次巡禮的面容。 《新編傳說》從此添加了嶄新的文學養分,茁壯了每個璞玉般的神話傳說。 |
|
| ( 創作|文學賞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