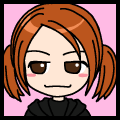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5/05/07 21:04:42瀏覽928|回應3|推薦13 | |
| 山雷從遠方轟打過來,挾帶悶熱而潮濕的水氣。 夏季的小城午後暑氣蒸騰,這裡接近南方,但沒有無止境的炎熾,只有午後短暫的燠熱難耐,所有居民都未能抗拒地形神俱疲,靈魂、思想都以如如不動的姿態凝結在空氣裡。街上似入無人之境,寂靜無聲,屋後蟬鳴也顯得軟疲。人們躲在家裡將電風扇轉速開到最大,大同電扇嗡嗡轉動,仍舊擋不住熱氣襲擊。老人家咒罵著幾乎令人窒息的溫度,豆大的汗珠就這樣滿頭滿臉、身上背上,又濕又黏。 山雨欲來。 西北雨每日來得又急又準,根據阿嬤們的說法是比火車時刻更準。小女孩跟著阿嬤在驟雨到達之前將晾著的衣服收好,包括弟弟的尿布。才八個月大的弟弟每天由她背著跑進跑出。她每天到河邊洗尿布,每每抬頭望去,小溪邊一群男孩打鬧戲水玩得渾然忘我,她僅能機械式地重複搓動泛黃的尿布,羨慕與忌妒在幼小心靈中縱橫交織。夏季的亮麗光燦下女孩的身影如豆,莫名湧上來的失落讓她無法承受,像是電視上孤女的境遇似的情節鑽進懵懂的腦海裡,她開始自怨自憐。 雨來了,伴隨著轟隆隆的雷聲。 周圍瀰漫的涼意讓老人家打起盹,阿嬤甚至誇張的穿起黃棉襖背心,躺在紅眠床上睏倦地翻動。老人家一動,整張床吱吱價響。女孩害怕這樣詭異的聲音,聽起來撕心裂肺,像阿嬤多病的身軀再也禁不住任何打擊。她逃離房間,跑進客廳,打開已褪去暗紅光澤的電視木箱外蓋,王芷蕾悠悠唱著台北的天空。台北,有爸媽建立的美麗香格里拉。 雨停了。她抓著綠豆冰滿足地舔著,阿嬤特地為她煮了清甜的綠豆湯,倒進有米老鼠圖案小小短短的衛生冰袋之後放進冰庫,在孩子們心目中,米老鼠牌綠豆冰是高級享受,絕非每家都有。她故意背著弟弟坐在門檻上吃冰,這時便換她接受鄰家小孩羨幕或忌妒的眼光投射。只有在這時候,她才像個公主,一個被國王皇后遺棄在窮鄉僻壤的落難公主。雖然她知道,那只是不真實的虛榮感,一戳就破。 牆上吊鐘敲了三響,窗邊蛙聲一片,廳堂內外是兩個不同的時空,女孩抓起老人的咳嗽藥,倒了沁涼的開水,沉沉的咳嗽把這個季節停滯在老人的追憶裡。把分針秒針轉了再轉,一回身,那是一個長鏡頭,溫溫吞吞的拉過去,也是個蟬鳴之季;蓮荷満池,閃耀成嫩紅雪白的絕美夜色,老人在蟬噪聲中低吟輕柔的搖籃曲:「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吋,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搖嬰仔歌累了於是睡去。倏地翻身,耳邊傳來嚶語:「阿嬤,呷藥仔啦。」天光原是亮的,失了神彷彿就晃過幾個漫漫的仲夏。 想起來了,阿嬤從來沒有哭過,阿公過世的時候也沒有。女孩三歲發了高燒,咳個不停,整日昏睡。雙腿患著風濕的老人到山裡採草藥,煎成一碗黑黑稠稠的東西,女孩大哭著打翻藥碗。阿嬤沒有哭,接著在冷風颯颯的大過年裡走了幾里的碎石子路,費力敲著診所的門。幸好醫生一家都在,但阿嬤劈頭便遭了狠狠一頓罵:「小孩子燒成這樣才送來,會變白痴你到底知不知道?」醫生娘在一旁答腔:「沒知識的歐巴桑你罵她也沒用,小孩趕快送大醫院要緊。」 阿嬤坐在病床邊,女孩吊著點滴,兒子匆匆趕來。 「阿母,阿惠是你堅持要自己帶,要是有什麼閃失你怎麼負責?我還要回去開會,不要害我分心!」 阿嬤忍著縮著不敢抬頭,雙手夾在兩腿之間,無助、慌張散布整間病房。 紅霞晚照,將一家家裊裊升起的白色炊煙染成了溫橘色,逐漸逸散。灶前女孩默默生火。電話難得響起,鈴聲惶惶,彷彿戰情告急。她探頭一看,阿嬤在正廳裡抓著話筒,眉頭有著深溝,聆聽由香格里拉捎來的詭密訊息。女孩突然升起一種戰士必須捍衛家園的心情,火光熊熊,奮力扔進去的柴枝劈哩啪啦爆出火花,壯烈犧牲。 祖孫三人保持一貫沉寂。在日落以後,老人濃濁的呼吸聲異於平日。她意識到某種危險,這座危危顫顫的小城即將頹圮,成為歷史廢墟,或是隨著夕陽沒落,隨炊煙昇華。相對於母親說的繁華台北,燈河悠長,這裡是一種黯然灰敗的狀態,傳達給她無法拯救的垂死訊息。 未知生,焉知死? 三叔公的弱智妻臨盆,昏黃的殘燈下燃起一絲新生命的喜悅。叔叔嬸嬸卻帶著簡單的行李趕夜車,急切切北上桃園。蒼白的燈影中兩隻羽翼不全的蝴蝶準備飛向另一個充滿險惡的美麗所在。大人都走光了,這裡只剩老人小孩,一隊沒有武器的孤軍,一座失去堡壘的危城,生命失去希望僅剩淒絶。黑夜把人帶向另外一個絕境,生命的起落,人世的離合在夜晚顯得更為清楚而深刻。她想起台北的國王皇后,剎那間開始願意做個被遺忘的公主,守著小城,守著蒼老的太后。 四周仍然是一片默然,時光隨著錄音機裡鄧麗君〈小城故事〉的歌聲流轉。唱了一遍又一遍,阿嬤終於開口。 「阿惠。」 「你阿爸明天返來帶你上台北。」 「為什麼?」 「你阿母住院,叫你幫忙顧。」 「你也要上小學,去台北才有前途。」 阿嬤沒再說話,落寞的表情把老人的皺紋拉成灰色的長線,綿延萬里。女孩沒有反抗的力量,也沒有悲傷的勇氣。真正的美麗總是容易被人遺忘,像海市蜃樓,終成幻影。她打開房間窗戶悵然望著,月圓了,明日也將月缺。她與這座小城,從此都有了某種程度的缺憾。 她蹲坐在柴房後面靜靜環顧夜色。夜空深遂,星點閃耀,流動成柔長的銀河如銀色流蘇。她想起母親說台北陽明山的夜空有著夢幻般的美麗,晝時遊人如織,夜晚更為詩情畫意。女孩可以穿著公主的禮服,恣意品嘗香氣四溢的美食,公主於是能夠睡在軟綿綿的大床上幸福睡去,在國王皇后的呵護中再無憂愁。今天之前,她凝聚著期盼,那是醉人的熱情火種,是隨時可以燎原的狂熱光芒,但她現在僅有落落惆悵,灰白色調的世界在夜裡沉淪不醒。 靜穆。靜穆連成整片夜色,伴著稀落的蛙鳴。 女孩悄悄踱進阿嬤房間,紅眠床兀自不爭氣的發出沉重的悶響。她心中掙扎了一下,走過去輕輕搖動老人家。 「阿嬤。」 「我想跟你睏。」 「恩。」 阿嬤翻過來面向她。她看到阿嬤的眼睛像星星,閃耀著星光的一面湖水。 阿惠爬上床,一老一小並肩躺著。 面對明天,她絲毫無欣喜之情,像生命裡某種珍貴的元素將被抽離,阿嬤輕輕哼著〈望你早歸〉,時鐘滴答是生命的流光,抓不住的悠長。 「阿嬤。」 「我們一起去台北。」 「阿嬤歡喜在這。」 「這裡卡自由自在,去台北關牢籠阿嬤不習慣。」 她惶恐的翻過身去,緊緊環抱住老人漸衰的身軀。忽然覺得抱著的動作有實在感,抓住了老人為了她而逝去的玫瑰歲月。她有一種感覺,人生最大的遺憾,不是面對死亡,而是來不及告別。 「到台北要乖,聽阿爸阿母的話,不要亂跑。」在魚肚白的微亮清晨,阿嬤摸摸她的頭叮嚀她。老人家艱難地蹲下來,慎重的把麥芽糖餅放進她紅色背心口袋,動作異常緩慢溫柔,卻像斷腸的心碎。 「阿嬤,」女孩認真地說。「你要記得吃藥,那個咳嗽藥青包早上要記得吃,還有膝蓋痛的藥膏在左邊第三個抽屜裡面,……」 老人轉過身去擦眼淚,天色蒼茫,散開的霧又聚攏起來,濕氣凝重。 阿惠頹坐在貨車上,遠遠看見阿嬤背著哭鬧不休的弟弟向她大力揮手。 「阿嬤───」她放盡力氣大喊,聲音仍被風削去了。 現在想起來,那眼淚是淒切的哀愁,她和阿嬤共有。多年後,她才知道,這居然是穿透靈魂的鄉愁,錐心刺骨。 繁華台北愈益繁華,破落小城卻斷了訊息,女孩在異域艱苦成長,模糊的記憶卻嵌著阿嬤的臉,那是種極度複雜的表情,面對生離死別,似乎故意漠視卻被迫強行面對。她還記得阿嬤離別前的強顏歡笑,掛著兩行寬寬的水痕。 很久以後的某一天,繁華台北刮起了風,帶來香格里拉的消息,死神的音信。老人生命殞落賦予她的意義,也象徵著一座孤城朵火的幻滅。她從此不再想起,卻偏偏在午夜夢迴回到映照著溫暖月光的紅眠床。隱隱約約的懷念……。 小城有故事嗎? 有的,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故事。 有個美麗的小城,香格里拉,女孩與老人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有一天,女孩離開了香格里拉,從此魂牽夢縈。老人日日倚窗等待,望穿秋水,生命隨著小城的沒落迅速蒼老,直到生命之泉乾涸。 女孩,投入城市的洪流,卻無法自抑地懷念著落葉紛飛,山雨欲來的那座小城。 再見,香格里拉,夢裡再見。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