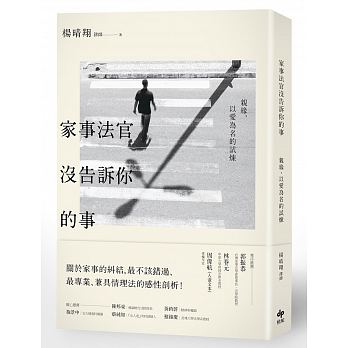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7/11/03 21:30:19瀏覽1450|回應0|推薦8 | |
※《家事法官沒告訴你的事:親緣,以愛為名的試煉》,楊晴翔著,悅知文化。 【前言】 最近來不及寫閱讀摘要,就把自己看過的書打成期中報告,於是現在閱讀筆記居然只能用期中報告呈現...(掩面哭),我都不知道怎麼跟過去系上的老師交代.......。 這本書是一位律師以過去曾任家事法官的經驗所作,書中的案例經過層層改編,看起來彷彿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則小故事,但小說往往比現實還真實,畢竟現實得讓我們自己來建構(這就是動態涵攝了).......說到這個,這次刑法實務,我沒有考好,老師說他還多看了我的試卷一下,檢討考卷時還一直過來看我的答案,看一次損我一次.........=___=||| 至於為什麼沒考好,其實我這次幾乎都沒怎麼考好啊(除了性平老師很喜歡我寫的申論,以及行政法老師意外地給了還不錯的成績,行政法我並沒有精確地背教官給的定義,完全用過去國考的印象寫...)....而刑法部分,大概就是我太仰賴正確答案了,所以封閉了思考,所寫的偵查面向過少之故,但如果指其他科,真的就是沒在認真地背好的關係(基本上學科大多是訓練短期記憶,把書一字不漏地背起來~),結果目前考得最好的,其實是刑事鑑識呢....當初我是不是該選三類呢? 但這次期中考期間照樣練跑,還是有點收穫的...雖然不在期中平時測驗裡,但今天體能課跟大家一起跑,順利達標了,大概進步了四十幾秒。 話說回來,這本書相當有意思,如果不是因為期中報告可以用到,我可能不知道民國幾年才會把閱讀筆記寫出來,於是再次用報告暫代筆記。只是,我們的時間太少了,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將要結訓,班上現在充斥著對成績的、對未來的不安的氛圍,畢竟成績關係著分發地區的填選,而我大概也只能靠著微弱地特考成績,稍微讓自己前進一些──現在的我對於分發,只是單純想著,若無法回家鄉,至少也還能留在彰化,回來看看教官們與區隊長,我命雖由我,但有很大部分也由天吧。 剩下五十幾天,我跟極少數的同學也想著趁現在還有機會能問老師們問題,就得趕快問──性平的教官很常被我們問保護令聲請的程序、流程之類的相關問題,畢竟實習時,同學們幾乎都會遇上家暴相關的案子,只能希望這世上無辜的孩子們都平安......。 -- 【正文】 性別平等期中報告─關於性別、場域與法律 「女性和寫作」,可以說是女性和她們的樣子;這樣子很可能就是你們的原意;但也可說是女性和她們所寫的小說,…….但當我開始用這最後一個角度,也是最有趣的角度來看這題目時,馬上就發現了這個要命的問題,我永遠講不出個結論來。 -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間》
吳爾芙主張女性必須要有自己的房間,擁有自己的資產才擁有真正的自由,而上段所示即說明了,「結論」是父系敘事結構中的封閉概念,性別本身是一個發散的體系,擁有各種可能。而性別平等所涉及的性別定義、權力場域、女性主義之發展歷史脈絡牽連甚廣,在解構主義突破統一思維後,誠然是一個相當大的議題。
性別問題常被扁平化,甚至被某些沙文人士訕笑,誤解為女性爭取自我權力的議題 (甚更狹化為生理性別的女性問題),但須知弱勢性別早已不僅指稱生理女性,而是泛指為各種因性別歧視所苦的弱勢族群,他們不被大眾普遍接受,失去自我定義、自我尊榮的空間,而那些本是原屬於他們身為一個人類,在這社會組織底下本擁有的基本權。
當我們談及性別平等,所涉及的是解構父權,並使之賦權的議題,當個人因性別問題而遭受歧視或暴力,而身為執法者,甚更身為一個人都不應允許這種迫害的持續。
性別主流化所欲抵抗的權力關係
你穿起女裝竟恰到好處呢,真是美,怎麼說呢, -成英姝,《男妲》
關於性別論述,最早依然須從兩性的權力分布與分配中談起,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即為生理男性取得主導權的漸進史[1],當人類聚落從畜牧進入農耕,從採集進入需投入大量勞力的種植,母系社會漸漸崩解。
而權力場域的不穩定,傅柯《性史》中,從結構主義的方向說明性別權力關係,性別結構網絡中的不平等,並說明權力/知識的關係並非靜止的分布,這權力關係會不斷游移,強弱間並不穩定,是故鞏固這權力結構,則為既得利益者的首要任務,於是不斷地厭棄女性身體、否認女性擁有靈魂一事,均為歐洲中世紀的主要論述脈絡,但也因為這重擊,使得性別議題終於躍然而上,女性漸有發生。
性別概念早遠遠超越了生理性別的二元限制,陰性、陽性特質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人身上,但不一定被意識所察覺,榮格將這特質視為人類的內在心靈結構,並將之稱為「阿尼瑪」(anima)、阿尼姆斯(animus),然而父系社會太過害怕自己對陰性特質的嚮往,擔心權力甚至位置被掠奪取代,所以在面臨任何挑戰父系社會所建構的知識架構,勢必被迫害。除了成英姝所描寫的《男妲》一作,我們能一窺性別歧視、性別麻煩於個人特質上所展現的魅力及人類多樣性外,也同時能從中了解不為他人所理解、為他人所恐懼、厭惡的人們的心情。而於2000年所發生的一起令人心痛的國中生不明原因死亡案,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亦是我們今日所要討論的多元性別的血淋淋案例,這名國中生因其較為文弱的性別氣質遭到同學,甚至老師的霸凌,連下課時間都不敢如廁。2000年4月20日早上,該名學生在下課提前離開教室去上廁所,卻被發現倒臥血泊中,可惜送醫後仍過世。這件事情促使2004年《兩性平等教育法》修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也使得LGBT的概念逐漸普及,而多元性別的教育也逐漸受到重視,然社會氛圍卻依然對多元性別不甚友善,近幾年來相關抗爭四起,身為執法者,我們在支援陳抗之時,也須了解這些民眾是如何長期的受迫、被漠視。
家庭暴力裡的權力關係與家庭暴力相關法制「性」並非如佛洛伊德所認為的是一種難馴且不斷須被壓抑的事物(佛洛伊德所指稱的性為「LIBIDO」,常譯為「原欲」),傅柯將之排除為其可能為原欲、性徵等各種指涉,而將之純化為一「名詞」,這名詞成為一種普遍的「知識」而得以被操作。
然而權力關係既然以知識架構存在,那麼家庭暴力中的性別強弱亦可能產生轉換,首先我們必須了解一個家庭組織裡,有暴力行為的不必然是生理男性,且不必然是因其配偶關係,在實務中我們亦常見到以其兄弟、兒女為相對人聲請保護令之狀況。
而在2016年2月4日,新施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六十三條之一,也就是著名的恐怖情人條款,更是反應了新的社會需求與親密關係,提供年滿16歲以上的被害人,如果遭到「現有」、「曾有」親密關係的伴侶(不限異性、同性),無論是身體或精神上之暴力、騷擾與跟蹤、控制等行為,都可向法院聲請民事保護令,而社群網站的紀錄亦可以作為其聲請依據。
身為執法者,我們除協助其聲請保護令外,其實有著更基本的事項須告知: 一、告知民眾須善用一一三婦幼保護專線:該專線由專業社工提供24小時的電話接聽服務,而其中內容涵蓋了家暴防治、兒少保護、性侵害等協助與救援。 二、盡快到醫療院所取得診斷證明書、收集照片或破損衣物等相關事證:法院採取優勢證據法則,只須讓法院在兩造提出的證據兩相比較即可,無須採取「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只要有被害人之陳述、診斷證明書,只要家人無法提出合理或具體事證反駁,保護令就很可能和發現來了。 三、保護令有時限,必要時可延長:原則上,通常保護令是兩年以下,目前並無延長次數限制。
性別平等議題、執法情境裡的孩童心理防衛機制
我最愛坐在客廳沙發的正中央,右邊坐著爸爸,左邊坐著媽媽,我們是幸福的一家人。但有天她倆外出,一場車禍,從此以後只剩下我還看見爸媽雙方的世界……。 ─〈so-far〉,乙一
知名日本作家乙一,曾描寫過因夫妻雙方不願溝通而迫使家中孩童選邊站的文本,孩子做為雙方的傳聲筒與出氣筒,最後終於在大腦中無意識地做了選擇,從此他只看得見母親,在同一空間裡的父親,他再也見不到。
乙一描寫孩童的心理防衛機制非常傳神,也體現了孩童在家庭結構中,為了生存必須倚靠雙親,而不得不選擇立場的艱難狀況,當一個案子涉及到家庭、涉及到孩童的親權與監護權時,有時父母某方會以對方對孩子不好,莫名跑進派出所詢問聲請保護令以達獲得監護權的目的,然而告知除了告知親權、監護權與保護令之間並不必然存在關聯性,判定孩童的真實心意其實亦並不容易─因為孩子的戰場,可能就在這家庭裡。
身為執法者,我們所要了解的,除了是性別論述所建構出的知識體系外,更需具備的是了解性別歧視背後的權力關係,這權力關係底下所產生的弱勢族群並沒犯錯,他們的心靈以及基本權(包含Maslow所言地安全需求、自尊需求等)的保有,也是我們需同理且為之守護的任務。
孩子在無力停止父母間的爭吵或衝突時,可能選擇與其中一個父母結黨的方式,去排斥另一個父母,很多時候這種選擇是在無意識下發生的(saposneck)。孩子這麼做的時候,為的不是不讓自己在忠誠度衝突的漩渦裡淪陷,是一種精神抵禦的功能。這是所謂的「父母親疏離症候群」,強烈排斥父親或母親的會面交往。[2]
而在性別權力關係失衡的場域中,除了當事人外,守護第三人,特別是孩童的心靈更是我們的首要工作,人並非在完全成熟後而成為大人(成為父母、成為師長),而是經由學習、領悟而漸漸成為,但在這段經歷裡,對孩子們的各種錯待,卻可能成為影響他一輩子的創傷記憶,了解性別相關法規、家事法規,我們才有足夠的智識來面對各種性別案件,盡可能減少性別衝突帶給當事人、少年孩童們的傷害。
|
|
|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