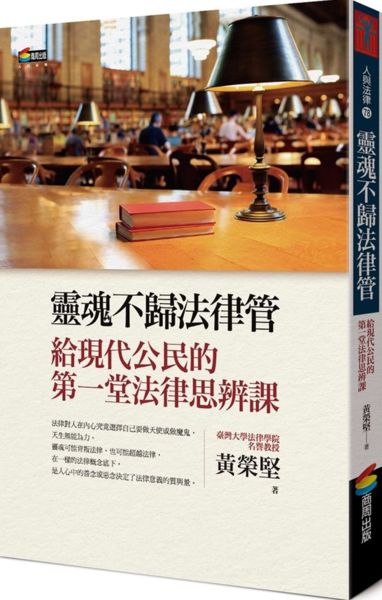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7/10/22 13:20:07瀏覽2637|回應0|推薦1 | |
|
※《靈魂不歸法律管:給現代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http://www.cite.com.tw/book?id=73503 這最近要生出一篇書評都完全沒時間啊,所以先暫時「刑法實務」的報告代替(ㄟ),作為讀書紀錄── 這份報告,以黃榮堅的《靈魂不歸法律管》作為依據來書寫,主要只是為了陳明「動態涵攝」的概念,也是刑法實務的老師急於想知道同學們是否了解「素樸事實」、「動態涵攝」等觀念,因而要求我們繳交的報告。 其實我們的刑法課一直都相當有趣,我們的老師是在彰化地檢的檢察官。上學期老師突然在香菸案(某A在跟店員聊天時,指定了某牌的香菸,並趁店員在忙時,突然拿了香菸就走),考大家「如何偵查」、「如何進行筆錄詢問」,讓習慣書寫論罪的同學們屍橫遍野(大家都寫了行為評價)。 但我記得,那時拿到那份考卷時,我覺得非常好玩──反正我術科便是那樣了,而學科大家的成績都差不多,那一分、兩分更無法補足我跑步的落差,所以寫這種新題型,我也沒什麼成績的顧慮,於是我便順著題目的挑戰答題,結果拿到大概九十幾分的成績,原以為大家的成績大概都如此~但沒想到,居然是刑法課程中相當高的成績@ @ (後來同學們在期末時問成績,看到我的刑法成績時,便很好奇地問我為什麼會高這麼多……我就照實答,真的是因為我沒什麼落敗的顧慮,而且比起那個,我通常都會被眼前的挑戰吸引,當時同學們還是照樣寫論罪,是因為怕不這麼寫,會拿到很糟糕的成績….人類會被這個所困囿,真是因為我們的自我價值總是建立在排序之上啊) 這學期刑法實務的有趣度又爆升,因老師這次居然從他自己的實務中出題,所以在面對這老師所提出的問題時,因這些題目較之考古題有著更高的真實性、不確定性,所以討論的空間更大,而所適用法律的範圍就更加模糊.......案例中包含公務員貪瀆、毒品防制、青少年犯罪以及風化案、性侵案等,這些案件必然會成為我們未來勤務中的常客,老師問我們針對這些案例,我們應該思考哪些可能性?如何偵查?如何適用法律要件?以及如果如此適用,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為了要了解我們是否了解「動態涵攝」的意義,所以讓我們繳交了這份期中報告~ 受訓時間,我想~真正比起外面課程更有價值的,就是這幾堂課「道路交通事故」、「刑法實務」、「刑事訴訟法實務」(我不會說受訓期間不會遇到搞不清楚自己在教什麼的老師,但很幸運的是這幾堂實務課沒遇到.....遇上這種老師,一開始我會相當生氣,覺得被謀財害命(下行註)了,摀著耳朵聽課,連老師在敲我桌子時,我照樣摀著耳朵看書,後來同學們說我的抵抗表現得太明顯,所以我現在會把手放開,但似乎還是很明顯...→強烈覺得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是楊門一家,不是說學生會跟指導老師越來越像嗎?我的老師會在校務會議時,若聽到令人無言以對的發言,就把筆放下,趴在桌上.....) ※魯迅:時間就是生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無異於謀財害命的 我們班相當幸運的是,這幾堂實務課程,都有很棒的老師在授課,如果不希望自己將來是以一張白紙的狀態進入職場,這幾堂課一定要用心....其他的,可能就是看造化了
「刑法實務」真的是這段受訓日子中,非常意外地有著大收穫的課程,希望後來受訓的同學們,能夠真心投入這段學習(刑事訴訟實務也很棒,但我一開始沒有刑事訴訟的基礎,所以無法比較與一般刑事訴訟課程的差異)
--- 【正文】 《靈魂不歸法律管︰給現代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與動態涵攝
「動態涵攝」一詞,其實在刑法相關文獻、討論中相當少見,但其概念在實務中卻在在呈現,偵查過程中的檢警,必受現場時空、證據的限制,需一步步發掘新證據,進一步了解案件真相,而這過程中所踏出的每一步,在檢警個人的價值體系中,因其思考脈絡,使得事證、線索的發現產生改變,真相並非一個靜態的標的,而是逐漸由檢警於該件的偵查過程中,一一建構而得出。
浮動的真相與動態涵攝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不可能像是看推理劇、看小說般地去理解每個來到自己身邊的案件,沒有合理的動機、沒有已被規畫的文脈、沒有作者的寫作與思考慣性等線索可以去推測案件的全貌,我們在真實世界中更不具備全知的視角,在這個對當事人可能完全陌生的案件中,執法者、審判者所面對的,是一個浮動的事實、難解的人性,如黃榮堅於《靈魂不歸法律管》一書中所言: 問題是讀者看到的是從作者角度以文字呈現清楚案情發展和清楚證據背景的書,法官調查案情時面對的是不清楚的案情和意義不確定的證物。[1] 這些「不確定」編織出一個待解的謎團,與該案相關的檢調人員必須致力於抽絲剝繭,並在深信唯有越接近事實真相,才能做出正確的詮釋與取捨,而法官們亦須依賴不知何時才會出現的新事實與新證據,重新對整個案件進行價值判斷。然而,如同黃榮堅於《靈魂不歸法律管》一書中所言: 對事實的認定是困難的事情,因此我們也沒有把握說,一個案件裡所認出來的事實就是真的事實。為什麼事實的確認有那麼困難?姑且不論,即使事實在我們眼前上演,我們也會誤認事實,更何況法院裡的案件。[2] 而誤認事實更是常見的狀況,在真實世界中,檢調偵查、法院審判中沒有英雄的存在,有的只是一群努力想將該案關係導正的人們,使被害者得到聲張、使得加害者能夠伏法,讓各方利益(無論是財產或精神的),能各歸其位。
而不同人循線的方式、各式的價值觀,都會產生各種相異的詮釋,即使該案件事實穩定、明確,但各方詮釋依然而產生不同的結果。這當中牽涉到偵查、審判中的檢警與法官們的各自心證,雖唯有法官的心證才有可能讓案件的判決產生既判力。但檢警所調查而出的證據,以及其循線的方向,因其主動性亦會影響到法官最後的思考與判決。就算進入了審判程序,各級法院又因各法官的價值觀與詮釋不同,同一事實可能會導致不同的行為評價結果。 其實思想規則除了就是思想規則之外,更深遠的意義是在形成一個人的獨立觀點。[3] 法律學問無論是在抽象法律的訂定或是具體個案的法律適用,都是從一定的事實基礎加上合於邏輯規則的推論去尋找問題的答案。雖然邏輯只是思想時的推論規則,這些規則本身並沒有生命的存在,但這些推論規則是思想效率所依賴的基礎,因此也是探求正義的途徑所不可或缺的工具。[4] 黃榮堅《靈魂不歸法律管》一書所談及的法律專業部分並不太多,取而代之的是較為淺顯的、白話的,對讀者進行思想層面上的闡述,於是在本書中,黃榮堅真正堅持著的,其實正是思想的塑造、執法與立法者善良的本質,前者影響個人價值觀,後者則牽動著對每個案件求真的願望,並為之減緩傷害。如他於本書中提到的: 法律的詮釋在正義理念上本來就是要容忍無窮盡的想像和主張,因此即使魔鬼戴著魔鬼的面具而來,程序上魔鬼也有權利對法律做詮釋。只不過既然是魔鬼詮釋,所詮釋出來的也是傷害整體社會利益的法律詮釋。雖然政治掌權者所做的決定後來也須面對法律的檢驗,但那通常是在已經造成傷害,或甚至傷害根本無法平復以後的事情了。[5]
高橋亨曾言:「自己與他人相對,因此,為自己所做的事情並非為他人而做的,然而這樣反而會有害人的情況發生……在此情況下,只能用義來制裁,不是減少己利就是削減人利……。[6]」 「正義」在儒學解釋中,亦可指為將利益重新分配,亦即「分配」本就為正義的概念。而如何進行分配而使之公平,取決於法律的使用者。
如廚房中可能有著雞蛋、牛肉、芹菜、番茄等食材,卻因掌廚者的不同,有人烹調出羅宋湯、芹菜炒肉片,也有人便作出了壽喜燒一般,食材雖已受限,但依掌廚的烹調慣性與口味,依然可能變化出不同的料理。而法律的適用要件就彷彿廚房裡已經既定的數種食材,某甲殺人越貨、某甲傷害他人,這是一既定事實,然如何說明當時狀況、考量某甲的行為應受如何評價,如同食材本質雖然不變,然依烹飪者的廚藝與烹調手法,亦產生不同的料理。法律雖係一種規範人的行為的工具,但卻因其為工具的被動性質,其作用能載舟亦能覆舟,法律效果將因使用人的關係,呈現流動的狀態,儘管其應用以邏輯為本,但使用者的心念則會影響到論罪、評價行為的結果。 詮釋奠基於思想 而社會思潮的推進,自然也會牽動法律的成長,現代社會是一個多重價值的時代,而對每一種聲音波動,進影響到法律的上位階概念與思想之時,也會影響到立法目的,舉凡如毒品罪、通姦罪、死刑等相關討論,亦隨著時代演變而產生異於之前的面貌,常聞報章雜誌說:「毒品現在罰得太輕,甚至比酒駕輕多了,這就是毒品氾濫的原因。」而毒品相關法律的適用,其實也正是我們將吸毒看作為「罪」或「病」這兩種面向,正如黃榮堅所言: 對於法律問題基礎事實的確認,本來就經過應用基本通識的推論過程而來的,換句話說,所依賴的主要是思想。[7] 因社會思潮的反省與演進,除討論毒品濫用的行為評價外,立法者也不斷受兩種刑法價值挑戰:刑罰的概念究竟是為了懲罰犯罪,又或是為預防犯罪而設置。而牽動立法目的的變更以及刑罰的輕重,立法者的思想佔了相當大的因素。
只是法律永遠不僅僅是立法者、執法者的事情,儘管法官有自由心證的自由、檢警各自有取證的方式,但社會輿論依然可能動搖判決的結果,畢竟能接受千夫所指的人僅在少數,關於此點,黃榮堅說明道:讀書確實是一種現代公民應從事的行為。
黃榮堅提出這點,充分體現了「閱讀使人自由」這句話的意涵,現代社會講求自由,對自由進行各種定義,而操作人的意志最主要的,即是個人價值觀的展現,若閱讀本身不能讓你變得更理性或更感性,變得更能同理他人、更為善良,那麼閱讀是無效的。
法治社會裡的公民享有自由,但也須同時尊重他人擁有自由,如此才能讓利益盡可能公平地為眾人所有,有限的資源不至於失衡,當人類思想前進到使得利益漸可能為眾人所有,並為此制定法律─「憲法」,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理所當然亦須尊重他人實現這些權利,而了解與尊重源自於對世界的觀察,一個人類在其有限的生命裡,不可能活過幾千、幾百個世紀,對於世界的了解可能在生命結束時嘎然而止,但透過閱讀浸溽生命,或許能使得其智識發展延展,若我們不能站在各個巨人的肩膀上觀看世界,持續著自己的偏見與傲慢,人生短短數十載,手中的紙本盡可燒了吧。 求真的善念與態度的選擇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 (劉鶚,《老殘遊記》第16回)
此為清代小說家劉鶚在《老殘遊記》中,對清官的評語。探求事實、挖掘真相有何不對?今日的檢警,我們對其品格操守有著一定的信心,然而剛愎不識人心卻為其弊,作為一個好的偵查人員,如黃榮堅所言,必然有著求真的盼望,但當我們在實務中面臨的是人世間糾結的是非,又該採取怎樣的態度來面對,黃榮堅亦言「採取態度」的重要性: 剩下的只是面對問題的態度問題,因為只有態度可彌補人的低能問題。那是帶著慈悲意味的態度問題:既然對事實的理解是善良的前提,那麼如果我們心存善念,必然會有求真的意願。[8] 這「求真的意願」起源於人性固有的善良,雖善念則源自於對他人的不忍人之心,當我們越是理解人心的脆弱與現實的艱難,儘管希望善惡因果各歸其位,但既然善良的前提是對「事實的理解」,那麼執法者、審判者的善良必然擁有鋒芒,我們偵查、還原事實真相的目的,也在於降低該案件對當事人的傷害,並避免傷害繼續滋長、延長,無論是否溫暖,那依然是「制裁」的姿態。
而態度的採取必也奠基於足以進行邏輯思辨、感受他人所感的智商,在要求自己理解事實,避免自己於推論案件事實時產生明顯偏頗的前提下,我們逐漸了解到自己所知的極限,於是主張「證據會說話」[9]變得艱難,案件的詮釋最終會回到自身,要「說話」、「取捨」的始終是自己,於是你不能再說自己沒有立場,做出某種評價必然有其立場,而這立場如何確立一直操之在己,於是你有怎樣的生命深廣度、有什麼樣的信念,亦左右了案件的走向與他人的人生,如黃榮堅於《靈》一書所言: 最後重要的是你的高度決定法律的高度,所以你對法律的詮釋也是你對自己的詮釋,換句話說,這也是做人自我定位的問題。如果人的類型有快樂不快樂的問題,那麼對待法律的態度也有快樂不快樂的問題。簡單講,法律只是技術,只是工具,比這更重要的是帶著善念的靈魂。[10] 如黃榮堅所言,我們如何適用法律,亦表彰了自己是什麼樣的人,雖如上段所示「帶著善念的靈魂」相當重要,但我們的思想高度,在其案件結果的主導及影響上,卻更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動態涵攝的過程中,思考邏輯的偏差、對案件構成要件的誤解,將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可怕後果。因此執法者與審判者,在自我人格與自我概念的建構上,除了須具備不忍人的善念、求真的態度外,思想的深廣度以及對人世的洞察,在我們發掘線索、涵攝法律要件並以此建構法律事實之時,占了更大成分的主導地位。
[3] 黃榮堅,靈魂不歸法律管︰給現代公民的第一堂法律思辨課,商周出版,頁112,2017年。 [6] 林月惠、李明輝編,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台大出版中心,頁262,2015年。 [9]「但「證據會說話」這一句話只是舉證者主觀上的表態,自認對事實主張已經提出無法被推翻的完美證據。」(《靈》,頁104。)
|
|
| ( 心情隨筆|心情日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