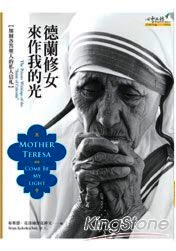原來是個美善的誤會
Sholoshoti看起來四十歲左右,是個中風的病人,除了左半邊的身子不遂,身體的狀況大致還可以,能吃能喝還可以自己坐在地上拖著身體上洗手間。 我剛去時,還曾看到她佇著拐杖艱難地行動,自從一次摔倒頭部受傷後,她床位旁邊的拐杖就不見了。看到她要從床邊椅子移回床上,或是跟我說她要上洗手間,我總是吃力地幫她扶她挪著身子,後來,看到一位退休後來此長居的日本志工Sumiko,是挪動座椅到床旁讓她自己用健康的右手撐著床躺下,或是用這個方式下到地上去洗手間,這才恍然大悟,原來Sholoshoti告訴志工要下去或上廁所,其實只要把她移動椅子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冒著閃到腰的危險辛苦地去搬她,或勞師動眾去找人來扛,很累的。所以此後有志工要搬她,我總會跟她們說,她會自己上廁所,讓她多活動。
有一次聽Tomomi說她前一年第一次來時,Sholoshoti還可以拄著拐杖走的,現在沒有繼續做復健,幾個月的時間就退步到只能在地上拖著身體移動;那時候Tomomi都每天帶她做復健的。聽到這麼一說,剩下的兩個多月時間,幫她做復健就成了每次到時的一個重點項目了。剛開始我只是幫著按摩手腳,後來看忠愛修女曾示範怎樣活動她的手跟腳,她看我真的是很認真固定幫她做,就找來一條粉紅色長褲給她復健時穿。 幫她做手部擡高動作時,她常會喊痛,我一定告訴她,痛沒關係,痛才好。
有一天我一到,就聽到她的大嗓子在講一堆什麼的,像在抱怨什麼似的講個不停,睡她上層的Shepaly說她已經叫了一整天了,還邊哭邊喊痛。我那天就讓她休息,正好口袋裏有幾顆糖,就把糖給了她,封了她的嘴。這邊的病人有些真的很像個單純的小孩,跟她們互動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此後,住處如有什麼零嘴,我就帶著,有時幫她做完復健就塞個幾顆給她。有一次,她又拗在那邊不願動,我就把預先擺在工作圍裙口袋翻開給她看裏面旳糖,這個像是賄賂,又像交換條件的動作,給旁邊一位德國來的復健科護士看到可笑煞她了,不過有時零嘴真的可以打敗Sholoshoti的偷懶。 在幫她復健的這段期間,我最常說的孟加拉語,除了「不要偷懶」,還有就是從已經學會的數數一到五,再擴大到二十,這中間,有時我忘了,一時想不起來時,她就順便教我。
到了我服務最後的那一天,總算讓她靠著助步器走到復健腳踏車的地方,去做一次踩腳踏車的運動。以後她會不會有人再繼續幫她做復健,我實在也無法預料,不過至少我在的時候,讓她有段時間是有活動的,而且有明顯的進步。忠愛修女調到痲瘋病患中心了,我也離開了,不過還有個專為病人做復健,做了二十年的印度男志工Vineet,因為我請教過他幫忙Sholoshoti復健,所以,只要他們都在,他幫完現在的那個胖胖女病人,總會找上她的。
眼藥水點開信任的眼睛
有一個矮小的病人,是因為腳傷進來的,不安與畏縮地躺在床板上;最初幾天,我看到她的眼睛紅紅的,不斷的有分泌物及淚液流出來,修女要我幫她點眼藥水;看到有人要踫她的眼睛,嚇得要命,驚恐地一直喊著na, na,na(no不要),第一次很困難讓她乖乖睜著眼睛。她兩隻眼睛,只剩一隻可看,到這個地方來,有個陌生人一來就要抓她僅有的眼睛,那種恐懼與驚駭也可以理解的。
第二天我又試著幫她點,這次比前一天稍微好一點,接著幾天都幫她點,她的戒心與懼怕,隨著眼睛的狀況越來越好,而日漸消失。 當她可以到處走動時,就開始找人串門子,或看哪裏有需要幫忙的,會看情況幫點忙;看得出來她很高興也很感恩能在這裡。
有一次,一團穿著體面的日本婦女觀光團,帶著戒慎恐懼的神情進來參觀,這位病人大概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穿得這麼漂亮離她這麼進吧!她走到其中一位女士的前面,雙腳跪下雙手踫觸她的鞋尖,再把手放到不知是額頭或是嘴上踫一下,我猜測那是一種尊敬的動作,但是被踫到的五十幾歲女士,可不這麼認為,只見她臉色大變,面露恐慌一付不知馬上逃離現場,或是繼續站在原地手足無措的窘狀,果然不到一分鐘,就消失在現場了。這團導遊的誠意與熱心,可也難為了這些日本貴婦們了。我想如果這位女士能像其他的日本志工,在這裡稍稍再待一下下的時間,那種恐懼感大概就會減少一些了吧!
這個由疑慮轉為信任的病人,在該走的那一天,讓修女幫她打點得乾乾淨淨地,穿著一套全新莎麗,揣著修女給她的一些吃的、喝的、以及一個裝著夠她搭火車或巴士回鄉的硬幣小布袋,在病人的目送與志工的道別聲中,高高興興地走出垂死之家。
生命力旺盛、捨美女而就我的老人家
那個疑似腦積水的老人家,每次葉培一到,就拿張可靠躺的大椅先讓她坐起來,再去忙別的。有人關照的日子,老人家通常是精力旺盛的樣子,看到人來了,雖無法站立或行走,但總是一付企盼的神情,抬著頭渴望地望著常照顧她的人,伸出右手朝上像是要人拉她起來的模樣,當你握著她伸出的手时,她會把你拉靠近她,有的西方志工就順勢抱抱她。我絶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遵守垂死之家的守則,不與病人擁抱,所以開始時老人家對我伸手,也並不太瞭解她的意思,只好試著拉她起來看能不能助她移步,幾次嘗試再加上工人告知她無法行走,只好放棄她想走動的渴求。 葉培回香港那陣子,少有人關照到她,我餵Rosy後,或在忙的同時也會抽空看一下她是否有人照顧。
有一天到的時候,看到床上的她不似平素睜著雙眼期待地望著來人,而是矇著氈子把整個人蓋得緊緊地,走過去喚她,卻毫無動靜,試她額頭的溫度似乎有些燙,趕緊去拿了體溫計,一量果真是38.9度,修女給我一顆退燒藥讓她吃了,她昏睡了兩三天後,隔個休假日再去時,她又是生龍活虎地吃喝,伸手找人握,跟發燒時毫無生氣的樣子判若兩人。
此後我就開始注意她的精神狀況,有一段時間,她就是昏迷個幾天,修女予以處理然後過幾天又是一條活龍。這樣反反覆覆幾次,我又開始給她儘量多的食物,不管給她多少份量,她一定很盡責地吃個精光,所以只要時間許可,有多的食物就會給她吃。慢慢地,跟葉培及修女的默契就是,多的食物或較營養的補充品如牛奶、好立克或高蛋白,必是優先考慮病弱吃不下的或是年老體衰的。
照顧她的那段時間才發現她有時還曾嘗試自己起身,結果當然是跌得頭破血流了。由於我注意到她可能因年老或缺乏運動之故,皮膚很容易在搬動或穿脫衣服時,稍不小心被扯破而有傷口,為此我會幫她擦藥或貼上OK繃以防感染;慢慢我發覺她對我也產生依賴感,也開始偶而想開口對我說話,只可惜實在是聽不懂她的話,可能是印度有列入的十四種語言其中一種,只能聽一聽,隨後用無奈的表情,加上一句孟加拉語「 Ami Jani Na(我不知道)」做結論。
有一次,忠愛修女請一位剛來沒多久的歐洲年輕美女幫她做腿部運動,一開始我有點不明究理,跟這年輕志工說老人家常摔倒,不要動她讓她坐著就好,後經溝通及求證後才明白,也跟她道歉,但也許是老人家看到我跟志工的溝通與互動,她對志工的幫忙採的是排拒、喝斥甚至有一次是打那位美女的,然後老人家就抬頭望著我像是求助的表情。當然美女志工每一次總是很盡職地幫她做運動,這時我也盡量不靠過去,但還是有一兩次經過時,老人家總抬起頭來望向我。
我記得每一張服務過的病人面容, 我懷念她們各種的喜怒哀樂神情,感謝她們讓我體驗在別的地方所難能經驗到的,再見到她的機會微乎其微其微,之所以要詳盡地記錄與她們共處時的點點滴滴,是因為在我的生命中曾經與她們交會過,並因而留下痕跡而成為人生旅程中的一段軌跡。
志工始於善止於美的旅程...

工作結束後,到頂樓平台喝杯熱奶茶,配片特有的白餅乾,志工在此交流 到此做志工服務,參與的年輕人以服務經驗的學習,及增廣見聞居多。對於多次或是每年固定期間前來的,應該是回家的感覺讓他們如候鳥般,時間到了就出現在一定的棲息地。至於長期定居的志工,可以是退休後的第二春,可以是高成就的絢爛後,另一種簡單而有意義的生活之尋獲,繼而歸屬之所的長宿。 來此服務的志工,來自世界各大城市各小角落的凡夫俗子有之,權貴名流有之,不拘他們是誰,修女們一概等而視之,因為,窮人之前,人人平等,所以你是美國某一州長或國會議員,是摩納哥國王或是義大利某名導演,修女們都裝做不認識,照樣讓他們去洗碗盤,晾衣服,餵食藥物及餐飯。因此,在這邊很容易就能夠看到堅挺著的身段,很柔軟地就輕輕地放下,放下了之後,被看到的就是無私的奉獻與真誠的付出,這過程走下來的就是一份愛。這些無私與真誠,不僅用在病人身上,也同樣對待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志工身上.
因為這份愛...

所以在待了一、兩個月後,可以看到每天在唱祝福感謝的送別歌的韓國女志工,換她接受別人的送別時,是如何地因不捨離開而淚流滿面,一旁有經驗的長期志工,就會對著不忍離去的志工說,「會的,妳一定還要再回來的。」;馬來西亞、日本的男志工硬ㄍ一ㄥ著,但從臉上神情就可窺知離別情緒。也因此我們就在此看到,即使已來此服務三次的台中的國小教師,每天都高高興興地來,像訪視老友般服務病人、再次遇到曾經一同服務的舊志工溫馨熱情地互動,到了離去那天依然還是不捨還是淚如雨下。每年都固定來服務一、兩個月的米蘭醫護人員Joseph,喀什米爾人Yosef... 所以有人捨原來的高薪與優渥生活,轉而在此定居,可以看到是因德蕾莎姆姆感召,不先收其捐款而要求先做幾天志工而留下來至今己逾二十年的德國銀行家Andy;因緣際會而放棄銳利而燦爛的記者與編劇生涯,選擇符合簡樸環保理念的生活方式的香港八年志工葉培;從很年輕就來此進而度修道生活,與葉培同年到此,至今仍未滿三十歲的愛爾蘭志工Martin;每天在修會學校下完課就來志願服務的愛爾蘭志工Jim;已來多年的法國志工Vincent;注意病人復健的荷蘭志工Alan…

所以有人退而不休,遠度重洋來此找到銀髮第二春的義大利退休的護理長Teresa,日本志工Sumiko,韓國大叔,西班牙Malisha,德國退休傳道人Helmut,到此擔任station worker(志工最前線,每早到車站尋找垂死者)的瑞士志工Albert,西班牙的大鬍子志工... 所以有來自大阪,去年秋天第一次到此服務,便決定申請入會的,現已到馬尼拉研讀神學的Tomomi。 第一次來服務的日本教友Tomomi(右),就決定當修女了,這次是第二次前來,將父母的同意書交給修會,以取得修會的許可.

所以有來自加爾各答本地,家離垂死之家不遠,瞞著知名整型外科醫師母親,印度燈泡大廠老闆父親,攀越嚴密的種姓階級制度,服務上層階級不能踫觸的,可能是賤民(untouchable)身份的垂死者,在一次疏忽的情況下,不小心說溜嘴才讓父母發現,已偷偷在垂死之家當了八年志工的印度加爾各答人Vineet。到目前為止,他已當了二十多年志工,算算時間,應該也是在學生時代就開始了他的志工服務,至今已身為公司主管,仍每天早上先到垂死之家服務到近十點鐘才去上班,每有出國或出差較久的時間,常一到加爾各答,還未回到家,就先到垂死之家去看他照顧的病人。

千千萬萬個志工,他們來,他們去,教友者意義上可能是因垂死之家是德蕾莎姆姆的起源地,或帶有朝聖的心情,非教友者可能是慕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或純為志願服務,總之,在加爾各答的志工幾乎是源源不絕,一年當中的志工淡季大約就屬最為乾旱的四月,到濕季開始的五六月。基本上這裏的志工是不缺的,倒是台灣來此的長期志工,曉萍,有時較有機會造訪南印其他的收容中心,所以得知,南印那邊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是沒有志工的,所以兩年前姜樂義老師所帶領的印度志工團隊,捨加爾各答而就孟買,對既非朝聖亦不慕名,純粹只為志願服務的志工而言,這個走向是對的,畢竟,服務的質性是真誠的呈現與雪中送炭,而未必要蜂擁著去追逐群集,以至有錦上添花之虞。

在台灣,同樣有許多志願服務的機構可供我們付出與學習的,相較於加爾各答,全世界的各國際志工服務據點,可能不太容易找到像這邊這樣以如此低的身段去服務受助者,因為那要捨棄許多用金錢都可以解決的救助方式去服務。到那邊去做一段期間的服務,在日後於其他不同地區服務時,或可有不同的思維與參考。 從每個志工服侍病人以及在休息時彼此之間聊天的態度與神情,常可以看見一股很美的氣息飄揚其中,那是由一顆顆良善與誠摯的心所匯集出來的。 矛盾、對立與衝突之中的接納與融合... 印度,不管在文化、風俗、宗教、人種、語言等各方面,都是極其繁複的,而加爾各答更是集其大成。如此複雜而多元的國家,卻在其中可以見到某種和諧與融合,我想這跟他們八成八的人信奉印度教不無關係,由於印度教信奉的是多元神祇,所以在路上在車上,只要有人看到路旁的任何神像,隨時都會伸出手在額頭與下巴上來回點三次,所以看到許多印度人在聖誕節期間,進到裝點得很有耶誕氣息的東正教聖堂內,用印度教的手勢向耶穌聖像行禮如儀,也就不足為奇了。 色彩在印度是生活上很重要的一環,蒙塵的灰暗街景 -- 道路、老舊商店、英殖時代留下來的建築或斷垣殘壁,全因一塊塊色彩鮮麗包裹出的移動布料而生活了起來,它可以是絶大多數印度女人不可或缺的莎麗,也會是沿途攤販所賣的家用如床單、被套、桌巾、窗簾等,哪怕是多髒多醜的土堆上或帳篷內住的人家,只要是有婦女住在其中,就可平衡掉周遭的晦暗了。而華廈或宅邸外的一些角落裏,有時可見到一堆堆無屋無頂的露宿人家,這樣的存在現象,也能彼此相安無事,這樣的貧富懸殊可以如此地心照不宣,是我深所感觸的衝突與對立並存;若非那牢不可破的種姓思維,印度教所孕育出來的廣納包容,如何可使貧者在這矛盾中安之若素,富者如此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氣壯。

是得恩寵,不是罪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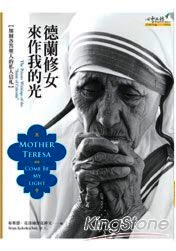
兒子在進高職前的暑假期間難得地乖巧,跟著姑姑學點家務以外的時間,都是待在家的,豈知一開學進了新環境,交了新朋友,生活步調丕變,前後落差太大,這非關學校,因為那還是個名聲與管理不錯的溫馨校園,而是他心性未定,才因而起心動念決定此行。就在出發之前不久,聽到電影「最遙遠的距離」導演在介紹他的這部片時,講到一句話,「當陷於困境,就出走」,讓我很有感覺,沒錯,出走,是先跳開煩亂的現狀,去釐清,去思考,然後再回來,或許另有一番新氣象,或是不同的思維去看待先前的景象。所以到了越接近出發的日子,就越常跟兒子或旁人講的一句,就是,這次能夠成行,也是要感謝兒子;很多事情有時還真的要有些激發元素,才能促成一個行動力很弱的人去完成一些事的。 他在剛到的那段期間,有幾次半玩笑地跟華人志工說他是來消業障的,而到了我準備回來的那個月,有兩次他在我面前,跟台灣來的志工說,他很感謝我讓他去印度,且不究他感謝為的是哪個層面,至少他在情感或情緒上的表達,是有進步的。 就在服務滿一個月的一天晚上,睡前達達提到,沒有上網的日子也是很好的,生活越簡單越快樂。這是真的,我們每天穿的就那麼兩三套衣服,腳上就拖著雙夾腳拖鞋,大家都差不多,不需要一天到晚跟同學比誰穿得最嘻哈,褲子是否夠垮,T恤是否夠大夠寬,球鞋十雙了還覺得少了一雙,誰的遣詞用字最瞎,即使這些稱得上是快樂,還得用金錢才能堆得出來,這樣屬於流行物質堆砌出來的快樂,不也是會隨著時尚而褪色而淘汰嗎?這種快樂的追求,不也像流行的追求一樣地起伏不定嗎?反而,在這邊他發現,原來自己也有一種能力,給予的能力。 在這裹,他看到一些跟他同年齡的青少年,過的日子,與他及所有在台灣的同儕們是那麼的不一樣,有的是在街頭討生活的,如幫傭,苦力,掃街,乞討等等,甚至在垂死之家遇到年紀相仿,因傷入住的喑啞孤兒,這些讓他有了一些反思。就有一天傍晚,下工後回到住處地區,我們一起去買麵包後,走出店門,正好看見一個約兩歲或三歲的小男孩,蹲著正對門的出口,一雙異常大而美麗的眼睛瞪著我們看,那是一個帶著期盼獲得某些給與的可愛精巧小臉。走在回去的路上,兒子突然問了一句,這個時候台北像他這麼小的小孩,都在做什麼? 我聽了有些意外,他會有此思考,我想到的當然就是很尋常的,要嘛正在幼稚園等爸爸媽媽或爺爺奶奶去接他們,要嘛就已經在家或在某個速食店享用晚餐了,而,那個夜寒的晚上,那個小小孩孤單蹲踞等待施與的身影以及那麼可愛掬人的臉龐,始終深烙於腦海。 在離開加爾各答前不久,有一天,義大利退休的七十歲護理長Teresa,在志工洗手枱旁,特別走過來跟我說:You have a good boy。她跟我說的這句話,勝過所有修女及各國志工對我說的,He is a nice boy。只因她是個低調地默默做事,不說閒話,不抱怨,不哈拉,不倚老賣老,不僅專業的事她做,其他的服務工作也做的奉獻者,也是香港資深志工很敬重的人。幾天後他爸爸在網路通上關切達達時,跟他提到這件事,他的反應是雖然高興,但是難過兒子是不是因父母的錯誤決定或做了什麼錯事,讓他要為父母受苦受累,我的反應是,那不是受苦受累,那是恩寵。如果他做得高興快活的話,怎會是受苦受累呢?

經過這段時間在垂死之家的服務,我近日就感覺到自己的改變,更自在地去幫助人。或肇於以往各掃門前雪的觀念,或因台灣現在的社會凡事都多靠自己獨立行動,儘量不去打擾別人,所以就不隨便要求他人之助;就在回來的一個多月某一天,在樓下看到一些血,順著血跡走過去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工人,那兩天在樓上住戶家做整修工程,想必是在搬運時受的傷,平常看到這種狀況,當然會過去看看有沒有需要幫忙的,那工人用植物的葉子壓住傷口止血,也客氣地說不用幫忙,如果是以前的我,聽到這樣的回答,大概也就算了;而在垂死之家看到外傷的病人不少,而我最常做的動作,就是發現病人有小傷口,第一個反應就是去找OK繃;所以雖然那個工人客氣地婉拒,我的習慣反應還是讓我走回家去拿OK繃及消毒的東西而給他用。所以對我兒子而言,或許出於年紀輕,比較羞於做出幫忙的動作,相信現在他會更有勇氣在外面對陌生人伸手援手。 這趟加爾各答之旅獲得的比預期還要多,而且還是始料未及。至於會為他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嗎?我想是有的,但是要怎樣的變,那其實也不是我們所能設定的,只把它當成一粒種子,播了,發芽生長的事,就交給天主吧! 一百多個日子, 每天幾近一樣的行程,吃得很簡單,印度飲食多為素食,有肉吃的話,肉吃得也很少,油膩自然也攝取得很少;交通上,因為地方大要搭個車總也是要走些路,所以走的路相對也就多了,我常玩笑說,在這兒的期間,把過去十五年沒走的路都走回來了;衣著上,因為賣的都是印度人穿的服裝,也沒什麼需要去逛去買的,每天就那兩三套在穿,生活真的是到達了簡單樸實的境界,也真符合現代人想改變的輕食與慢活的健康概念。也因這樣的機緣,才有機會深度體驗這種的生活,而非過境式的青蜓點水輕體驗。 心願是一顆種籽,只要你有過,它就已埋入土裏,不管多久,它就是會有發芽,成長,茁壯的一天… 在這過程中,也許我們會質疑、甚至放棄期待,但是,祂要給的,終究是會給的,這,是天主給我的一堂人生課程…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