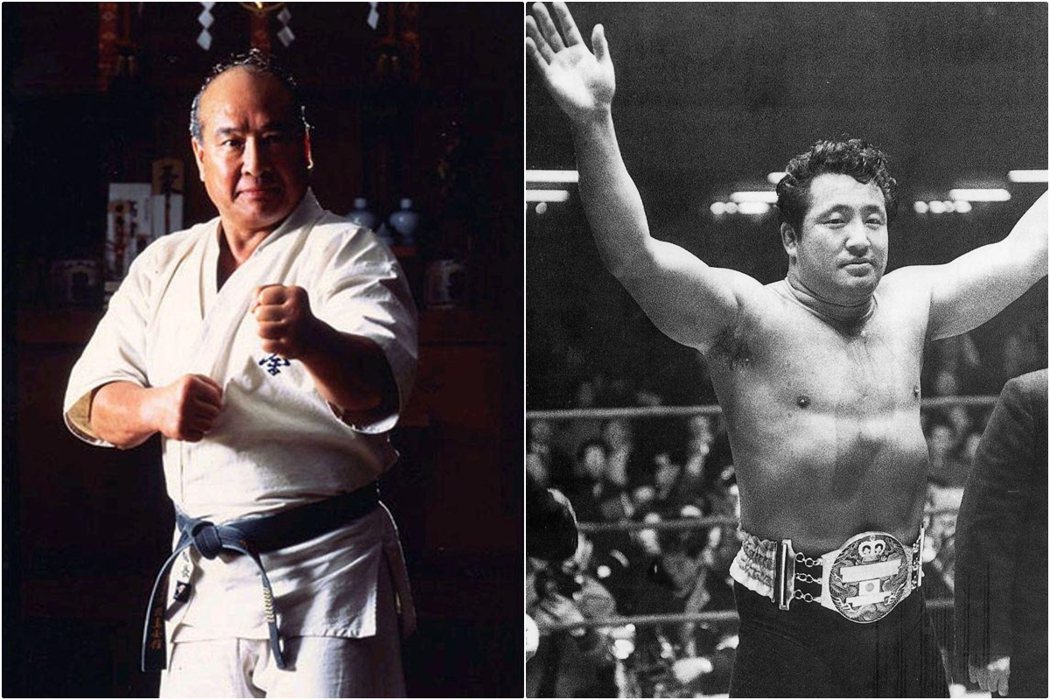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7/02/10 12:25:55瀏覽477|回應0|推薦1 | |
日課綱明載釣魚台是領土 我代表處抗議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287490?from=udn_ch2cate6638sub6656_pulldownmenu 2017-02-16 00:42聯合報 東京記者蔡佩芳/十五日電 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最新「學習指導要領」修正案,在中小學社會科目中,首次明載釣魚台列嶼(日本稱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並特別就釣魚台列嶼部分寫道「不存在領土問題」;我國駐日代表處十五日表達嚴重抗議。 駐日代表處重申釣魚台列嶼是我國固有領土,日方任何意圖損及我國主權的舉措均屬無效。呼籲日方能基於「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之精神,與我國共同維護東海和平與繁榮,避免目前極為友好的台日關係因相關議題受到影響。 日本學習指導要領規定須向學生講授最低限度學習內容的標準,約十年修訂一次。現行指導要領僅提到與俄羅斯有領土爭議的北方四島是固有領土,但未提及與南韓有領土爭議的竹島(南韓稱獨島)和釣魚台列嶼。 這次修正案中,在涉及日本領土內容的小學五年級科目與初中地理課領域中,明確寫進上述三處都是固有領土。
孫揚明》謝長廷太不了解歷史孫揚明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209006349-262105 民進黨政府駐日代表謝長廷日前表示,「美國對於釣魚台列嶼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的立場始終一貫,我們政府也從來不曾針對此點向美國或日本抗議。不是民進黨執政才如此,國民黨執政時代亦然。」此一說法問題極大,大概是不了解歷史所致。 就美國本身解密的檔案來看,很清楚的是,美國至少早在1978年就不是謝長廷這樣講的「始終一貫」,而時離1972年對日本的承諾不過6年。現在卡特圖書館中一份已解密的1978年4月17日的檔案,清楚載錄了美國當時的立場。這是一份由當時美國國安會主管亞太事務的奧森伯格寫給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的兩頁備忘錄。在這份2000年解密的備忘錄中,很清楚地表示,在釣魚台一事上,美國是要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奧森伯格該備忘錄,告知及提醒布里辛斯基,在有關釣魚台一事上,「日本外交部小心地試探我們,以期得到一個更傾向於他們的防衛立場」。但奧森伯格在同一份備忘錄上緊接著表示,美國在釣魚台的立場與利益在於「不做任何損及日本的事,但同時,對此一中日間潛在爭端爭議的領土保持距離。」(Our interest is in doing nothing to undercut the Japanese, but at the same time remaining aloof from this potentially contentious Sino-Japanese territorial issue.) 該份文件中也特別明述,對於日本有關對釣魚台的法理宣示,美國的立場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對」。(neither added to nor subtracted from Japans legal clam to the island.) 這樣看來,只有國家利益才是永恆的。作為國家的外交官或代表必須要了解相關的史實,切不可只為意識型態或黨派利益講話。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釣魚台爭議 謝長廷炮火對內不對外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8001900-260407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日前表示釣魚島適用「日美安保條約」,對釣魚台主權被蠶食鯨吞,未見蔡英文總統和駐日代表謝長廷抗議,引發國民黨批評「兒皇帝」、「孫代表」。謝長廷對此立即回批國民黨辱罵,並稱美國一貫對釣魚台列嶼適用美日安保條約,遭譏駐日外交官忘了自己是誰? 謝長廷為何面對日本立場軟弱,對國民黨批評卻火力十足?據《中評網》報導,去年4月謝長廷接受日媒專訪時已剖白心跡,未來在釣魚台問題上「不會聯中對付日本」。這是民進黨政府的政策,毫不掩飾的親美、媚日。該報導呼籲,安倍與川普見面時可能確認「美日未來將共同武力防衛釣魚島」。蔡英文總統和駐日代表謝長廷面對釣魚島主權爭議別忘了自己是誰。 駐日代表謝長廷「忘了自己是誰」還有一例,去年11月,謝長廷在臉書貼出一張日本超市販賣福島花椰菜的照片,表示自己也吃該地區食品,竟強調日本福島核災食品,若能夠證明無汙染,應該開放進口。當時即被輿論炮轟「謝長廷,您究竟是哪一國的代表?」 (中時電子報)
在日韓國人:燒肉、名字與「異鄉」的微物誌2017/02/08 14:48:26 蔡曉林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271484 在日本的下班時間,經常可以看到各種場合的聚會出現這樣的光景:眾人圍住一個熱騰騰的烤盤,上面散發著濃厚的香味,放上各種新鮮的薄肉片或者內臟,等烤熟了再添加各種調味料如沙茶或者奶油來食用。這種「燒肉」的飲食文化,以日本為首,已經擴散到東亞各國甚至全球,廣受歡迎。而它的源起也反映了一個時代人們因戰爭移動求生存的故事。 自從日本步入明治維新,從思想到吃飯的方式都產生了巨變。為了證實日本已經進入西化時代,明治天皇大力鼓吹人民吃肉食以培養健壯的體格,吃肉也逐漸成為文明的符號。雖然此時,「肉」的定義從今天看來還是侷限了一些,當時的人們還不敢食用動物的內臟,料理時也都會將這部分丟棄。 也就在這個時候,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開始有人前往日本討生活,特別群聚於大阪周邊。根據朝鮮半島文化史專家佐佐木道雄的考察,這時來自朝鮮半島的人們開始將日本人捨棄的內臟等拿來當食材烤肉,形成現代燒烤店的雛形。不過另一位食物史專家宮塚立雄則指出,這種飲食方式其實是戰後食糧短缺才開始廣泛流傳,動物內臟(ホルモン)逐漸為日本人所接受,燒肉開始發揚光大。直到1965年日本與南韓恢復邦交,日本國內取得韓國國籍的人也增加了,日本內部來自南韓與北韓的團體為了該取名為「韓國料理」還是「朝鮮料理」而爭鬧不休,最後乾脆統一稱為「燒肉」。 燒肉隨著日本的經濟起飛而壯大,也與傳統的「韓式料理」分家,近年更進軍世界各國,也「逆輸入」回到韓國。而燒肉文化背後的支撐者,最主要仍然是「在日韓國人」這個曖昧的族群。全日本目前共有近六十萬的人口屬於「在日韓國人」,他們在日本社會是一種特殊的存在,既是戰前歷史的延續,也是全球人口流動下的結果。在日韓國人作為日本社會隱性的「他者」,長期未受重視,他們大多扮演如同在料理店為客人提供美味餐點那樣的幕後角色,以這樣的形式在這個陌生又熟悉的國度生活下去。
所有人都知道 但它不在地圖上 因為它不在地圖上 它不是日本 ——金時鐘,詩人、在日朝鮮人 這首詩的場景座落於關西大阪一個叫作「鶴橋」的地方。乍看之下,這裡與一般日本街景大同小異,不過繼續走下去,眼前突然出現一座高聳的「百濟門」,周圍也多了其他不是日語的招牌,尤其是好幾間韓國燒烤店,便顯得別有一番風味。同樣地,在東京最具代表性的韓國城新大久保,走著走著也會意識到周圍的韓文突然多了起來,周圍的人也說著韓語,甚至其它日語之外的語言。這裡的居民可能是從小生長在日本,日語比韓語更嫻熟的韓裔人士,也可能是近年來日本留學、求職的韓國年輕人註1。 如同金時鐘的詩句所道出的,地圖上找不到韓國城的位置,就好比裡頭的居民隱形般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既不被視為一份子,也不是完全的外人,卻又沒有其他地方能回去。許多住在韓國城或者日本任何一個角落的在日韓國人,都如同張英仁一樣覺得裡外不是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韓國人。 張英仁(化名)出生在日本、韓國之外的第三國,從小在日本長大,是第四代在日韓國人。十二歲的時候,由於韓國國籍對父親升遷不利,根據日本當時的法律,全家人的國籍必須一致,她就在沒有選擇權的狀態下跟著家人將韓國國籍換成日本籍。 儘管對於不會說韓語的她而言,韓國或許是一個更陌生的國家,然而成為「日本人」以後,在日本的生活雖然更為輕鬆,不用為簽證或者入境時填各種表格而煩惱,但她仍覺得與日本社會格格不入,除了學校教育中對於殖民主義的態度,就連她想擁抱像是和歌等傳統日本文化時,都會感到一種強烈的矛盾:這些傳統文化所堆疊塑造的「日本性」,正是將她所屬的「在日」社群排除在外的根源之一。
像張英仁這樣所謂的「在日韓國人」,是日本不被看見的族群,卻普遍存在於各個角落註2。日本與韓國的交流從數千年前即有歷史記載,今天存在於日本的「在日」族群,最早源於二十世紀初。當時的朝鮮人,就像從殖民台灣來到日本的台灣人一樣,赴日多被視為低階勞工,從事建設相關的工作。除此之外也有高階知識份子來日本留學。這些韓國人在日本的生活並不好過,除了領不到跟一般日本人一樣的薪水,還受到許多歧視。1910年「日韓合併」,朝鮮半島正式淪為日本帝國的領土,此後更有成千上萬的韓國人為日本帝國打仗犧牲。 戰爭結束後,許多韓國人並沒有離開日本回到故鄉。當時韓國本土的情勢也不穩定,像是發生了濟州島事件註3,大量平民遭到殺害,1950年代朝鮮半島又爆發韓戰。不少來自南北韓的難民湧入了日本,從此定居,他們的子孫也在日本列島出生,上一般的小學,與普通日本人無異。1952年舊金山條約註4簽署後,日本正式放棄前殖民地的所有權,這些曾經擁有日本國籍身份的韓國人,也自此喪失日本國籍,成為這塊土地上的「外國人」。 戰後初期,在日韓國人由於無法享有公民應得的權利,多數從事餐飲業,如韓式料理、燒烤店等,或者經營柏青哥產業(彈珠機,日語發音讀作:Pa-chin-ko)。即使多數在日族群外表上沒有明顯差異,日文能力也近乎母語程度,但無論在婚姻、就職上,仍隔了一道隱形的牆。不少在日韓國人組成各自的社群,例如公民團體、韓國學校,以保存韓國的文化。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兩個公民團體「民團」與「總聯」分別擁護南韓與北韓,其成員也包括已經歸化為日本國籍的在日韓國人,他們在各種議題上發聲,並且為在日韓國人爭取更多福利。如今,多數的在日韓國人的居住方式與一般日本人沒有什麼不同,儘管重要節慶時仍然注重韓國傳統禮儀,日常生活說日語的比例已經高於韓語,出國時手持的護照可能已經換成紅色的日本護照,當然,也有人仍拿著陌生的祖國韓國的護照。 美國社會學家John Lie指出,50年代在日韓國人從事不被看見的工作,到了60、70年代當日本的經濟正起飛,在日韓國人已經逐漸在日本社會中成為隱形人。第二代的在日韓國人經常不以真身示人,他們隱藏了身份,不「出櫃」自己的民族背景,用著日本名字,說著流利的日文。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人們紛紛朝向大都市移動,生長在大都市的在日韓國人,似乎還比從鄉下地方來的日本人更能適應社會潮流。此時,在日韓國人的文化也逐漸受到重視,好比不少在日作家所寫的文學作品一度蔚為風潮。
時至80、90年代,也有另一批韓國的「新移民」(ニューカマー)前往日本展開新生活。即使背景有別於戰前或者戰後初期的在日群體,這群韓國人也屬於在日韓國人。時代前進,在日韓國人的處境也有好轉的趨勢。不論以本名還是日本名字示人,他們在演藝事業、運動球隊以及商場上,由於表現良好,逐漸受到矚目。例如知名的導演李相日,以及身為日本首富的軟銀社長孫正義即是在日韓國人後代,但即使他以韓文名字示人,早期經商時也有人建議他隱藏身份,以免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如同孫正義與張英仁,不少在日韓國人開始將國籍換成日本,或者改名換成日本名字。曾經,在日韓國人只與彼此通婚,一方面是在成見仍然很深的時代裡,與日本人通婚並不容易。不少家長會在婚前派偵探調查對方底細,除了部落民註5的後代之外,在日韓國人也是一般人不願意通婚的對象。尤其就現實考量,日本女性若與在日韓國男性結婚,在過去的法律下便有喪失日本籍的風險。在日韓國人自身也可能因為身份認同而不鼓勵子女與一般日本人通婚,好比吉田修一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東京灣景》中,便描寫到在日韓國人家長秉持著民族主義,即使在日本事業有成,卻不願意看見子女與日本人結婚。 一位出生在濟州島的在日韓國詩人金水善曾如此寫道: 半個世紀 孩子們成人了 長者逝去了 學生年長了 我仍然看不見阿里郎山坡。 不論持有日本還是韓國護照,或者是否與日本人通婚,身為離散族群的在日韓國人縱使不屬於日本,卻也不屬於「祖國」。許多人表示,他們回到韓國後,發現民族情感仍然難以克服語言與文化的隔閡,那個祖國已經回不去了,他們也無法成為真正的韓國人。於是,他們只能回到異國的家鄉——日本,努力地生存下去。那個傳說中的阿里郎山坡,也只能留在夢中了。 ※本文原標題〈燒肉:離散的深夜食堂〉,節錄自《微物誌:現代日本的15則物語》。
▎備註註1:
城市中的街景與空間政治也反映了日韓複雜的政治與情感關係,90年代末,韓流在日本興起熱潮時,新大久保一度成為最熱鬧的區域之一,其後不時由右翼團體鼓吹的反韓遊行,也選擇以韓國人為主的此地作為示威中心。 註2:「在日」族群若要嚴格定義,又分為來自南韓的「韓國人」與北韓的「朝鮮人」。本文為方便書寫,統一使用「在日韓國人」一詞。 註3:濟舟島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朝鮮半島情勢混亂,人口大量移動,大韓民國政府與人民之間互不信任。1947年3月1日,官民之間產生衝突與死傷,政府開始對人民暴力鎮壓。由於牽涉到共產黨,美軍亦參與其中。一直到1949年間,都持續有平民受害,至今各方提供的傷亡人數都不相同,有人推測高達兩萬人以上受害。 註4:舊金山和平條約:此乃1951年日本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於美國舊金山簽署的條約,處理的議題主要圍繞在日本前殖民地領土的託管,包括承認朝鮮獨立、放棄台灣、澎湖、千島群島、庫頁島南部、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等地之主權,並同意美國將琉球群島等地交由聯合國託管,讓美軍駐紮於沖繩。此和約的前言中,日本亦請求加入聯合國,1956年,聯合國正式接納日本成為會員國。 註5:部落民:日本邊緣的少數群體,儘管被認為與多數日本人同為「大和民族」,但是由於屬於早期封建時代的「賤民」,多從事「不潔」的工作,例如屠夫等,因此即便二戰後日本的新憲法規定人人平等,但社會上對部落民的偏見仍然存在,也有許多團體仍試圖化解這種文化隔閡。
|
|
|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