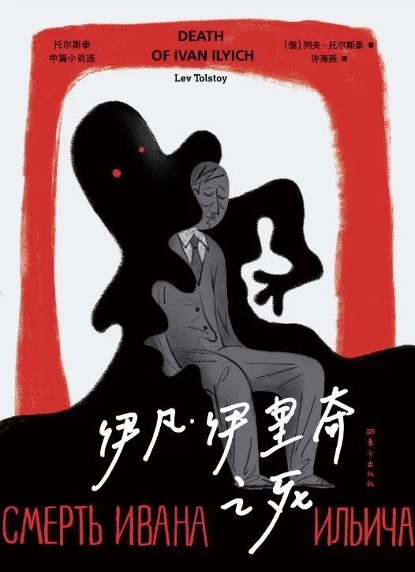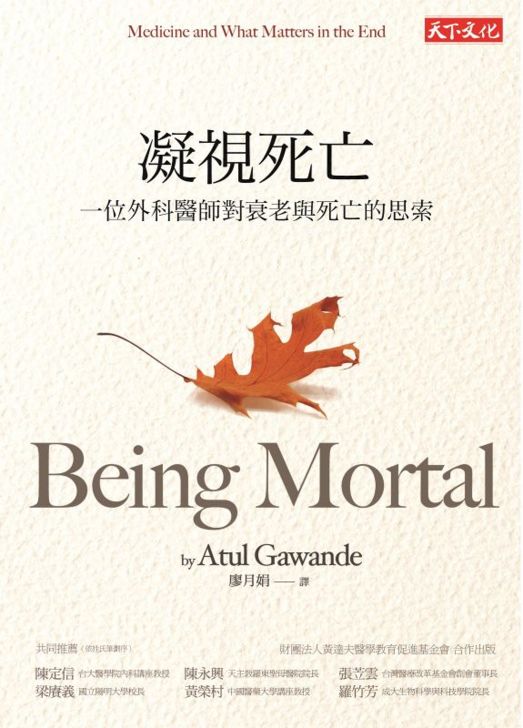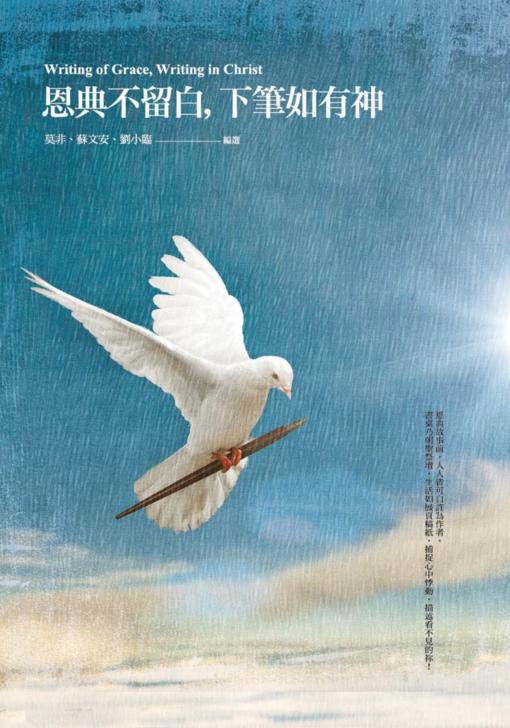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3/03/30 10:21:08瀏覽2620|回應0|推薦3 | |
年邁父母最看重什麼?生活環境的舒適安全?東西好吃?作者通過閱讀和親身照護的經歷,給出了真知灼見。
在哈佛醫學院一場有關病醫關係的研討會上,葛文德與他的同學們花了一個小時討論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伊凡· 伊里奇之死》。小說主人翁伊里奇是19世紀末俄國聖彼德堡的一位45歲法官,罹患了某種不治之症,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伊凡· 伊里奇之死》 當時自信滿滿,即將成為外科醫生的葛文德,絲毫沒有心理準備要去瞭解主人翁心中的孤獨、痛苦與被憐憫的渴望。他認為醫學上的同情心是理所當然的。伊里奇的病情應該可以藉由現代醫學被治好。當時他和同學們關心的只是如何獲取更多的醫學知識與能力,並沒有意識到死亡也是醫學方程式裡的一部分。 進入外科行醫多年之後,葛文德終於了解為何伊凡·伊里奇的故事,必須是醫學訓練裡的一部分。「我從未想過,作為一名醫生,事實上,作為一個人,我所學到最有意義的經驗來自於幫助他人處理醫學上不能解決以及能夠解決的事情。」葛文德在書中寫道。 「醫學這個行業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修補人體的缺損。如果你的問題可以解決,我們自然知道該怎麼做。如果無法解決呢?於是,我們變得茫然、冷漠,而病人只能受苦,覺得活得沒有尊嚴。」 曾經擔任《紐約客》主筆,數次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哈佛醫學院外科醫生、作家葛文德(Atul Gawande),在《凝視死亡》(又譯《最好的告別》) 一書中,透過深情溫暖的筆,娓娓道來一個又一個故事,帶我們凝視、探索衰老與死亡的議題。 作者描述自己擔任外科住院醫師的第一個臨床案例,病患是60歲出頭的公務員拉扎洛夫,因前列腺癌細胞擴散到胸脊,壓迫到脊髓,已無治癒的可能。當時神經外科給出兩個選擇:延後醫療或者切除壓迫到脊髓的腫瘤。 「我站在病房外,拿著病歷,手心冒汗,一直在想,怎麼談這個話題才好?我們希望藉由手術使他的脊椎不再遭到進一步損傷。然而,手術無法使他痊癒,不能使他擺脫癱瘓重新站起,也不能讓他回復原來的生活。」葛文德說,無論醫生再怎麼努力,頂多只能讓病人多活幾個月;但是手術本身風險很高,猶如兩面刃,可能改善病情,但也可能帶來更多併發症,包括全身癱瘓、中風,甚至致命。 「別放棄我,給我活下去的機會吧!」躺在床上的拉扎洛夫提出要求。葛文德醫師寫道,「患者追求的只是一個幻想,卻可能因此踏上一條漫長而痛苦的死亡之路——事實正是如此。」 從技術層面來看,那次手術可說無懈可擊。外科團隊花了八個半小時切除腫瘤,解除了脊椎的壓迫,但是後來在加護病房裡的拉扎洛夫卻出現所有併發症:呼吸衰竭、全身性感染、血栓等問題,讓醫師團隊有節節敗退之感。最後主治醫生在家屬同意下,決定拔掉呼吸管。 寫下《凝視死亡》一書時,距離拉扎洛夫的故事發生已有十多個年頭,回顧當年的決定,葛文德坦承,醫療團隊所有人包括腫瘤科醫師、放射科醫師及外科醫師,都知道病患不可能痊癒,但還是眼睜睜看著他受盡折磨。
《凝視死亡》 「我們不曾使他看清事實的全貌(疾病的現實),沒坦承自己的能力終究有限,更別提跟他討論在接近生命終點時,什麼對他而言是最重要的。如果說他在追逐幻想,我們又何嘗不是......我們沒能面對現實,沒能給他安慰,也沒能引導他,告訴他要怎麼做。我們只是給他一種又一種的治療,騙自己相信,說不定會有奇蹟出現。」 葛文德指出,延遲死亡的現代科技對醫學界仍相對較新,哪些患者面臨長期威脅生命的狀況?哪些真正經歷瀕死?平時習慣教導病人如何養生活出健康的醫生,真的預備好跟病人展開有關死亡的對話與討論了嗎? 閱讀此書之前三個月,父親健康情況急遽衰退,我踏上照護之路,因此對書中有關老年病學的篇章,特別有共鳴。美國醫界有一套老人「獨立自理生活能力」的評估標準,包括獨自上廁所、進食、穿衣、洗澡、整理儀容、下床、移動(不需旁人攙扶,自己從座椅上站起來)以及行走等八項能力。若有人無法獨立完成這八項活動,就被視為缺乏「獨立自理生活」能力,無法獨居。 父親向來注重健康,飲食作息正常,有病看醫生,可說是老當益壯。新冠疫情爆發兩年前,當時93歲的他仍維持每週打2—3次高爾夫球,每天走路半小時的習慣。居家隔離期間,因為我們不准他開車,他的活動力急劇下降。半年前,他在自家附近公園散步時,開始出現走路失去平衡,雙腳無力的現象 我們一直以為父親年紀大了,這是自然老化的跡象之一。但是在一個週末,他突然無法從座位上站起來,大小便失禁,下半身形同癱瘓。失去行動力的他已無法獨立生活,驚慌失措之下,我們短時間內為他找到三班看護輪流照顧,加上我和妹妹,24小時永遠有人守護在旁。 接著他抱怨肚子疼,醫師排除中風的可能性後,建議先使用Tylenol(泰諾,解熱鎮痛藥)觀察一陣子再說。有一天父親腹部急遽疼痛到無法忍受,我們打了911,用救護車將父親送到醫院,這才展開一連串密集檢測,終於查到父親脊椎上有囊腫。MRI(核磁共振)顯示這個囊瘤非癌細胞,但是已經壓迫到中樞神經,而且造成脊椎發炎。醫療團隊建議立刻開刀,「否則父親將終身癱瘓」,外科醫師助理路易智鄭重地告訴我們。 「手術相當複雜,」路易智不諱言,「我們要打開他的脊椎,抽掉底下一小根骨頭,接著在T7、T8、T9(椎體)兩邊各打釘固定脊椎。」當醫師助理在電話上耐心解釋手術的複雜與精細過程時,電話另一頭的我和妹妹,邊靜靜聆聽,邊想像讓一個95歲的老人經歷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如果不動手術,醫師說抗生素已經無法消除囊腫,他一輩子就得癱瘓在床上。手術至少提供一線生機,解除父親中樞神經被擠壓所產生的劇烈疼痛,其他術後復健等就只能靠上帝了。至於大小便失禁問題,醫師沒有把握手術後一定得以恢復功能。 情感上,我和妹妹很理智,不像六年前母親驟病昏迷過世時感受到震驚與無法承受,另一方面也體諒到父親年紀到了,總是會有這麼一天。上帝如果要帶他走,我們預備心接受;可是如今有了開刀的選項,似乎上帝有美意在其中那麼我們為何不繼續仰望上帝的憐憫與恩典,借現代醫療科技與醫生的專業知識,解決父親的問題呢? 脊椎囊腫移除手術比預期短兩個小時。操刀的外科醫師費里步手術後立刻來電告知一切順利,他成功切除那塊囊腫,疏通了原來被擠壓的部分。「沒看過一個九十幾歲的老人骨頭那麼硬,花了我好大力氣才把樁釘鑽進去!」醫師笑著說。 手術後父親在保險公司的安排下,於復健中心展開密集的物理治療與訓練。 那是一所結合復健與養老功能的療養院。當初選中這家,是貪地利之便(離我住處只有十分鐘車程)。網路上的照片使這裡看起來設備新穎,寬敞舒適;沒想到親眼目睹後,深覺受騙上當。父親從採光明亮、乾淨清爽又有專業護士伺候的大醫院病房,被送到一個灰暗老舊又沉悶的住所,猶如從五星級酒店淪落到Motel 6(六號汽車旅館,二星級),父親心情的起伏與不安可想而知。後來打聽得知,大部分聯邦醫療輔助體系下的復健療養院都一樣,沒得選。
「反正來這裡只是暫時復健,很快就會出院!」我們如此安慰父親,也同時激勵他積極復健,才能早日搬離這個讓人沮喪的地方。 但是離開復健中心之後,要搬到哪裡?父親顯然不能再回原來的地方獨立生活,我們必須幫他安頓一個新家,一個舒適、安全又有專人照護的居所。 這時我們首度接觸輔助生活住宅(Assisted Living Facility,以下簡稱ALF)的概念,俗稱「老人公寓」。輔助生活住宅有點像獨立生活與養老院之間的中途站,是老有所終,連續照護的一部分。最早提出ALF構想的是擁有老年學博士學位的凱倫·威爾森,她在1980年代因自己母親的實際需要,在俄勒岡州嘗試建造老人「樂活園區」。威爾森當初的想法是使ALF取代養老院,成為長輩們的終老之處。她認為儘管老人年邁體衰,但也不一定要過得像囚犯一樣,處處受到管制。 在威爾森的理想園區裡,ALF給人一種「家」的感覺:居民(residents)擁有自主權與自由,時間如何分配、空間如何處理、傢俱如何擺放,做決定的人是自己,而非看管照顧的院方。反觀一般養老院裡的生活作息,舉凡睡覺、穿衣、吃飯、活動必須完全按照統一的時程表。基於安全考量,他們也不允許老人把自己的傢俱擺在房間裡,更別提拒絕某些長輩晚餐前喝雞尾酒的習慣。 理想歸理想,現實終究是骨感的。 輔助生活住宅概念說來容易做來難。比如老人穿衣一事,用心、有耐心的看護會讓老人自己穿,她在一旁觀察,以便適時協助。如此老人的自主能力才不致退化,也有獨立生活的感覺。但是看護在同時照顧好幾位長輩的情況下,不可能有充裕時間慢慢等每一個老人自己穿上衣服,或陪他們緩緩踱步到洗手間大小便。對看護而言,當日的工作成效遠比老人的能力與感受更重要。對管理者而言,老人的體重是否減輕、是否按時吃藥、有沒有摔倒,這些具體專案在評分系統裡都比關心他們的心情更為優先。 葛文德在書中提及,威爾森表示ALF是為老人建造,但是老人住哪裡又大多是兒女做決定;業者促銷的對象其實是他們的兒女,並非老人本身。 「環境看起來是否高雅、安全?東西好不好吃?這些都是我們這些做兒女的所看重的,但不一定是父母所想要的!」與我一同走在照護之路,為父親安頓新家的妹妹發出類似的感慨。可想而知,業者為了視覺效果,大廳門口佈置得猶如酒店一般,以吸引參觀者的目光。 記得首度探訪住家附近的ALF那天,正好碰上他們的午餐時間。外頭陽光璀璨,我站在走廊裡,透過餐廳玻璃窗往裡看,想像著坐在輪椅上的父親,被看護推來這裡,現場有爵士鋼琴樂伴奏,老克拉(閱歷深,收入高,消費前衛的都市男性族群) 一邊品嘗平日喜愛的卡布奇諾、拿鐵,一邊和同桌的美國退伍老兵交換他的越南故事。以父親樂觀開朗喜歡社交的個性,加上他流利的語文能力,應該很適合ALF的生活模式,可以在這裡交到好朋友。 這會是他未來的第二個家嗎? 「老有所終,不只是醫療問題而已。」葛文德在書中寫道。關於老人和病人的照護,醫療與安養機構的問題並非源於他們對生命的觀點有誤,而在於不知如何重視生命。醫學專業人士只關注對身體健康的修補,而不管靈魂的需求,這是令人痛苦的吊詭之處。
葛文德引用1908年哈佛心理學家羅伊斯(Josiah Royce)的《忠義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這一著作,想了解為何人單單活著(有地方住、有東西吃、安全無虞)不夠,我們還需要一些別的什麼,才會覺得人生沒有白活? 他得到的答案是,我們不能僅為自己而活。他說我們內在皆有為他人而活的需求,大者如為了家庭、國家,小者如為了實現某項計劃或照顧寵物。猶如馬斯洛人類需求金字塔頂端的自我實現,人人都有「超越」的意念,只有發揮一己的潛能,助他人一臂之力,我們才會覺得有價值。 兩個月前,我們為父親在ALF老人公寓安頓了新家。一個studio(單間公寓)形式的房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寬敞的廁所(方便輪椅進出)、衣櫃和小陽台。對目前行動受限的父親來說,這樣的空間已經足夠,加上輪班看護和護士的照料,讓我們很放心。這所私人ALF公寓設備齊全,從圖書館、健身房、游泳池、交誼廳到美容院,宛如一個度假酒店。我們希望前半生流離動蕩的父親,晚年能夠安舒,享受人生最後一裡路的風景。 「這是教會查經班的Zoom連結資訊,麻煩你每週四早上10點鐘幫他在iPad上設定,讓他進入查經班。」我在傳給父親看護的簡訊上這樣寫著。看起來20來歲剛畢業模樣的莫尼卡其實已是三個大孩子的媽,她對父親有著無比的耐心,總是稱他Papa。 五分鐘後,手機傳來莫尼卡拍攝父親在Zoom裡跟查經班打招呼的視頻,畫面上躺在床上的他看到久違的弟兄姊妹,開心得合不攏嘴。 「Papa好興奮!」莫尼卡在簡訊上說。 「牧師說每次在銀幕上看到你,對弟兄妹妹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喔!」我們告訴父親。時間概念已經模糊的他,綻開笑顏,說好好好,只要有人幫忙,一定準時參加線上團契、查經班、禱告會與主日崇拜。老人家真心期待有一天能夠再度回到教會裡做禮拜,和大家握手問安。 父親手術至今兩個多月,仍無法站立行走。兩條腿肌肉無力,且大腿以下經常感到麻木。物理復健師能做的有限,我們盡可能每次探望他時為他按摩,幫時血液迴圈流通。有時候忘了自己下半身癱瘓,他會囑咐我們把家裡的拐杖拿來,「等我好一點,一起去吃『上海灘』!」 身體受限於一張床與輪椅的他,還是感恩,知道自己的存活全操在永恆主的手中。日日皆好日,每天都是感恩節。早晨醒來,他會默默背誦詩篇23篇與主禱文;週三和兩位弟兄電話禱告,週四早上參加查經班;週五晚有團契。他祈願自己長年栽於溪水旁,年老的時候仍結果子,滿了汁漿而長青。 葛文德在《凝視死亡》中分享自己同樣是外科醫生的父親最後因罹癌而失去身體自主能力的故事。他和父親展開行醫生涯中最艱難的對話,描述家人在絕症,身體走下坡的殘酷事實面前,內心的悲傷與恐懼。葛文德家中有三個醫師,醫療經驗加起來有120年的他們,卻對父親每下愈況的身體感到萬般無助。 在探討生存的最終目標並非好死,而是好好活到最後一章時,作者得到一個清楚的結論:「我們對老人、病人的照顧做得不好,是因為我們誤以為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安全和活得久一點。」葛文德說,如果要延續有意義的人生,必須把握機會,塑造自己的餘生。「我們還有機會重新打造適合老人居住的機構,改變我們的文化,用不同方式來對話,使每一個人的生命之書最後一章,都能變得精彩。」
人生最後一哩路上,何時進行合理的醫療干預,何時尊重生命的週期性,或許是我們和父母長輩們應該認真討論的重要人生課題。 文中主題書籍: 《凝視死亡:一位外科醫師對衰老與死亡的思索》,天下文化,2015年9月出版。又譯為《最好的告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END- 作者簡介 語聆 創文公關同工,前新聞主播/記者。目前為《真愛家庭》雜誌、《神國》雜誌採訪及撰寫文章。 圖書推薦
《恩典不留白,下筆如有神》 -莫非 蘇文安 劉小臨著- 恩典故事前, 人人皆可 自許為作者, 書桌乃朝聖祭壇, 生活如展頁稿紙, 捕捉心中悸動, 描述看不見的你! 購買資訊: 台灣:橄欖華宣 https://www.cclm.com.tw/book/19314 北美:gcwmi622@gmail.com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