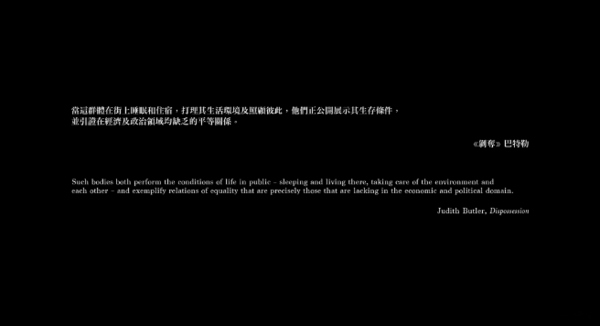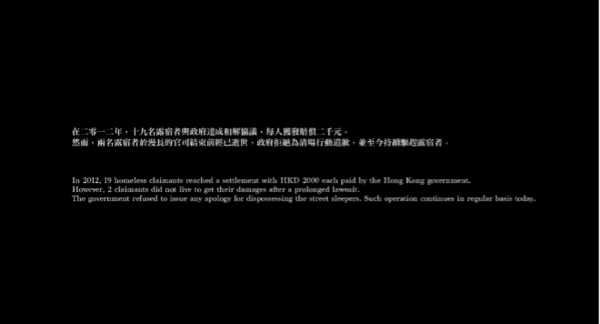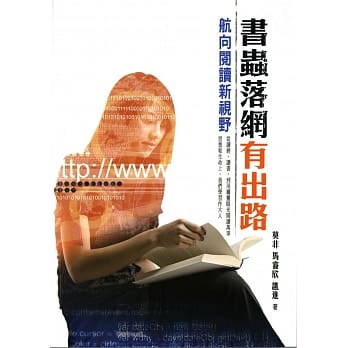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2/11/28 10:11:54瀏覽1406|回應0|推薦3 | |
電影觸發了作者的深思:「面對最微小不堪的人,我們是跟做禮拜時一樣看他人的後腦勺,還是與之面對面?」也許這是我們都該思考的問題。
作為今年金像獎11項提名以及2021年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電影,《濁水漂流》故事的吸引力在於,這是一部講述社會底層被邊緣化的片子。片中,吳鎮宇、謝君豪、李麗珍、葉童等眾港星一改光鮮亮麗的形象,變成了香港深水埗最貧窮、最落魄的露宿者。 《濁水漂流》講述了香港深水埗天橋底下聚居的露宿者,如何在狹縫中生存的故事。電影改編自2012年深水埗通州街清場事件。2012年2月15日,食環署在無事先告知的情況下,會同警方清理街道,將在通州街與界限街交界露宿的數十名露宿者的家當,像垃圾一樣扔進了垃圾車。 露宿者在社工的説明下打官司,他們想要得到賠償,更想要得到道歉。當年通州街事件後,導演李駿碩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學生記者的身份,前往採訪,因而認識了這群無家可歸的人,隨後將此事件拍成電影,搬上大銀幕。 露宿者是垃圾,還是人? 片頭字幕引用裘蒂斯·巴特勒《剝奪》一書中的話:「當這個群體在街上睡眠和住宿,打理其生活環境及照顧彼此時,他們正公開展示其生存條件,並引證在經濟及政治領域均缺乏的平等關係。」然而,這群無家可歸者的聲音卻被當權者忽視。
片中,吳鎮宇飾演的輝哥作為露宿者,遊蕩在深水埗,是香港最底層的人。監獄工作人員告訴出獄的阿輝不要再進監獄了。他想擺脫令人窒息的環境,但卻無奈地說,外面只是一個更大的監獄罷了。在香港這個節奏飛快、由混凝土構築起來的城市裡,一幢幢建築拔地而起,漸漸把他們擠出原本屬於自己的狹小天地。 政府的清理車拉走了露宿者們的家當,扼殺了他們生活的最後一絲希望。阿輝憤憤不平地說,丟我的東西還說是垃圾,我們是垃圾,可能把我們也扔掉。 阿輝對世界的恐嚇早已習以為常,他決定不再退縮,迎難而上。為了打贏官司,阿輝決心戒毒。阿輝在政府門前抗議的時候,對著前來的記者表示,我們露宿者希望政府能夠公正地賠償我們和公開道歉:「露宿無罪。」 結果,政府願意賠償,但是不會道歉。阿輝怒火難消,在公開道歉的問題上,不肯妥協;其他露宿者也因他的堅持,不歡而散。對輝哥這個角色,導演這樣說:「其實他沒有什麼可以輸了,因為他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他對於人的最基本尊嚴很在乎。」
影片中,當露宿者的困境被媒體報導後,許多人前來探問。有扛攝影機的記者,有來幫他們義剪的髮型師,有來做社會調查的大學生,還有來體驗生活的大學迎新營。 李駿碩導演將這場戲處理得輕鬆幽默,背景音樂甚至有些輕快,彷彿是一種刻意的嘲諷。憐憫、同情與幫助,似乎成了廉價的施捨。而這樣的同情與憐憫,通常來得快去得也快。當新聞熱度散去,高架橋下的露宿者們,又恢復了他們無人問津的苦悶生活。 輝哥常說一句話:「深水埗是窮人住的地方!」這座城市對他們的需求,看不到,聽不見。偶爾有人路過看見,扔下一枚硬幣就走。 導演說:「以前在深水埗上學,每天經過通州街橋底,直行直過不以為然。直到露宿者被驅逐事件上了新聞,才令我走到他們面前,聽他們的故事。然後每次回去,都面目全非。藩籬越建越高,社會越來越冷。」 誰來關心窮人 據瞭解,1975年,香港成立安置收容越南難民的營地,直到2000年6月1日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香港一共接收了近20萬民眾。影片中也出現不少來自異鄉的角色,如謝君豪飾演的老爺便是來自越南的難民。 看著深水埗建起來的高樓,阿輝感慨萬千,深水埗本來是窮人住的地方,如今在這裡造這些昂貴的公寓,窮人能住在哪裡?這是他必須每天面對的現實,無奈的現實也逼著他不得不做出選擇。 香港著名小說家劉以鬯在小說《蟑螂》裡寫到香港生存現狀時說,香港就是這樣一個「不均」的地方。「有」的人有得太多,「無」的人非凍斃街頭不可。 阿輝厭惡了如同一潭死水的生活,但是離開濁水談何容易。阿輝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危險,活著的希望也很渺茫。覺得死也要有尊嚴的阿輝,最後因為政府不肯道歉,而拒絕政府的賠償。 電影的最後一個場景不僅令人感歎,也使人觸動,在我腦海深深定格。阿輝在一把火中喪失了生命。燃燒起來的火焰沿著橋下的橋墩向上突躥,橋下車道上的車輛呼嘯而過,彷彿看不到一個生命的離開。 更諷刺的是,輝哥其實知道,即便自己死了,也換不回什麼。他早在之前記者採訪時說過:憤怒本身毫無價值,無人圍觀。憤怒燃燒殆盡後的悲劇,才是供人咀嚼的養料。憤怒沒有任何意義,或許死亡會有些意義,以此喚醒人們沉睡的心。 就如輝哥所說,他是生活在監獄籠子裡的人,籠子外的人難以體會他所受的對待。他不想放棄這塊窮人生存的僅有之地;如果他放棄了,這裡的情況也許不會有任何改變。妥協就意味著不公者的勝利。人一旦有了心中嚮往之地,他就會堅持下去。
《濁水漂流》借露宿者事件,重新喚起社會對邊緣一角的關心重視,也牽繫起近年來香港人所爭取的公義與心中憤慨,輝哥說:「沒有人關心我們真正的需求,只關心我們在這裡睡了多久?為什麼流落街頭?為什麼坐牢?為什麼吸毒?我只要求政府賠償我們的損失,要求政府跟我們道歉。」至今,這一句道歉遲遲未來。 這些年他們的生存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電影只留下黑屏裡的一串字幕:2012年,19名露宿者與政府達成和解協定,每人獲發賠償兩千元。然而,兩名露宿者於漫長的官司結束前已經逝世,政府拒絕為清場行為道歉,並至今持續驅趕露宿者。
當希望變得渺茫時,電影中還閃爍著一絲微光。值得關注的是,電影中出現了「北河同行」為露宿者免費派飯的一幕。「北河同行」是一間開在深水埗的茶餐廳。它以關愛社會基層為宗旨,為街坊提供物美價廉的食物,也會定期在區內免費派飯。 「北河同行」的老闆陳灼明曾坦言:「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在派飯行動中,也從基督徒身上學習到『以愛和寬恕對待人』的精神。未來希望可以學習更多,令我們的活動辦得更好!」由此可以看到,基督徒群體對露宿者群體的影響。 與窮人做鄰居 片中也能看到一些信仰元素。阿輝的小屋門上貼著喜傳佳音。寶珮如飾演的蘭姑住進公屋後,用餐時會謝飯禱告。 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耶穌願意與窮人做鄰居,他與稅吏共進晚餐,與妓女交談,提醒他們自身的價值;由此,教會也一直對邊緣群體有負擔。而許多人一生都在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耶穌所服事的人。 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喜樂容易,但哀哭難。因為這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但事實上,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就要懷疑自己是否真像耶穌那樣活在愛的誡命中了。 作家傑弗遜.貝斯克(Jefferson Bethke)曾寫到:在我們做禮拜的時候,總是看會眾的後腦勺兒,而不是看他們的臉,這樣的情形不會對我們造成威脅;但在餐桌上或者當我們面對面的時候,我們會看著他們的眼睛、他們的表情,這些常常會讓我們感到良心不安,從而迫使我們選擇行動。作為教會,我們應該在他人需要的時候,更多地面對彼此。當我們沒有轉移視線選擇走開,而是願意看到彼此的現實需要時,我們就可以成為那位良善的好撒瑪利亞人。
我的鄰居是一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雖然她不常關心國家大事,但是身邊的小事,她都看在眼裡,放在心上。她看見誰家缺衣少食,就會時常把自家種的新鮮蔬果送給人家一些。冬天她也會提著儲藏的大白菜送人。村裡遇到災年,她一定積極募捐,帶著教會一起回應。 在困難的時候堅持下去,是向我們的鄰居展示一種持久的愛,這表明我們不僅僅關注自己的需要;相反,我們的鄰居和他們的需要比我們的舒適更重要。 《濁水漂流》,不只是香港的《濁水漂流》,也是世界上每一處艱難生存、為生存抗爭人群的《濁水漂流》。基督徒可以成為給被污染的濁水帶來凈化的凈化器。愛的活水,如同一股細流,可以漸漸地讓濁水變為清澈的水,讓魚兒不再掙扎窒息。 -END- 作者簡介 劉嘉 曾為老師,多年前深受《在永世裡拋擲一個身影》一書的影響,開始思考講台與書桌的服事。目前委身教會牧養和文字服事。 圖書推薦
《書蟲落網有出路》 莫非、馬睿欣、譙進 著 從讀經、讀書 到用屬靈眼光 閱讀萬事。 本書探討 現代基督徒 如何透過閱讀, 在思想和生命上, 學習做大人。 購買資訊: 台灣:道聲出版 https://www.taosheng.com.tw/search?q=%E6%9B%B8%E8%9F%B2 北美:gcwmi622@gmail.com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