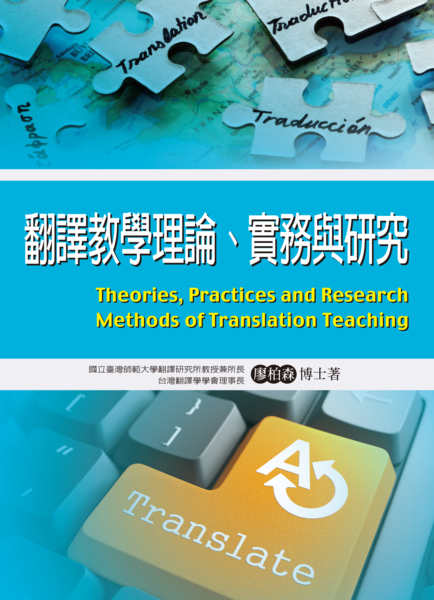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5/01/05 11:21:03瀏覽1477|回應0|推薦8 | |
|
人文學者研究翻譯常是以人文思維來立論,鮮少以量化客觀的證據來進行分析推論,這其實是相當可惜的事,畢竟科學量性研究方法亦有其長處,也能提升人文學科的研究品質,但往往被忽略或輕視。此舉一例如《重寫翻譯史》(2005:22)一書中曾論及「翻」和「譯」兩字在中國歷代典籍文獻出現的頻率,其原文如下: 唐代慧立所寫的玄奘傳記,明顯地出現“翻”字次數比“譯”字次數為多的情況,這種情況,玄奘本人所寫的表奏也可以為證:“去月日奉敕,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者在後翻……已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引文中玄奘用了一連串的“翻”字,充分說明“翻”字用做翻譯解,在唐代已完全確立,而用來專指佛經翻譯,起碼在玄奘及其弟子時更比“譯”字通行。到了宋代,“翻”和“譯”兩個字在佛學圈子的使用率似乎又有改變,“譯”字在比例上再次佔上風,出現了唐代用“翻”而宋代用“譯”的例子: 唐:﹝太宗﹞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珈》。…… 遂下敕:“新翻經綸寫九本……” 宋:“……比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彌勒《瑜珈師地論》……”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
這幾段話要論證「中國唐代多用翻字,宋代多用譯字」的歷史現象,但提出的證據只有引述少數個別案例,如慧立、玄奘等人所著述的文字。此種以少數案例證成普遍事實的論證方式在人文學科中頗為常見[1]。例如在譯本研究上常見的方法就是以幾個譯例證明該譯本是直譯或意譯、異化或歸化等風格,有時甚至是先有普遍結論再尋找個別例證支持。但如此的命題推論方式在效度上是不足的,如以上引文,讀者可以詰問是否為玄奘個人的書寫風格?其喜用「翻」字如何而能推論至近300年整個唐代都多用「翻」字?而宋代多用「譯」字的證明也只一例,顯然也過於薄弱。筆者也可另引宋代贊寧所著《高僧傳》中對翻譯的論述:「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贊寧使用就是「翻」字,而非「譯」字,這又要如何自圓其說呢?
從實徵量性研究的角度來看,在上述引文中「出現“翻”字次數比“譯”字次數為多」、「“譯”字在比例上再次佔上風」等句時,我們就可質問其中提到量性字眼如「次數」和「比例」的數據是多少?更嚴謹的研究者可能還會進一步追問在唐宋兩代中,目前可考的佛經翻譯相關論述典籍有多少?以其為母群體所抽取的樣本如慧立、玄奘的特定文本為何具有代表性?是否經過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或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所抽取的代表性文本中使用「翻」字和「譯」字各出現多少次數?兩字數量的差距有多少?用卡方統計法檢定(chi-square test)後是否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significant difference)?經檢視過這麼多分析步驟後,最後才可得出「中國唐代多用翻字,宋代多用譯字」的有效結論,而不只是作者個人主觀對有限文獻的直觀感受而已。在過去古典經籍取得不易,或許引用古人說過的幾句話就可作為反映當時社會語言特徵的證據,但是目前的電子資料和語料庫工具相當發達,已經可以大量提升蒐集檢索典籍中特定詞彙出現頻率的效能,對於「翻」字和「譯」字在各個朝代使用的次數應該可用更科學客觀的方式來研究和呈現。換句話說,實徵性研究採取的是科學思維與實證方法,而概念性研究則常使用人文思維與論證方法,雙方各有所長、亦有所短,應該相互借鏡,共同發展。 [1]如《古史辨》中梁啟超就常以隻字片語來考訂著作的年代,或以幾個字句有疑義就推斷全書是偽作等,都有以偏蓋全之嫌,許多學者都認為不可靠。
出處來源: http://www.crane.com.tw/ec99/crane/GoodsDescr.asp?category_id=35&parent_id=6&prod_id=0080645
|
|
| ( 知識學習|語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