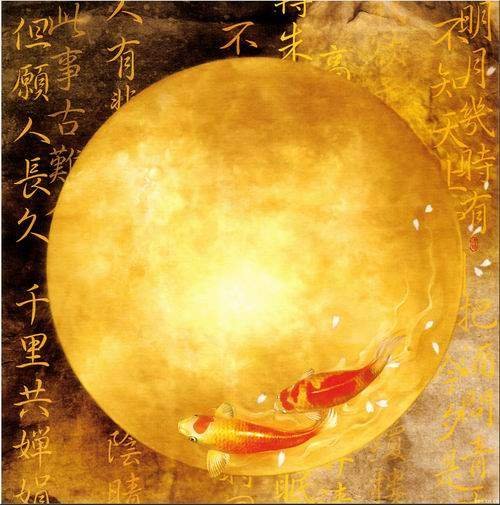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11/04 09:14:14瀏覽2424|回應6|推薦126 | |
第六十五章 《紅絲線》 華霜在客房中左等右等,始終不見東方域歸來,心知有異,連忙步出客堂,逢人便問起東方域的下落。好在東方域俊美非凡,吐屬俊雅,在這荒城中極是醒目,不一會便得知寧熹和東方域不久前曾經在暗巷中拚鬥,情急之下,也顧不得玉體欠安,推知二人定是行往崑崙山,但見路南一間酒肆外的木樁上繫著兩匹坐騎,立即飛奔上前,揮劍割斷了坐騎繫繩,往城門的方向去了。 出了金城,按轡疾行一陣,唯見一望無際的青翠草原上聚集著成千上百的綿羊,不少牧童揮著桿子催趕羊群,朔風呼嘯,寒意凜冽,不由得感到一陣悵惘蒼涼。她放眼望向暮靄中蒼茫遼闊的天地,心中陡然晃過一首古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正是曹操的名作《短歌行》,全詩跌宕蒼涼,筆墨酣暢,辭意平實卻深藏幽怨,氣度恢宏而不失赤子之心。 放蹄快行一陣,前方便是青海湖了,這時已是傍晚時分,一勾冷月緩緩從碧藍的湖面升了上來,高原入夜後倍覺陰冷,她衣衫單薄,寒氣絲絲襲體,懷孕後容易倦怠,但東方域危難當頭,這時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其實他的心思再明顯不過了,他之所以甘冒奇險,長日伴著這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好挨機刺殺,十九是怕她找華霜的麻煩。寧熹見他毫無逃脫之意,於是鬆開他穴道,路上覓了匹野馬讓他騎乘。不出一日,便繞過青海湖,往西南方向馳去。這日晚間來到星宿海,寧熹忽地勒馬止步,向北首一個隆起的土丘而去。 這星宿海藏語叫作「錯岔」,意思是花海子。這裡是個狹長的盆地,密佈著上百個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湖泊,登高遠眺,這些湖泊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宛如夜空中閃爍的星辰,因此便得到星宿海之名。清乾隆初年編修的《西寧府新志》有這樣的記載:「星宿海形如葫蘆,腹東口西,南北匯水汪洋,西北亂泉星列,合為一體,狀如石榴迸子。每月既望之夕,天開雲淨,月上東山,光浮水面,就岸觀之,大海汪洋湧出一輪冰鏡,億萬千百明泉掩映,又似大珠小珠落玉盤。少焉,風起波回,銀絲散渙,眩目驚心,真塞外奇觀也。」 東方域自幼生在西域,這般世間罕見的美景自是司空見慣,但見寧熹緩步走到土丘前,於是也跟著下馬過去一張,那土丘原來是座土墳,墳前墓碑上刻著「羅剎教金長老鐵心英雄埋骨之塚」十四個大字。 寧熹背對著東方域,東方域見她背脊微微聳動,似乎正在哭泣,心想:「這女子雖然無惡不作,但她一生守寡,舉目無親,處境其實很可憐。」忽覺自己的惻隱心實是莫名其妙,此時性命全在她掌握中,居然還有心思去同情她。轉念又想:「我此時發一招『天馬行空』,十拿九穩可以刺他一個透明窟窿,但若一擊不中,那可誤了大事。」悄悄按著刀柄,一時拿不定主意。 忽聽寧熹一聲低嘯,他心頭打了個突,下意識的向後躍退,只見寧熹面目猙獰,雙手捉住長鞭,臂膀齊張,做出發難之勢。 東方域單刀拔了出來,喝道:「幹什麼?」 寧熹陰惻惻的道:「除了我那當家的,你是世間第一個瞧見我哭的男子,若不把你一雙招子挖出來,怎麼對得住先夫?」 東方域道:「妳這女子當真不可理喻。」 寧熹道:「廢話少說,你是要自己動手挖呢,還是讓我來代勞?」 東方域一步步向後退走,道:「妳不是想拿我交換情兒?一個殘廢的東方域,能換一個完好無缺的情兒麼?」 寧熹道:「你崑崙派敢動情兒一根寒毛,我寧熹勢必將崑崙山履為平地。」 東方域道:「情兒跟妳毫無瓜葛,妳幹麼處心積慮的想要幫她?」 寧熹冷冷的道:「天下間焉有一個母親置兒女生死於不顧?」 東方域「啊」的一聲,道:「妳說什麼?情兒是妳女兒?她……她不是伊鳳的私生女麼?」 寧熹大怒,道:「你說情兒是私生女,豈非當眾辱我?」 東方域道:「是情兒自己說的,她說自己是伊教主私生女,教中人士個個瞧她不起,她才會到崑崙山臥底,好在教中揚眉吐氣。」 寧熹沉吟道:「她這麼說,無非是想博取同情罷了,又說什麼自己是伊教主的私生女。嘿嘿,伊教主三個字就像一張護身符,果然誰也不敢對她無禮。妙極,妙極,這女孩兒果然遺傳到鐵哥的聰明。唉,鐵哥,鐵哥。咱們的女兒正身陷虎穴,你在天有靈,一定要保佑我母女團圓。」她說到最後,眉心罩著一抹以往難以得見的溫柔,突然臉色陡變,喝道:「還不挖了招子?」 東方域見她正一步步迎面逼近,情急之下,突然腳下微陷,似乎踩中什麼軟物,低頭一看,竟是踩中一灘沼澤旁的污泥,污泥濕黏異常,猶如一團樹脂漿糊。 他曾經將一根樹枝扔入沼澤中,樹枝初時浮在澤面上,不多時便漸漸陷落,下沉之勢雖甚緩慢,卻絕不滯留,兩旁淤泥掩上,樹枝立時消失無蹤。樹枝份量之輕,尚且如此,常人深陷之後,必難自拔,然而沼澤旁的污泥已黏膩萬分,幸喜並非陷在沼澤之中,否則勢將遭淤泥滅頂。這其時星月黯淡,沼澤淤泥於晚間竟是難以察覺,他突然靈光一閃,道:「慢著。」 寧熹道:「幹什麼?」 東方域道:「妳是鐵了心要挖我眼珠子了?」 寧熹揚眉道:「不錯,誰教你生了這雙眼睛瞟啊瞟的讓人討厭。」 東方域微微苦笑,道:「我少了這對眼珠子,還做什麼人?不如一刀給自己一個痛快,省得成了殘廢,苟延殘喘的活在世上。」說罷,白光一閃,已挺刀往胸口插落。 寧熹「哎喲」一聲,搶前兩步,突然轉念一想:「怕是突施詭計,故意引我上鉤。」但半截單刀已沒入東方域胸口,東方域悶聲不吭,立時倒地。這時哪還有半絲懷疑?此人死了對自己無甚痛癢,但情兒可就糟了,若說回頭再尋華霜,朗朗乾坤,卻上哪兒尋去?心想這一刀若非正中心臟,或許有救,當即飛奔上前,去查看他傷勢。 她挨至東方域腳邊,俯身翻過東方域身子,猛見他胸口雖插著單刀,卻無血漬,心頭一凜,東方域突然左手一翻,立時搭住她肩膀,同時右手托住她手臂,施展崑崙派擒拿手法,一勾一拉,登時將她托倒在地。她哪知東方域自殺是假,那一刀正中懷中的藥包上,當時寧熹距他不過數寸,東方域突施暗算,的是防不勝防。寧熹一驚之際,已被他雙臂牢牢抱住,東方域潛運內勁,雙臂猶如鐵箍,讓寧熹短時間內無法逃脫。 寧熹驚怒交迸,危急中立時便要向他發射火焰箭,但自己和東方域肌膚相貼,這一來豈非連自己也全身著火?東方域抱著寧熹一記「懶驢打滾」,滾了十尺,將至沼澤邊時,突然左足勾住草石,雙臂環抱之力倏地改為橫推,這一發力勢在必得,本擬將寧熹推入沼澤中。不料寧熹情急之下,分寸盡失,一陣死命掙扎,竟牢牢抱住東方域身子,二人身子不由自主的滑了一尺,突然噗的一聲,墜入了沼澤中,大片淤泥淹將過來,登時蓋過二人頭頂。 有好一瞬間,東方域一顆心似乎已飛到了九霄雲外,腦海一片渾然,什麼也想不到,無論是華霜、崑崙派,還是人世間的種種悲歡離合、禍福憂患,於己都已是雲淡風輕了。 二人雙雙沒入沼澤中,那沼澤深不可測,二人身不由主的沉落澤底,就連屍體也浮不起來…… 人人有生必有死,生固欣然,死亦天命,一代使刀高手、一代武學奇才、崑崙派的精英門徒、當世武林第一美男子,都隨著他軀體的沉沒而灰飛煙滅…… 東方域就此從人間蒸發,華霜尋訪他很多很多年,東方域一直都沒回來。等待的日子,其實是很苦的,永無止境的等待,更是一種漫長的折磨。許多年後的一個夜晚,她夢見了他,他在夢裡向他微笑,他熟悉的臉龐充滿了無限的溫柔和關愛,眸心卻有一絲淡淡的哀愁…… 他夢中那抹淡淡的哀愁,往後便深深烙印在華霜腦海,她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了,不只眼前一片黑暗,就連內心也是一片片黑暗。在她內心深處,始終相信東方域尚在人間,只要不見他遺體,那麼她就不會輕言放棄,偶爾思念過度,裹著被褥無聲飲泣,在別人面前卻又故作輕鬆,好似不將內心的痛當作一回事。 忽忽冬去春來,崑崙山上的白雪都已消融了,江南的桃花爭香吐豔,處處生機盎然,不知又是幾個月倏忽飛逝了。她的心一天冷過一天,腰圍也一天粗過一天,到了這步田地,她再也流不出淚來,只覺得內心一片空白,什麼都不必想,也是什麼也想不到,眼前固然奼紫嫣紅,縈青繚白,但映入她眼中,卻跟天黑沒什麼分別;只要那人一日不歸,這個世界再怎麼花團錦簇,卻一如她內心這般死寂與荒蕪。 某日她從漫漫長夜中甦醒過來,但見一抹金黃色的陽光從遠處墨綠色的山巒透了出來,枝梢鳥囀聲聲悅耳,林間松鼠爭逐嬉戲,突然她有所醒悟,東方域的離去,並沒有帶走她的世界,天空依舊那麼遼闊,白雲依舊那麼瀟灑,那就不該絕望,腹中的孩子是她唯一的心靈寄宿,也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依賴。這個孩子象徵東方域和華霜彼此的希望,使她終於清楚自己往後的路該如何走下去,從現在開始,她再也不為東方域掉一滴淚水,她要將所有沈痛與悲憫都化為最深最深的母愛,全心全意關照腹中的孩子,直到東方域回到她身邊,她才能盡情的痛哭一場,並且十分驕傲的告訴他: 「域哥,我沒有為你感到絕望,就算沒有你,我一個人也能堅強的活下去,我們的孩子,象徵我們至死不渝的愛。在行走江湖的日子中,有個人告訴我,只要兩個人真心相愛,他們之間就會有條紅絲線,無論相隔多遠、多久,那條紅絲線還是會將兩人繫在一起。現在,我終於找到你了,我可以靠在你肩上,痛痛快快哭一場麼?」 午夜夢魂縈繞,她枕邊不再殘留淚水,一覺醒來也不再空虛無助,一切都似乎東方域不曾離去,等待的日子,其實也可以用平常心面對,因為她等著東方域一個可以讓她哭泣的肩膀,也只有這個肩膀,才能讓她感到溫暖可靠。 一日華霜在藏邊雪地中隻身漫遊,忽然腹痛如絞,勢將難產,她痛得滾倒在雪地上,只道自己和孩子都要臥雪而死,不由得萬念俱灰。突然一陣大霧在毫無預警之下瀰漫過來,華霜竟隨著大霧從雪地中消逝不見了,沒有人知道她身在何方,也沒有人知道她腹中孩子的命運會是如何……
消息方傳開,各派泰斗便在洛陽設宴商酌,最後組成聯盟,擇定臘八節那日大舉攻入魔教老巢玄冰島,接著並順利摧毀了島上堡壘,俘虜不少昔日曾經為禍武林卻在島上藏匿的奸邪惡人,並將島上所藏的寶物和武林秘譜搜刮出來。至此羅剎教才算是真正灰飛煙滅,要想東山再起,卻是力有未逮了。 墨貍傷勢痊可之後,便同林萍珊快騎趕回揚州和凌逍遙二人會合。一入杏子林中,尚不見凌逍遙和鏡兒出門相迎,一個紅衣女子卻聞聲從柴扉後走了出來,和墨貍一朝相,都是「噫」的一聲驚呼。墨貍驚喜交集,戟指道:「妳……妳怎麼會在這兒?」 那女子尚未答腔,林萍珊搶著問道:「誰啊?」 墨貍道:「是……是燕姑娘啊!」 林萍珊一時想不起來,愕然道:「哪個燕姑娘?」隔了半晌,才恍然大悟,「啊」的一聲,道:「燕飄絮。」那紅衣女子,正是燕飄絮。 這時凌逍遙和冰鏡在屋內聽得人聲,相偕出來一張,但見燕飄絮、墨貍怔怔的凝視著彼此,嘴唇動了幾動,似有千言萬語便欲傾訴,一時卻不知該從何說起。 林萍珊是小心眼兒,燕飄絮突如其來出現在墨貍面前,更讓她心意惴惴,道:「燕姊姊,妳不在江陵縣作妳的金枝玉葉,卻千里迢迢跑來這兒幹麼?」她目不視物,殊不知燕飄絮此刻荊釵布裙,風姿愁悴,面目已非,似乎飽經深憂大患,歷經人事滄桑。 墨貍聽出她言語間蘊蓄著濃濃的火藥味和醋酸味,竟將燕飄絮當成敵人,忍不住道:「小朱兒,妳少說一句,成不成?」他心神失常之餘,口氣自也好不到哪去了。 林萍珊揚眉發慎,左足微跺,噘嘴道:「鏡兒,小……咱們到裡邊去,不要理他們啦。」冰鏡知她失明後極不方便,於是主動過來相攜。 林萍珊本想叫凌逍遙一道入內,但轉念一想,墨貍和青梅竹馬的伴侶燕飄絮獨處在外,雖說光天白日,也不須如何掛慮,但林萍珊對墨貍存著患得患失之情,要他和別的女子單獨敘舊,自己便滿腹不是滋味,是以便讓小七待在外邊,目地便是代替自己監視二人。 不料凌逍遙卻道:「小貍子,燕姑娘,你們故人重逢,定要細敘契闊,互聲舊故遭際,我便不來打攪你們了。」轉身便要進屋。 林萍珊哎喲一聲,急道:「慢著。」 凌逍遙頭也不回,道:「怎麼?」 林萍珊道:「我忽然不想進去啦,嗯,今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鏡兒,咱們到處走走,好不好?」雖這麼說,卻沒有移步之意。 凌逍遙見外頭沒己之事,一眼也不多瞧,逕自舉步入內。冰鏡向他背影望了一眼,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林萍珊只覺氣氛尷尬,故意道:「鏡兒,妳幹麼嘆氣?」 冰鏡隨口道:「沒什麼。」 墨貍對林萍珊性子瞭若指掌,知道她心中所思,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道:「飄絮,咱們到屋簷下坐著。」二人於是並肩坐在屋簷下的石凳上。 林萍珊道:「鏡兒,咱們也過去坐著。」 冰鏡道:「姊姊,妳不是說今個兒天氣好,我陪妳到處走走,好麼?」 林萍珊道:「不,我們就在屋簷下坐著。」 冰鏡向墨貍瞧了一眼,墨貍雙手一攤,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勢,冰鏡也不堅持,扶著林萍珊到屋簷下坐著。 墨貍側目凝視著燕飄絮,但見她容光清減,柳眉深蹙,面有憂色,長長的睫毛下垂,說不出的楚楚可憐,他隔了片刻,溫言道:「飄絮,妳怎麼到了這兒來?」 燕飄絮早料到他有此一詢,心頭猛地一酸,低低的道:「是冰鏡姑娘助我脫離火海的。」 墨貍吃驚道:「火海?什麼火海?」不禁向冰鏡望去,眼神示意相詢。 冰鏡和燕飄絮相視一眼,臉上頗有淒涼幽怨之色。冰鏡道:「燕姊姊,妳就告訴他吧!讓他知道妳這一年來是怎生熬過的。」 燕飄絮輕輕的嘆了口氣,極目仰望著青天流雲,緩緩的道:「當年你離開江陵後,我原以為你還會再度還鄉,於是便不捨晝夜的在山坡茅屋中等待。輾轉又過月餘,那時已是隆冬了,某日夜裡,一群官兵打著火把衝入我家,不由分說,便將我爹爹五花大綁的押走了。(墨貍聽到這裡,心中一凜:「是爹在京城裡告燕幕遮一狀。」)過了幾日,我爹爹就在城裡被皇帝斬首示眾了,燕家也被官兵抄了。我被府裡一個忠心耿耿的下人帶了出來,躲在荒山野嶺中避禍,日子一眨眼就是八個月,後來那下人也染病死了。我遭逢大變,舉目無親,又無自力更生的能力,想要出來尋你,便一個人流落江湖,孤苦無依,後來被人口販子賣到揚州天香閣……」她說到這裡,眼中依稀有一泓清淚,上齒咬著唇皮,竭力忍著不哭。 墨貍心頭突的一跳,激動的握住她的雙手,顫聲道:「飄絮,妳……妳怎麼會在天香閣?那是……那是……妳……這些年時以來,妳當真……當真淪落風塵了麼?」此言一出,登覺不妥,「哎喲」一聲,急急忙忙的道:「對不起,我一時情急,才會口沒遮攔,沒有別的意思。飄絮,是我不好,妳別見怪啊。」 燕飄絮幽幽的橫了他一眼,道:「我怎麼會跟你見怪?這些日子以來,我雖住在天香閣裡,但卻誓死守住我的貞節,無一刻不是想要脫離風塵。直到前幾日冰鏡姑娘重返天香閣,鬼使神差的撞見了我,替我贖身,才撮合今日你我的重逢。」 墨貍聽到這裡,心頭湧上一陣莫名的悸動,道:「飄絮,難為妳這一年受了這麼多苦。」 燕飄絮聲淚俱下,道:「你知道麼?我一直在等你,等你帶我遠走高飛,天香閣裡的日子雖不好過,但我始終相信有朝一日你一定還會出現在我面前。我時常夢見你這般抱我,也時常在夢中向月老爺爺祝禱,只消今生能再見你一面,我所受的苦楚都不算什麼了。我就知道,只要我懷抱十二分誠意,只要……只要我沒有一刻停止思念你,那麼我的願望就會實現。如今真的實現了,不但你出現在我面前,而且還這般緊緊的摟著我。」 燕飄絮當下又說起墨攻死而復甦,在江陵購了一座華廈,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墨貍回首當日與父親毅然決裂之景,再見今日與燕飄絮並坐敘舊,真乃恍如隔世,不由得百感交集,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燕飄絮霽顏開導幾句,墨貍才重拾胸懷,暫時拋開父親的陰影。二人互訴別來情事,直至夕陽西下,歸鴉過境,方始入內。 簫聲奏至最高峰,驀地劃然而止,只聽「喀」的一聲,卻是凌逍遙雙手折斷洞簫,拋在地上。他輕輕的道:「逝者已矣,夫復何留?」適才吹簫大耗內力,此刻精力虛脫,一跤坐倒在地,凝望著足邊兩截簫身,茫茫然只是出神。 凌逍遙「啊」的一聲大叫,輕輕的道:「鏡兒,鏡兒。」雙目向冰鏡望去,似乎在找些什麼,但目光一片茫然,猶似身在夢中。 凌逍遙全身一震,忽然緊緊摟住了她,喃喃的道:「鏡兒,我好怕,我真的好怕,我好怕一日妳也像他們一樣離開了我,妳別離開我,好不好?」 凌逍遙心下又是喜慰,又是淒涼,不再發話。二人形影相偎,黯然神傷到天明。 凌逍遙始終難以拋開父母雙亡的陰霾,伴著凌家眾墳,往往終日默無一語,墨貍覺得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便決定帶他到處遊山玩水,敞開胸襟。 聽說塞外河套平原氣象豪闊,陰山便在河套北邊,敕勒歌辭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凌逍遙長伴江南旖旎春光,此時更要換個新視野,五人放蹄馳騁,沿著黃河北去。 凌逍遙哪有心情遊玩?卻不忍拂逆三人一番好意,一顆心翻來覆去盡是想:「三哥這時候會在哪兒?武林正派已對他發出通緝令,不知他現下安不安好?」想起當年自己飽受正邪兩派的唾棄與追殺,如今所有慘遇都將轉移到三哥身上,自己在這世上便只剩三哥一個親人,倘若他步上絕路,那些嫉惡如仇的武林人士豈肯輕易放過他?想到這裡,全身冷汗淋漓,熱血如沸,正要開口表意,忽聽東北角隱隱有馬蹄奔馳之聲,聽聲音似有八十餘騎。林萍珊心頭一跳,道:「幹什麼了?」 墨貍沉吟道:「北方雖被苻堅統一,內部卻不太安定,想來只是尋常盜賊,等會兒由我跟小七打發便了。」林萍珊雖覺不是,卻也沒有表達什麼。 但聞蹄聲如雷,不遠處黃沙翻滾,塵土飛揚,一大隊人馬疾風般捲上山來,緊追著前方乘在駿馬上的灰衫漢子,叫囂叱喝之聲破空響起,其中赫然不少是五胡語言。身後追兵叫得兇惡,八騎反而愈奔愈快,雙方漸漸拉開距離。 墨貍、凌逍遙定睛一瞧,八騎中居首的兩名乘客面目依稀,一個相貌青瞿,一個丰神俊逸,赫然是金刀寨兩位當家扶笙和御慶。墨貍大喜過望,縱聲高呼:「大寨主,二寨主。」 二人倉促間聽得有人呼喚,不約而同的循聲望去,乍見墨凌二人,均是一怔,兩年前的記憶潮水價湧到,腦筋兜了幾轉,這才認了出來,不及招呼,身後追兵已到,長槍大戟,紛紛往前遞上,一時間刀光槍影,叫罵聲、呼吒聲、兵刃交擊聲、慘叫聲、馬嘶聲震天價響了起來,場面忒煞混亂,聲勢之壯,猶如千軍萬馬一般。 扶笙、御慶一揮金刀、一揮長劍,加之六名金刀寨兄弟,雖然敵眾己寡,卻絲毫不落下風,不多時便已殺了二十名追兵,然而己方卻也折損一人。林萍珊哎喲一聲,道:「怎……怎麼打起來啦?小貍子,快上去幫手。」 扶笙喝道:「對付區區幾個狗崽子,老子還用不著幫手。」怒吼一聲,金刀劈處,猶如虎入羊群,追兵驚呼後退。他從馬背上縱到一個騎青驄馬的漢子身旁,挺刀戳去,那漢子早有防備,馬鞭在扶笙臉上劈落,扶笙閃身避過,刀勢略沉,砍向青驄馬前蹄。青驄馬驚嘶一聲,前腿一撲,將那漢子筆直摔了下去。扶笙刀影一晃,那漢子登時身首異處。 這時御慶已被十餘名追兵絆住,數十條鐵鍊在他身周呼嘯而過,他展開身法在群敵中穿來插去,長劍白光一晃,將馬上兩名漢子的手臂齊肩斬斷,又揮劍刺死了二人。御慶劍上濺血,不禁熱血沸騰,豪氣陡生,只聽哀號慘呼聲此起彼落,轉眼間又是三人斃命。 扶笙叫道:「二弟,是氐人便留下活口。」 御慶道:「我理會得。」躍下坐騎,挺劍向一名頭目似的青衫漢子衝去,那漢子吃了一驚,鐵鍊當頭砸落,御慶一矮身,突然鑽至馬腹下,那漢子待要縱馬踩他,也已不及,被御慶一劍戳到背心,悶不吭聲,登時氣絕。 扶笙百忙中笑道:「這種白虜狗子,殺得好。」突然臉色大變,金刀舞得虎虎生風,刀光劍影中殺聲震天,直打得追兵人仰馬翻,四下潰逃。 冰鏡道:「林姊姊,什麼是白虜啊?」 林萍珊道:「妳一輩子住在江南,難怪有所不知了。白虜就是氐人口中的鮮卑人,這群追兵中倒有一半都是白虜,少部份是氐人和漢人,不過說也奇怪,金刀寨響噹噹的字號,怎麼有人膽敢侵犯?」 鬥到分際,金刀寨已有三人斃命,追兵卻已損折大半,地上橫七豎八躺著不少人馬屍體,有的兀自奄奄一息,讓眾人策馬來回踐踏,連掙扎哀號的餘力都沒有。過不多時,忽聽前方喊聲大振,近百名追兵從道旁衝將過來,手持強弓硬弩,將到近處,突然分邊左右馳去,將金刀寨五人困在核心,外圍密密麻麻的圈了一層又一層,好教五人難以突圍,只見群兵個個扯足弓弦,箭頭對準了五人,嚴陣戒備,為首的是個頭戴氈笠,跨著烏駁馬、手持紅纓槍的葛衫老者。 先一批追兵中只剩寥寥幾名氐人,剩下的均被扶笙二人殲滅,眾氐人見來了臂助,忙不迭的向眾兵士投奔。 扶笙道:「好哇,正點子總算到了。」 那老者冷冷的道:「兩位寨主都是當世響噹噹的人物,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快快拋下兵刃,別在逞困獸之鬥。」 扶笙呸的一聲,道:「要殺就殺,囉嗦什麼?」 那老者搖頭嘆道:「兩位都是不世之材,卻偏偏不肯投效明君,一味逞匹夫之勇,真是……真是……唉!」 扶笙揚眉道:「怎樣?」 那老者嘿的一聲,道:「你自己清楚便了,何必由我說知?」 扶笙道:「你這張嘴還能說出什麼好話?你既然說我一味逞匹夫之勇,下半節定是接真是胸無遠見,或許又要說我不識時務了,是也不是?」 那老者道:「你既已心知肚明,何必宣之於口?」 扶笙正色道:「我輩身在草莽,最要緊的是俠義為懷,救民孤苦,而不是跟著陛下行軍打仗,想見帝國大兵指日南下,雙方要是短兵相接,不知又要傷害多少無辜生靈。若是我等響應秦兵,豈非有悖金刀寨開山創立的宗旨?」 那老者道:「非也,非也,常言道:『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兩位寨主若肯降順,那是再好不過了。待陛下拿下江南,且別說是功名富貴,單是北國百姓感恩愛戴,已是足夠金刀寨揚威立萬,聲勢大非昔比。」 扶笙、御慶勃然大怒,御慶冷然道:「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兄弟縱使今日頸血濺地,也絕不為虎作倀。」 那老者冷笑一聲,道:「二位一意孤行,我只有將你們生擒回去,交由陛下發落。」 扶笙道:「你手下或是漢人,或是白虜,或是匈奴、羌人、羯人,而你自己卻是氐人,雖然為數眾多,卻都是一幫烏合之眾,以為拿副強弓硬弩就能上得了排場麼?這道理就和陛下伐晉相當,記住你今日的下場,就是帝國明日的氣數。」 那老者厲聲道:「危言聳聽,煽惑人心,光是你這句話,就已是大逆不道之至,你若不棄械投降,我立時長槍一指,萬弩齊發,你也休想活命。」 扶笙仰天打了個哈哈,道:「世上只有戰死的扶笙,沒有投降的扶笙。」 那老者心想陛下求才若渴,若一時魯莽殺了二人,最後倒楣的仍是自己。他臉色一沉,道:「我說扶寨主,你這又是何苦呢?」 扶笙嘿嘿一聲冷笑。林萍珊聽二人愈說愈僵,只怕立時便要動手,急得六神無主,一扯墨貍衣袖,道:「小貍子,快想辦法。」 墨貍急道:「正在想啦。」 凌逍遙驀地雙腿一夾,胯下白馬向眾兵士疾衝過去。眾兵士一怔之間,凌逍遙已衝破重圍,馳向那老者,霎時叫囂喧空,眾兵士箭如飛蝗,流星趕月,齊向凌逍遙射去。 凌逍遙伏在鞍上,翻出竹棒,撥挑拍打,近百支弩箭或被凌逍遙竹棒擊落,或在凌逍遙棒風帶動下失了準頭,插入土中,眾兵尚未搭起新箭,凌逍遙已向老者馳近一丈。驀聽颼颼兩聲,那老者已換過弓弩,向凌逍遙接連射了兩隻勁箭。凌逍遙左手揮棒撥開一箭,另一箭卻無論如何也不及架開,情急下右手一翻,食指和中指硬生生夾住來箭,喀的一聲,羽箭登時斷成兩截。 (倩女幽魂:黎明不再)
|
|
| ( 創作|武俠奇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