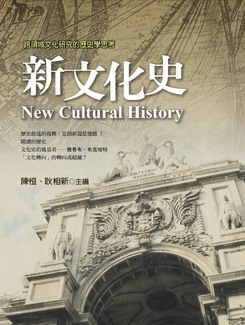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7/09/10 16:46:43瀏覽1358|回應6|推薦6 | |
文化史過去一直被等同於文明的歷史,而所謂的「文明」多半指的是伴隨資本主義崛起與帝國主義擴張而形成的歐洲文明,最精妙的代表便是藝術史(諸如建築、文學、繪畫、雕刻等等),美學價值是核心關切,是人性(humanity)的文化表現,最終設立正典(canon)形成規範。文化史的書寫成為區分自我(主人)/他者(奴隸)的文化政治,是歐洲布爾喬亞登上世界舞台成為歷史主體的論述實踐,同時提供歐洲帝國對外殖民的正當性說詞,生產全球擴張的慾望。作為勝利者,布爾喬亞必須一方面剷除舊有保守勢力,一方面建立自身的文化優勢(品味),這便是十八世紀歐洲歷史主義者承擔的任務。 姑且不論這個現代主體與帝國主義互為表裡的後殖民批判,此宣稱無關利害與權勢的美學神話與現代文明,在西方世界內部也並非一派祥和的太平盛世。先有十九世紀的階級革命,並在二十世紀形成各自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然後是二十世紀六零年代中期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分別從種族、性別、階級等不同角度批判現代主體及其文化權威。此即新文化史誕生的土壤與知識任務。可以說,新文化史是西方內部自我批判的產物,部分學者甚至認為這是整個(西方)現代性論述內在的矛盾與動力。 循此脈絡,新文化史在研究對象與方法論兩個方面有突破性的進展。首先,在研究對象上,新文化史從帝王將相的廟堂轉向常民,從支配者的凝視轉向被排除與被壓抑的他者(瘋狂、勞工、婦女、同志、少數族裔…),文化不再是附庸風雅或是藝術鑑賞,而是充斥著權力的刻痕,是讓常民噤聲乃至刻板化的支配效用。新文化史對「文化對象」與「文化」本身的反思,受人類學的理論滋養甚多,例如Marshall Sahlins、Levi-Strauss、Clifford Geertz等。 然而,儘管新文化史有此初衷,但如果沒有方法論的突破,仍然很難克盡其功,因為歷史留存的檔案,若不是勝利者的痕跡,也是經由勝利者安排與挑選的結果,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關於瘋狂的檔案。特別在文化史的研究對象上,能夠經受歷史長河的沖刷而留存下來的文化造物(例如建築、文學、繪畫、生活方式等),很難不是權勢者的遺留,只要看看今天重要的觀光景點的清單(大教堂、羅浮宮、紫禁城…),以及總是引起爭議的古蹟認定標準(如台北的違建聚落、新莊的樂生療養院都一貫以「違建不符美學價值」為由要求拆除),便可一目了然。於是,新文化史研究比起移轉視線替換對象之外,更艱難的挑戰便在於被排除者的歷史痕跡經常同時在排除過程中被一併抹除,有幸殘存者也會因為被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安插進支配體系的管理系統中而面目全非。因此,想要打開文化史的疆界,除了理論視角的轉換之外,終究得在歷史材料、歷史編纂的場域上一爭高下,也就是說如何從既有的檔案系統的排除結構中,解讀出被排除者的歷史便成為方法論的主要課題,甚至說是勝負的關鍵都不誇張。Foucault的博士論文《古典時期瘋狂史》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想書寫的不是被理性社會所建構的瘋狂的歷史,而是要從已經被排除系統整形後的檔案中,寫出被壓抑的瘋狂自身的歷史。新文化史在方法論上的巧思,精彩紛呈,履履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成見,以及早已乾枯的創意。 《新文化史》這本論文集是新文化史開疆闢土的里程碑,不僅勾勒出新的發問角度與研究方法,更提供重回爭論現場的重要線索,是進入新文化史領域不可或缺的指南。 |
|
| ( 知識學習|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