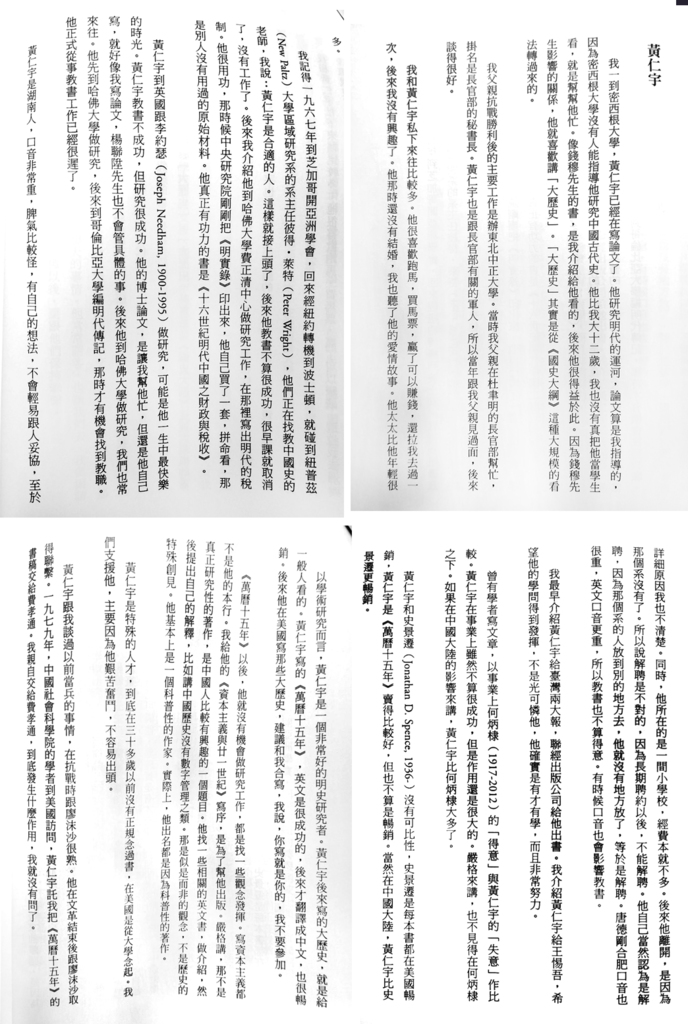GuangTian捎來余英時書,同時也郵贈ZG 一冊,通話交談,都在說黃仁宇,而黃已是儕輩追隨仰望中國近代史觀之所繫,心有所梗,因整筆留駐:
黃比余大12歲。余對黃語帶數落,雖未致“孽徒”,然殊乏敬意。我以為不能盡以史學界傳統的文人相輕看待。可以分三點說:一,黃的論文:明代財政。二,黃代表作【萬曆十五年】。三,黃作品主線:【大歷史】。
一,黃的論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余說黃教書失敗,失業,而余牽線,介紹他去了哈佛費正清中心,
―――――《《《《。。。後來我介紹他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做研究工作,在那裏寫出明代的稅制。他很用功,那時候中央研究院剛剛把《明實錄》印出來,他自己買了一套,拚命看,那是別人沒有用過的原始材料。他真正有功力的書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余肯定黃書有功力,但黃是偷吃天山雪蓮才長奇功,而雪蓮《明實錄》乃是中央研究院種的,黃拿到剛印出來的原始材料,搶先看完,才寫成明代稅收。余固不能居功,謙稱論文指導只是名義,但亦不否認黃發跡自己是續命貴人。而黃用“數值分析”的方法學去分析明代稅收的原始數據,至少在中文的史學界是創舉,蓋吾國史學界無論長幼高低一貫缺乏數學基礎,是理科的貧瘠地,黃數學好,來自三個基礎(1)在南開(機械系)打下基礎,(2)入緬任遠征軍鄭洞國秘書,還有(3)公派入學美國軍校(陸軍參謀指揮學院),卻被硬分去主修人事動員(參一)。這三個罕見經歷都讓本性嗜理輕文的黃如虎添翼,等到戰後復員進大學,到了安娜堡,等於一個理工科學生,被塞進歷史系。
黃從明實錄整理400年前的納稅數據,並非簡單套入統計數學公式而已,須以橋樑實物―――米價,為折算基礎,等於normalization,這在理科荒地的歷史系中,也是天方夜譚。天方的論文,余如何指導?
二,黃代表作【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被耶魯選為年度最佳論文。中文史學界吃味者眾,吃味圍繞三項:數學,英文,歷史。――――比黃數學好(又英文好)的中國人,不懂或不屑明史。比黃史學好(又英文好)的中國人,不懂或不屑數學。
總之【萬曆十五年】取巧,黃沒原創,用英語來介紹西方陌生的中文世界。以經濟數學/應用統計學的方法來治史,冷飯熱炒兼媚俗。 耶魯立場可以代表西方精英層,而萬曆十五年先有英文後再英翻中,也可以看作美國大兵對小鳳仙驚艷,於是出口轉內銷,麥當勞賣包子而熱銷。 說西方史學界在同溫層內取暖,對中國歷史僅知皮毛,並非無的放矢。西方史學界同溫層以兩河流域為夏商周,以希臘羅馬為秦漢,以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大航海為宋元明清,研究離不開歐洲舞台。對東亞尤其中國陌生。談東方熱點只限日本和印度,論及中國缺乏起碼的善意,像卡斯達進入印第安部落,荒謬如馬可波羅拍拖杜蘭朵公主。而黃以西方可以接受的經濟學和統計學,分析確有實物的明代逐年稅收數據。萬曆十五年走紅像湯唯,章子怡總是恨恨地說“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三,黃作品主線:【大歷史】。
”大歷史“可說是黃仁宇全部歷史著作的主線,也可以說是他中國史觀的總結,黃沒有用“宏觀歷史”這一稱呼,既可以說是英翻中的直譯,也反映他對個人觀點突出其專利。外行看熱鬧,怎麼翻譯無傷大雅,內行看門道,名詞背後有原則之爭,老師余英時明顯不認同。黃用“大歷史”因其內容不止泛泛而稱的 “宏觀歷史”,黃將中國歷史分成三段,即秦漢帝國,隋唐帝國,宋明清帝國,這個觀點並非標新立異,因史學界將中國傳統斷代史分期從24史改為八段(毛澤東或翦伯贊以農民起義分期)、或10段12段。。。所在多有,也各有主張與論點亦皆言之成理。但共同點都在於傳統一家一姓的改朝換代,只是上層政治鬥爭落幕換了招牌,並不能同步反映時代的整體變遷,而物質基礎的變化決定民生、生產關係、水旱天災、武器形勢、交通運輸,其變化也許更能說明分段的合理性。黃仁宇把24史分成三大帝國,其實更能看出他多年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與心得。這當然因為他半路出家,中國古史古書讀的不如文科學生多,很有點科學家治史,先訂出假說或model ,再慢慢蒐證證明,從科班文科學者,黃不遵循漢書食貨志、不好好研究管子、努力抄敦煌卷子歸類排比,當然是理科學生跳槽玩弄,不但隨興馬虎,更顯專斷傲慢。
但我以為黃的三段分法也許粗糙,概念先行而闕實證,但黃原本即心不在此,對完備舉證無意追求,黃推出假說,草草分完三段,即跳到中國未來走向的申論,他想說的是:中國未來必須進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前面三段可以概括性描述:物理化學生物帶動農漁牧礦等等條件,是下層建築,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是上層建築,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因為社會矛盾產生了戰爭剝削和殺戮,內戰外戰你死我活,也許是下層建築規定的上層結果,三個帝國呈現螺旋狀的上升,問題糾結盤根錯節,不能也不必從道德的是非對錯上算賬,可以回歸下層建築的制約來尋找脈絡,也可以從大歷史變遷的必然性,來跳脫悲情與殺戮報復,物質條件已經渡過工業革命和大航海,已經回不去了,用數目字管理進入無性世代比較可行。
作為一個理科出身對數學英文歷史三者都十分喜歡的基礎上,我更理解黃觀點的成因,而黃若用字不小心,一再強調物質基礎,恐怕被打成唯物史觀信徒,應非黃所願見。如果我用學習生物醫學,對達爾文演化論的理解和服膺作基礎,來理解黃仁宇的大歷史,黃把中國歷史上生旦淨末丑的愛恨情仇全部昇華成森林裡的動植物,他們的殺戮追逐須服從食物鏈,其互動和行為固然有偶發機率,仍遵循物理化學,有其必然性。
這種理工科學家的作學雅興,於文科的余英時及其所屬的學者群體,當然陌生而不以為然,而科學家跳槽膽敢用數學公式分析歷史,余當然反感。其對黃著仍出美言,甚至多處誇獎,已經是學者的敦厚和謙沖,很是難得。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