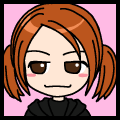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10/21 21:42:51瀏覽2166|回應2|推薦28 | |
夕陽下,鑰匙框噹框噹的聲響,把原本灰撲撲的巷子閃得像一彎璀璨華麗的鑽石項鍊,第七路隊的孩子陸續岔出蟻狀軌道,前進至秘密基地(鑰匙是開啟基地的通關密碼)。那時,大人都在辦公室裡、轟隆隆的廠房裡,或者,還困在震耳欲聾的十字路口動彈不得。一如往常,小怡往左,我往右,她是路隊裡唯一不用帶鑰匙的人。在那段經濟飛躍的年代,像小怡媽媽一樣的家庭主婦,是眾多職業婦女欽羨的對象。我開啟密碼的瞬間,我媽或許正要上工,同時,小怡已經將制服脫下,吞嚥著熱騰騰的飯菜。 通常,她會快速終結飯桌上的食物,帶著作業本移動到我家。 那是我在等大人揹負倦意回家的空檔,她會陪我啃食我媽匆忙間扔在飯桌上的芭樂,蹲在藤椅上迷戀卡通凡爾賽玫瑰,對著我們不了解的法國大革命哭與笑,開啟懵懂又早熟的悲歡情愫;我則陪她寫功課,相互擦拭歪斜錯誤的字跡,或者注視她小心翼翼清洗她的右眼。那幾可亂真的假眼球,是她全身上下最昂貴,卻不會遭竊的寶物。我撫慰她的殘缺,她擁抱我的孤獨,一種心靈交易的儀式,潔白而誠懇。 她很早就懂得避開使她重複陷入困窘的話題,關於失去的半邊視野。孩子的注意力未曾聚焦在她些微不同的右眼眼窩,但有著評論的、同情的、戲謔的各式街談,終日如流星襲擊。她無法假裝無謂,於是有著過於早熟的神態;母親匠氣的情緒偽裝使小怡不愛待在家,卻希望我別做個遊蕩的孩子,生活不夠明亮,因而我們都在尋找失落的火種,但純真仍然是最大的武器,即使我因寂寞而哭泣,她因流言而嘆息,彼此都相信,必然會有更好的戰士來拯救世界,讓所有醜惡與委屈滅亡。。 八零年代的環境事物價值觀有ㄧ片模糊的地界,我浮游在那潮間帶裡,渾渾噩噩自行咀嚼由電視聚攏起來的各種知識,包括病徵。身體某處的缺損,從不讓我感到厭惡,那是生活中時時刻刻都在接觸的,只當那只眼球是昂貴的玩具,像爺爺的假牙,隨時可以拆卸、清洗,而試圖忽略隱約侵入的異樣眼光;我們始終相信,殘缺可以用幸福感縫補,而孤獨可以用陪伴填滿,彼此都以為,可以治癒對方的傷口,也不間斷地相互努力,在每個陽光灑落的假日跳繩跳房子跳越ㄧ格又ㄧ格的小學生活。 木訥寡言讓我從未能成為討喜的孩子,但她曾說,殘缺的枝幹會長出孤獨的葉(因此我幾乎認定她未來會成為文學家)。我們具有類似性格,生理與心理,殊途同歸,這是我們相濡以沫的原因。直到小怡父親中風倒下促使我們提早走向別離。她在一個冬日下午默默離開小鎮,我們都來不及難過,因為一切如此倉促,我們的眼淚與苦悶很快被繁重的學業壓扁榨乾,存在過的童真瞬間蕩然無存,友情在這時顯得毫無質量。 通過入學測驗,我莫名進入中學升學班,她則被安置在鬧哄哄的市區學校,落入我永遠失憶的班級號碼。那是一種向上與沉淪的切割隱喻嗎?種種成長的驟變崩裂彼此的生活交集,距離是沉默的恆河,在枯黃書頁捲動的日子裡,總反覆想像,若她未曾離開小鎮,我們終究幾度相遇在課間的走廊,佇立在平靜河水的兩岸對望,卻無法吐露關切的語言,此情此景非我們所能承受所能釋然。於是那樣的心情讓我從不主動連絡,刻意讓她的消息如風,偶爾飄過眼前瞬間又蜿蜒至我無法到達的地方。該如何詮釋那些風稀雨疏的成長過程?推開記憶的後窗,從來就不是ㄧ氣呵成的青春像像過於疲乏的戰爭,以艱困的速度推進,或陷入泥濘中,陣亡。 那些日子以來的灑脫只是一種充滿霧氣的隱喻,因為我們都以為,必須以面對永別的頑強姿態去對抗分離的酸楚,彼此定義的早熟才能成為真實的標籤,牢牢貼在我們的身上心上。很長一段時間毫無音訊,我們是不由自主的落葉,秋天的風將兩個女孩各自吹向難以抗拒的年少,始終以為無法承受青春那樣無以為繼的殘破樣貌,直至走過它,才明白其實擔心都是徒勞;並非因為擔心的事未曾發生,相反地,ㄧ切必然發生,我們只能選擇以當初約定的步伐踏過所有紛擾,而不能選擇避開它。 產業外移的工業下坡時代來來臨,我媽退隱成為她從前所渴望的「家庭主婦」,讓我已然淡忘幼時過早感發的孤絕,,小怡媽媽卻為了生計,胭脂ㄧ抹踩著高跟鞋轉瞬成為幹練的保險業務員。我們初分離那幾年,小怡開始進駐她未曾經歷的,空蕩蕩的城堡,攤放著已入沉痾的父親及尚有溝通障礙的越傭,兩具分別被生理與心理所困侷的體肉,散發無能為力的霉味。家中鑰匙開始與她隨行,終日遊蕩在燈熄攤收的街心,非不得已不願回家,以ㄧ種被生活剝落的姿態,靜靜抵抗逐漸萌發的情緒野獸。 意外接到她的電話,沒什麼猶豫,決定去看她。那時她已患有重度躁鬱,我們攀坐在樓頂的露台,沉默就這樣忽然衝撞到面前,逼迫我們打破僵局。人生太容易被扭轉,從前困惑,是因為抉擇呈現徬徨模糊的樣貌;現在困惑,卻是生活底蘊太過清晰銳利的緣故。也許我把時光想得太艱困了,所以才會產生日疏路遙的錯覺,那些明明就是昨天的故事,有幾千個細微末節的日子實實在在被攀越了。歲月離離,真正的心痛是不可諭示的,我只能眼睜睜任憑它兵臨城下而束手無策。 她說,就讀高職夜間部時,有次下課,錯過平時搭乘的公車,延遲了返家時間。 在露臺上,她緩慢抬頭向天空。相對於從事教職的姊姊與就讀國中資優班的弟弟,命定的生理缺口與不靈光的頭腦,讓小怡始終以蜷曲的姿態及減半的視野瀏覽這個世界。漸漸有水珠噴落下來,我們轉身下露台,走進房間,周圍濕氣裡凝結的哀愁,只是ㄧ道薄膜,卻讓我不能看清彼此的距離。 寂寞膨脹到極致的時候,也成為一種景色,你只要闖進去就明白了。她在絕望裡渴望愛,並且不停在愛裡證明其本質是絕望,之於她。那夜她被迫離開家,跟隨某個到便利商店買菸的陌生男子回到獨居處所。 「你的眼睛很漂亮。」男子說。 男子停止動作,轉身坐起來翻找抽屜裡的打火機。 「我以為妳都是這樣得到溫暖。」他抬頭噴了一口菸,小怡抱著膝蓋,看見半掩的抽屜裡隱約有一些穿著暴露的女孩照片。 「出去,不要再讓我看到妳。」他轉身睡了。小怡還不能回家,只好頹坐在電視櫃旁直到天亮,在男人輕微的鼾聲裡,狼狽地逃離她以為有愛有溫暖氣味的樓閣。 「就算我被強暴了,我媽也會認為我是活該。」 我曾經以為很了解她,忽而又覺得在她的世界裡,離索才是常態,過於親暱會讓人散發某種圖謀的意涵,像可憐或同情的氣味。感嘆離散的時間總是比相聚多出ㄧ大截,分開太早,明白太晚,明白人生之所以為人生,在於其不可替代性。我們從某個時間起就已悖離,面向錯綜複雜的路線,不期然的交集是個美麗的誤會,我無力包覆與她格格不入的心情,只能注視她歪歪斜斜走向看不見盡頭的歧路。 從來從來,總覺己身是孤蓬,不知身在何處,也無從得知去向,然而,當我逐漸找到安身的養分入土生根,小怡卻成了浮萍,隨著破碎的激流斷了消息。生命裏曾經有過的相依是那樣不真實,那樣恍如一夢,甚至以為只是前世殘存的記憶。緣分是那麼美麗而纖細,相對也微弱,並且總是直到走過了,才發現最綿密的風景都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我努力回想卻記不起來的,其實是最重要的片段。 不去數算的生活無喜無悲,平凡的晨昏無潮無浪,踏進成人的世界如此無趣,世界沒有昇華沒有淪落,也沒有什麼救世主爬出電視機拯救地球,汲汲營營於腹肚而工作,成為生命裡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走入社會,走入真正的人生。 某個上班日,小怡在我心裡刻了一刀。 我走進A2廠房時,阿隆側身彎下腰。發現有人走進來,他慌張轉身,或許禮貌性怕驚嚇到我,卻不知道,他習以為常的動作也是我記憶裡熟悉的映像。一進公司,便了然於心,他的眼光,正是我從前灼灼注視著的,同樣的視覺頻率、角度,那已是我童年畫面中的一塊胎記。 「不要看我現在這樣,我還沒出事的時候也是少女殺手欸!」後來他攤著手笑談這件事。 幾乎相同,他的右眼,軟質假眼球,色澤蒼白而無神。一個年輕氣盛的飆車少年在一場意外裡的遺落,相較於小怡的無可奈何,他的毫不在乎讓我感傷。 「生命如果沒有遺忘,怎麼能夠往前走呢?。」小怡說。 可是我卻沒有忘記妳。 會不會是記憶跌得太深,老是撿不著所以扔不掉? 秋天的天空蒙上一層含著灰塵的黃綠色,那些日子我常帶著這些回憶騎在看不到盡頭的公路上,幾回魂夢裡,妳的身影愈來愈稀微,我的憂愁因此感到日漸厚重。小怡,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想起茫然青春的背影,希望從此妳以幸福為依歸,殘缺是圓滿,因為有缺才懂得圓的美麗。 夕陽下,路隊散去了,我跟小怡互道再見,待會兒見,明天見。 反正,總有一天會再見的。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