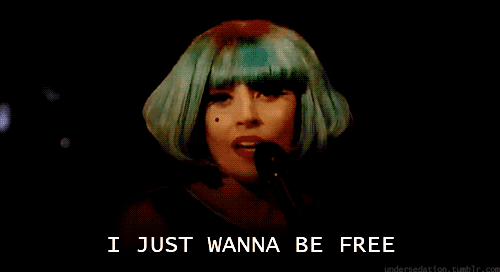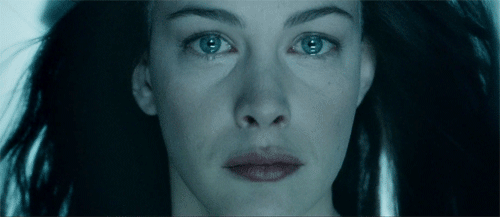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8/10/08 23:19:30瀏覽1943|回應1|推薦19 | |
|
阿清是個PUB歌手,雖然也有經紀人,但他的經紀人都在幫其他客戶服務,幾年下來,他還是在唱PUB。 唯一的不同,就是底下觀眾一批批換了,會坐在底下聽他唱歌的女朋友也一個接著一個換了。 阿清的木吉他沒換,他其實想換很久了,但每次領到微薄的駐唱費,還是捨不得換吉他。拿來吃飯、喝酒、抽煙所得到的快樂,相較之下還是容易許多。 素如是一位民歌愛好者,也是一位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她拿台灣的民歌駐唱當論文題目,這麼聯繫上了阿清,希望跟阿清做次訪談。 阿清答應了,他沒有理由拒絕,訪談通常能換到一頓免費飯。而且他確實有滿腹的牢騷,平常沒幾個人能說,女朋友才會聽一聽,但聽個幾遍,也就分手了。 沒有太多期待,阿清一面吃,一面聽素如的問題。那些問題,阿清回答了幾百遍,「為什麼當職業歌手」、「未來的夢想是什麼?」、「受到誰影響」、「收入如何」…… 面對這些問題,阿清的回答基本不超過三句,否則他自己都會覺得不耐煩,更何況他真的餓了。 素如約的是他喜歡的台式牛排館,玉米濃湯、沙拉跟紅茶可以一直續,吃到飽。 「妳沒要問的嗎?」阿清一陣子發現素如沒動靜,拿紙巾擦擦嘴,抬頭看素如。 素如的眼淚潺潺流下,無聲無息的像是季節最後的雨水劃過窗戶玻璃。 那片窗戶玻璃,是素如的臉頰。 阿清抽了兩張紙巾給素如,素如沒接,大聲哭起來。 店裡其他顧客都朝阿清方向看過來,一半的人看熱鬧,一半的人眼神帶著對阿清的究責,像是在指責他是個負心漢。 阿清內心罵了好幾次「幹X娘」,但他不敢有大動靜。 離開牛排館,阿清和素如坐在關渡大橋下,看著波紋閃爍的河。 素如跟博士班學長分手分了半年,還分不掉。 博士班學長已經有了新的女友,素如從現任,變成前任,如今又像個第三者。 在PUB駐唱多年,雖然唱不出什麼名堂,至少傷心的故事,阿清聽得多了。 阿清點了支菸,抽了兩口,問素如要不要,素如搖搖頭。 阿清說:「你只是想證明前男友的真愛是妳。但那又怎麼樣?誰有義務告訴妳?」 素如的眼神迷濛起來,像是在思考,又像靈魂遁逃到內心深處,好規避阿清犀利的評論。 見素如這樣子,阿清覺得今天真是太累人了。做了訪談,還要做心靈導師,光吃牛排有點虧。 「走了,再聯絡」 阿清揹著他的吉他,上到橋邊,騎上永遠不會背叛他的摩托車,突然覺得自己過得挺幸福。
§ 難捨難分的自我 自我,從形上學的角度看是整體的。 但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註定是割裂的。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哲思(Carl Rogers)說,人的自我可分成兩者:「主體自我」與「客體自我」。 「吾日三省吾身」,前者是主體自我,後者是客體自我。 主體自我,無時無刻不在檢視客體自我。比如一個愛漂亮的人,他照鏡子,妝點自己的面容,他妝點的就是客體自我。 一個愛面子的人,他不在乎別人對真實的他有什麼評價,他捨棄主體自我,因為他更注重別人怎麼評價他的客體自我,好比長相、學歷、職業、身份等。 熱戀初期,主體自我渴望得到愛與關懷,渴望得到真正與另外一個人融合。 但是,為了讓對方愛上自己。主體自我往往會把自認缺點的那些部份隱藏,甚至掩蓋,只把好的一面給對方看。 這些好的一面,又往往跟社會價值觀相結合。 比如一個社會如果都喜歡攀比收入,那麼拿收入出來給大家檢視,感覺對客體自我的被承認,更加有利。 沒有自信的人,就會逐漸失去主體自我,因為他不願意把主體自我加以呈現。 接著,他會花很多工夫去修整客體自我。 客體自我能被肉眼看見,不需要特別用心感受,可以用錢或物質的東西加以編修。就像某些專家的學歷,花錢買的,花人脈打點。 但一個人的良知,那屬於主體自我,花錢沒用。 愛,那也是主體自我的一部分,是一種內在感受。 當兩個只敢呈現客體自我的人在一起,他們不可能真正快樂,因為他們大多數的力氣都拿來壓制主體自我,要他們別出現,深怕主體自我的出現會毀滅得來不易的感情。 這種壓抑的消耗,又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在愛情中很努力。 實際上,依靠「努力的欺騙」來維持感情,那種努力得到的不是愛,因為主體自我感受不到,知道對方要的對象是客體自我,是主體自我打造的幻影。 我想起林宥嘉有首歌,叫《想自由》:
每個人都缺乏什麼 我們才會瞬間就不快樂 單純很難 抱負很多 已經很勇敢還是難過
許多事情都有選擇 只是往往時候我才懂得 情緒很煩說話很沖 任何人的溝通有時候沒有用
或許只有你懂得我 所以你沒逃脫 一邊在淚流一邊緊抱我 小聲的說多麼愛我 只有你懂得我 就像被困住的野獸 在摩天大樓渴求自由
每個人都缺乏一定程度的勇氣,讓主體自我呈現,讓它向著愛的暖陽。 因此客體自我得到很多,主體自我就越孤單、寂寞、難過。 當某些人在努力的追求客體自我的成就,空虛感也會更強。因為和內心主體自我的距離更遠,隨時可能失去聯繫。 一旦失去聯繫,一個人就會永遠的活在別人的陰影中,成為社會的傀儡,靈魂死亡,只剩軀體。 所以某個角度來說,每個人都很卑微,卑微到渴求有個人看見我們的主體自我,能夠不嫌棄,完整的擁抱。 這好像在說,每個人都像個殘缺的畸形兒,不值得被愛。 最高的愛,也因此被定義帶著憐憫,是一種願意共生、同死,沒有嫌棄的包容。 去接受這樣的愛,甚至相信有這樣的愛存在,我以為越來越困難。 這個社會給人的壓力很多,太多「典範」在告訴一個人該怎麼活。 所以悲哀的結局,大概就是一群被困住的人,彼此取暖。 這意味著,對真愛的放棄,也是對自己的放棄。 § 結語 當一個人自怨自艾:「為什麼沒人愛真正的我?」 可能有個相對情況是,這個人「不相信有人會愛真正的我。」 面對客觀自我膨脹,壓迫主觀自我生存的情況,最好的解藥,就是給予主觀自我更多生長空間。 這表示我們要跟社會抗衡,甚至跟我們的親朋好友,甚至伴侶發起戰爭。 但這有時無法避免,就像有的女孩出生載重男輕女的家庭,父母對她只有兩個期望,一個是找到金龜婿,最好金到可以改善全家的狀況。 要是家裡有哥哥或弟弟,那麼這個女孩,還得對家中男性繼承人給予金錢上的幫助。 這時候,翻臉也許不失為一個好策略,如果這個女孩真想保護主觀自我,不要變成父母的玩偶。 如果你身邊有主觀自我得到自由的人,好好珍惜,多跟他親近,也許你就能放鬆下來,相信完整的自己,能得到完整的愛。 當然,不只是得到,也要試著讓主觀自我扮演給予的角色,相信自己有能量去愛。 是的,這也就是所謂「實現自我」的意義所在。
|
|
| ( 心情隨筆|愛戀物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