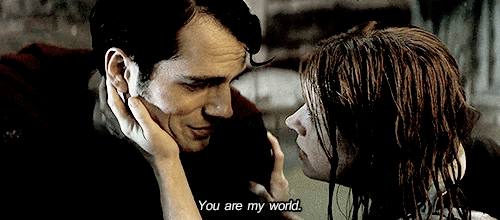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8/04/05 06:05:45瀏覽5591|回應1|推薦23 | |
◎前言 今天看了電影《金錢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裡面有個角色叫契斯(Chase),是一位退役的CIA特工,總是穿著非常有品味的西裝。 他奉命幫女主找到被綁架的孩子,剛見面的時候女主問他:「身上是不是隨時帶著槍?」 契斯回答:「不帶,那會破壞西裝的線條。」還補充道:「只有沒有錢的人才需要槍。」 最近某位藝人的孩子,在美國買了幾把槍跟上千發子彈,並且對學校做出攻擊宣言,因而被逮捕。 是否只有沒有錢的人才有槍呢?我想槍可能更重要的象徵是「安全感」。 一個對自己很有自信,內在安全感源源不絕的人,不太需要外在的安全感,比如通過槍,或是金錢。
◎對你來說,錢是負擔,還是財富? 我想起前幾天聽了德國心理醫師烏薩梅爾(Bertold Ulsamer)的演講,在一個談賺錢與投資的活動。 烏薩梅爾很有趣,他開場就說不知道主辦單位為什麼找他來,他說自己一生基本沒有為錢煩惱過。 倒不是說他生來就像王思聰,或者爸爸是李嘉誠,而是對他來說錢不是負擔。 他提到對某些人來說,錢是負擔。 沒錢,痛苦;有錢,也痛苦。 沒錢的時候想著這也不能幹,那也不能幹,感覺自己什麼都不行。有錢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花,花了又怕失去這個、失去那個,或者害怕失去錢。 如果內心恐懼,不管有沒有槍,恐懼感都不會消失。 我想通過他的看法,很好的說明了某些現代人的焦慮。好比最近台灣有個新聞,一些民眾認為月收入要有十萬台幣(約兩萬人民幣)才能生孩子。或者像我在上海,身邊不少人為了買房種種花費苦惱。 然而,到底要多少錢才夠? 如果內心沒有自發性的安全感,那麼即使有了錢、買了房,要擔心的事情還是沒完沒了。 就像養孩子,月收入十萬的兩倍、三倍,真的就能免除養育孩子的各種煩惱嗎? 回過頭來說,烏薩梅爾要聽眾好好檢視生命歷程中,自己和錢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關係,「為什麼錢會成為負擔,而不是為我們生活所用的一種工具?」 可能我們會發現,錢不是問題,問題可能是我們內心的某種貪婪、自卑,或是某種不安全感。 好比有種心理效應叫「冒牌者效應」,有些學歷很高、資歷很好的人,卻感覺自己其實沒有別人看起來那麼有實力,在公眾背後,深深的為自己的「無能」不安,感覺自己天天都在演戲欺騙別人。 實際上這樣的人可能確實很有實力,但他感受不到,也無法轉化為真正的自信。
◎總是渴望擁抱力量的人,很可能是因為內在缺乏力量 我記得在007電影《明日帝國》中,龐德的某個前任問他:「是不是跟過去一樣,帶著槍睡覺?」 龐德真的無堅不摧嗎?如果按照這位前任的說法,龐德其實是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人。確實他的工作也使他活在隨時可能被傷害、失去生命的恐懼之中。 這部份在換了角色,007電影去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化之後,自《皇家夜總會》系列後,確實把這部份人性的一面拍進戲裡,我們看見龐德非常沙文主義,好掩蓋心底的迷茫和害怕失去的依戀恐懼。 在電影《神鬼無間》中,也是如此,詐欺犯法蘭克變換機場、律師、醫生等社會地位高的職業,一方面是方便騙取金錢,另一方面也顯現他害怕扮演真實自己的恐懼。 當他把這些角色演得越好,離自己就越遠,也越不敢跟心愛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現實生活中何嘗不是如此,隨便一場酒會,只見琳瑯滿目的頭銜,但有多少人真正擁有充分的自信? 即使脫下華麗的晚禮服、卸下裝容、扔掉名車,拋去各種頭銜的自我介紹,依然能夠自在且快樂的享受當下呢? 回頭來說,我以為過去多數的童話故事,某種意義上都反應了社會對於女性的打壓。 白雪公主、灰姑娘、長髮公主、睡美人,哪一個不是「養」望著王子,看見王子的頭銜就徹底獻身了呢? 到了現代,即使不是公主,獨立自主的女性也能抗拒王子的誘惑。因為她們有充分的能力、視野與信心去過好自己的生活,而追求理想生活也無須依靠男人才能達到。 描述推進近代波蘭性解放女作家薇斯洛卡(Michaliny Wisłockiej)的電影《波蘭愛經》(Sztuka kochania),或許就是一個例子。 薇斯洛卡就像《性史》作者張竟生(當年從里昂大學拿到哲學博士到北大教書,年紀比胡適還輕)。 他們都用自己的生命,實地的「活」給所有人看,告訴大家性並不羞恥,羞恥的是「利用性去滿足權力,或是不尊重他人,只為滿足自己的性觀念」。
◎欲望就像一面鏡子,總能照見我們的不安 越是有信心的人,越能將安全感的來源尋求自自己內在,而不是過度流連在外在價值上,以致最終迷失於金錢、權力、關係或物質的洪流之中。 從這個角度,我想起佛洛伊德曾說,戲劇的動力離不開兩者,一個是「野心的欲望」,一個是「性的欲望」。 兩者欲望可能都是一種不安全感的顯現:因為對生存沒有安全感,所以必須掌握權力,控制身邊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因為對情感交流欠缺安全感,不相信自己能夠被愛,所以通過性的力量,以此來支配關係的生死。 可悲的是,兩者都使他人無法做自己,也使自己無法做自己。
◎阻礙別人正視自我,是一種最沒有安全感的暴力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就是從創傷與復原的心理研究,來談安全感與自我接納,乃至於接納他人之間的關係。 研究背叛創傷的心理學家弗雷德(Jennifer Freyd)就談到:當一個人欠缺獨立生活的勇氣和信心時,他會對背叛產生「盲視」(betrayal blindness)。 所以在心理諮詢中,要幫助來談者看見自己被背叛的事實,無論是一位女子面對父母長年重男輕女、壓榨自己的青春和金錢去寵溺自己的弟弟;或是一位學生,面對老師多年來的性侵;或是一位妻子,明明身邊的人都看見她的丈夫出軌,她自己卻總是視若無睹…… 更進一步,弗雷德談到機構、社會、國家與國家的背叛盲視。 譬如二戰時期,德國民眾為何讓納粹殘殺猶太人。因為當時納粹控制輿論,讓人民對統治者產生過度的依賴,就像嬰兒依賴父母的狀態,那麼當人民受到暴力對待,也會產生背叛盲視,對暴行視而不見。因為正視暴行,會讓他們恐懼,恐懼生活失去依靠該怎麼辦。 或者以前陣子的 “Me too”譴責性侵與性騷擾的運動為例,為什麼某些老闆能夠在性騷擾下屬多年?往往是因為其他同事礙於生活,於是下意識的對老闆的舉動產生盲視。簡單說就是睜隻眼,閉隻眼。 因此,按弗雷德的研究,盲視來自「少了對方,就無法獨自生活」的心理狀態,好以此保護自己的心靈不要繼續受傷,給自己一個繼續依賴加害者的理由。 唯有當來談者逐漸的找回獨立生活的勇氣,看見自己具有放下這段關係,仍能好好活下去的希望,他才能夠接受「確實『那個人』不斷傷害他」的事實。 以婚姻諮詢為例,在她的個案中,當受家暴的妻子不再是家庭主婦,逃離先生身邊,開始一點一滴的找回獨立生活的節奏,她往往就能夠正視丈夫的暴行,接受自己受虐的事實,這才能夠進入面對真相,處理真相的自癒階段。 ◎看見自己到看見彼此 儘管許多心理學家、諮詢師都談我們需要內在的安全感,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要像座孤島,遺世獨立的活著。 就像電影《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中的薩曼莎,她臉上有個紅色胎記,當她和伍茲在現實中相遇,她有意的用瀏海遮蓋胎記。 伍茲告訴薩曼莎,他並不在意她臉上的胎記,對她的感受從未改變。 乍看好像是伍茲在引領薩曼莎接納自己,但我們不要忘記,在他這麼做之前,是薩曼莎題醒他,「走出虛擬世界,直面真實生活」。 促使伍茲不再逃進虛擬世界,麻木自己的感受,兩人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建立真實的連結。 因此當我們欠缺安全感,我們需要回到自身去尋找,但我們依舊需要與外部保持連結,只是我們需要與那些不好的,壓榨我們的,把我們採取暴力的連結切斷。 換成互相尊重,彼此能夠健康的信賴、依靠的對象,如此便能在互動中,增進雙方的安全感。 傳統的依戀理論,好像孩子的安全感都來自父母。實際上,父母的安全感也來自孩子。 所以健康的親子關係不只是父母照看孩子,孩子只需要被動的被關注。健康的親子關係,如同其他關係,是雙方互相真誠關注的結果。 相反地,某些父母無法割斷對孩子的掌控,造就媽寶,需要父母自己去探問內心安全感的缺失,何以無法接受孩子的獨立,甚至害怕被孩子遺棄。 有些父母被孩子施暴,往往就在於他們反過來在老年時依賴孩子,無法獨立。 健康的親子關係,孩子離家,父母仍能很好的過自己的日子。這不意味著親子斷了連結,而是大家各自都有信心過好自己的生活,同時也相信對方能夠妥善的照顧自己。 ◎結語:吶喊!讓我們都聽見你 最後,如同弗雷德所說,當我們深陷不安全感之中,甚至出現盲視的被害者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揭露」這個真相,她引述治療師舒馬赫(William Schumacher)的話:
当我在诊所看到病人的时候,我才知道揭露创伤具有的治愈作用有多大,这让我异常震惊。我有一些病人通过揭露创伤,突然减轻了不少痛苦。
我們越是不想承認,我們就越會避開要處理的問題,同時也使自己與解救不安與恐懼的對象越來越遠。無疑地,那象徵著對自己的逃離,逃離真實的我們,逃離有希望的我們,以至於有天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我們其實有選擇保護自己的能力。 就像伍茲、薇斯洛卡、張竟生、魏則西、紅黃藍、“Me too”運動等人物與事件,當你在無能為力的時候吶喊,你會發現,你並不是活在傷痛中的唯一一人。 這時,我們就有機會看見內心的光明處,始終都有一塊應許之地,不假外求。
|
|
| ( 休閒生活|影視戲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