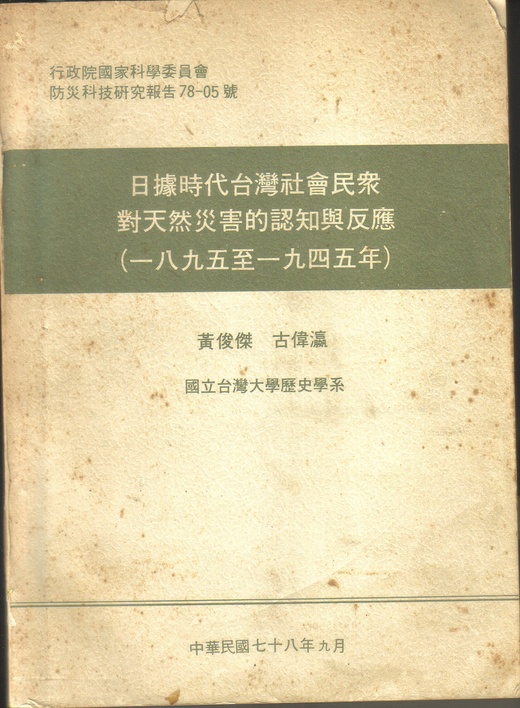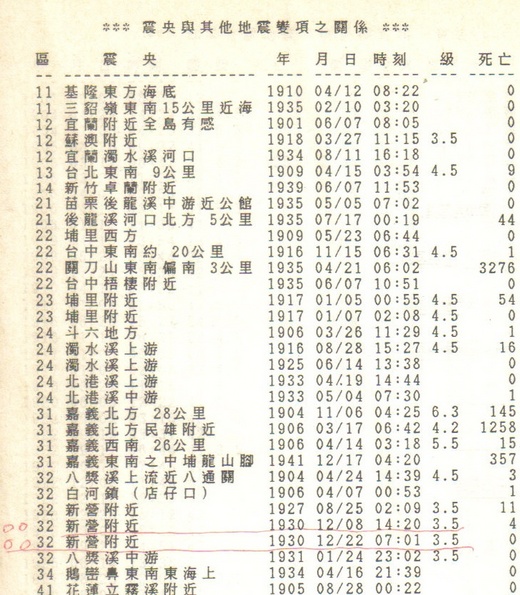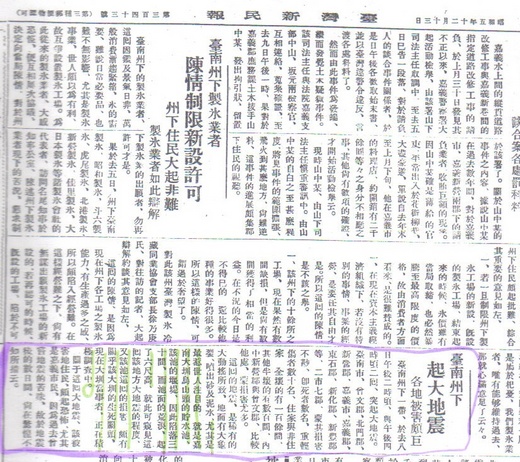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07/11 17:31:21瀏覽3131|回應9|推薦43 | |
剖讀 日本教育家古川的「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 泥人對於「八田神話」的研究,過去揭發了它的各方面;現在本文將針對日本人古川勝三的大著「『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一書中,對於八田的吹捧與揄揚的技巧與本領── 這位在日本以「教育」為專業,已擁有中學校長身份的作者,到底寫出了怎樣的一本書?通常一位中學校長,已可以說是「教育家」了,由於「教育」通常與「學術」是密切相鄰的事業,所以,那是在社會裡讓人信賴的、相當崇高的身分;然而,相對於史實,他寫出的是怎樣的一本書呢?──在台灣中譯印行以來是各家崇拜、最權威的八田傳記‧‧‧ 以下,泥人就把自身的研究,區分為「成長背景──他人格的主幹」、「自我認同──真認同於我台灣農民嗎?」、「決心──兩種煽情的描寫」、「兩種責任感──「災難之下」與「面子之前」」等四部份來與我們理性的網友討論: 請先看古川書中的描寫八田成長背景時的那三段精彩說法: 成長背景──他人格的主幹。 「德川幕府時代結束,……八田四郎兵衛已經變成村內數一數二的大地主了。……加賀這個地方是真宗的王國,八田與一從小就是在家中舉行的『講』或『御座』之下長大的。……佛前人人平等,不分師徒,彼此同朋同行,這就是親鸞對信徒的呼籲。八田與一深受這個教導的影響,而這也是形成他人格的主幹。」 「八田與一就讀的一中的學生當中,或許因為也以來自同故鄉關係,自然也都對宗教抱持深度的關心,這也就成為該校校風的特徵。……也有這樣的事。八田與一的朋友當中有所謂部落出身者,八田與一經常和他一起玩耍,有時也會到部落吃飯再回家。家裡的人注意到這事提醒他時,『同樣是人,並無啥區別,若用怪異的眼光去看,任何人看起來也都會變得怪怪的。』他這樣回答,而不理會家人的叮嚀。這樣的性格終生不變。在殖民地的台灣,不論和漢人或原住民接觸時,他也是視為同族地交往。八田與一這種沒有種族歧視的個性正是受異民族尊敬的所在。」[1] 「八田與一全心投入嘉南大圳工程時常對部下提到「覺、哲、悟」,這些就是根據從西田所學的哲學,和從真宗所學再經由自身體驗而得的。在台灣的行動和思想可說充滿了宗教,然而那可能是在四高時代所得到的。」[2] 該三段描述,顯然是想由家庭背景、中學時代到大學時代的經歷來強調八田的與眾不同;然而,假設他所提供的情境都是史實,所能養成的「人格」真的就能排除日本社會傳統性的階級懸殊與種族歧視,並且落實在我們台灣先民身上 嗎? 首先,應該指出,佛法的「人人平等」,從來不是「現世的平等」,是所謂「佛性的平等」,人人有佛性,是指有著來生成為佛的機會;也就是說,日本那以「和尚可以娶妻、生子、食肉」而著名的「真宗」,雖然有此類特殊的親民作風,但是,在現世還是尊重社會既有的權威和秩序的;所以,既使真有了真宗的信仰作為其「人格的主幹」,在種族歧視的現實問題上,並非就一定會有與眾不同的某些表現。 其次,引文中我們可看到,雖然他的家庭常在地方上舉行該宗派的「『講』或『御座』」,但是當我們讀到八田的朋友中有社會地位低賤的部落民,「經常和他一起玩耍,有時也會到部落吃飯再回家。家裡的人注意到這事提醒他」時,我們知道他的家庭並不同意他與日本賤民親近;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他來到台灣時,他可能怎樣看待我們台灣先民──當時,就所知,日本報刊上稱我台人為「土著」或「土人」,是比日本賤民地位更低的,受到日軍大量殺戮攘逐而竟然不肯離開島嶼,以致破壞了他們移民計畫的「被征服者」──「清國奴」啊。 知道麼?有一位當年曾經積極參與大圳建設時期的台灣長者,是當年罕有的工地小主管廖欽福先生,在其回憶錄中,他完全沒有直接提起自身對於八田的印象,我們只見到他說「當時日本人是會歧視台灣人的,但因為推薦我的土肥老師背景好,加上我有桃園大圳工作的經驗,工作又很認真……我的直屬上司就很看重我,……我一提到我是土肥老師的學生,他不僅不敢欺負我,而且還很照顧我。」〈該書頁44~47〉」;這樣的回憶,是否也讓我們有理由充分懷疑八田先生當年真的如今天的日人古川所言,那麼地對於我們台灣先民實踐著一種「現世的平等觀」? 自我認同──真認同於我台灣農民嗎? 其次,倘若八田真的擁有了那樣「人格的主幹」之後,古川又強調八田來到台灣後認同於我台灣農民:然後,這位大地主的兒子就由於自視為農家子弟,於是就設想出了那在古川口中說來極為好聽的、似乎八田自以為理想的「三年輪作」的灌溉方式: 「這不是技術員的觀點,而是我個人的想法。因為這兩個水源每年可供水的面積最多近七萬甲,因此這七萬甲可以收割稻米。而這以外沒水灌溉的地方仍是不毛之地,別說米連甘蔗及雜糧都收成不好,……如果這樣的話,有水灌溉的農民的收入將增加而變得富裕,……其他農民則永遠……不能脫離貧困。」[3] 「我是農家子弟,我認為再沒有比住在怎樣耕作都不能收穫的土地的農民更慘的。因此我考慮將嘉南平原分為兩三個區域,每兩年輪流給水,讓全嘉南農民都可平等受到水的恩惠。……他由技術者變為農民,他站在農民的立場考量。絕大多數的技術者認為土木技術只造水庫及水路,讓農民有水就好了。如何使用是別人的事,並不是土木技術者的責任。……但八田與一不以為然,儘管建造了一個很好的灌溉設施,但如果沒有適當地使用,便失去了意義。……總而言之,灌溉工程是為了農民而造,並非為總督府或技術者。八田與一如此想。」 「大家所講的都有道理。但是這樣的狀態繼續下去的話,對台灣的將來絕對不好。請你們想想這是放棄醭耕至而讓農民知道近代農耕法的好機會。雖然改革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是…除此以外,沒有開發嘉南平原的方法了。」[4] 這是多麼漂亮的說辭!好像一齣頌揚英雄偉業的浪漫主義的電影情節一樣!然而,那是真實的故事麼?除了在建造大圳之中,在1925年的「台灣民報」上,就曾有強烈憤怒的批判,表示了對於該制度的批判── 「三年輪作的內幕……我們要分三種來說吧:第一、這個組合的補助金1,200萬圓,不消說需要經過帝國議會的協贊才行。所以灌溉的地面愈大,即四千萬圓以上的大工事費,較容易得著議會的承認……第二、因為這工事費很大,對五萬甲土地的業主們要徵收著年年的組合費,他們一定是負擔不起,故使15萬甲土地的業主來負擔較為容易。第三、若把五萬甲的土地一旦變做水田,即那灌溉區域裡的製糖會社們一定極力反對起來,去阻止組合成立。……有些人說過,三年輪作的計畫,不過是製糖會社們和組合的倡首者們預先妥協的條件吧。我們也確信第三的理由是頂重要的。」[5] 不僅於此的,當年的日本學者在檢討官方的台灣殖民地政策時,也指出 「各種作物以50甲為一單位,從事集體耕作,以150甲為一輪作區。唯此輪作區,既非強制的,也非自由放任的,而是在嘉南大圳組合的『指導』之下,從事集體輪作。……故此計畫變成蔗作為中心。」 更重要的是,直到工程完工後,我們先民仍有下列的種種怨訴── 「會社與嘉南大圳互相連絡……大正九年編入嘉南大圳區域……一般農民明知甘蔗之無利,…無奈受嘉南大圳之強制輪作法,三年播種一次水稻,想此農民救死猶恐不足、奚暇治禮義哉……嘉南大圳雖曰成功,而給水溝及排水溝,俱不完全。農民朝開溝暮築堤,每甲之園地歷年負擔工作將近十餘圓之數,徒負種種義務……若嘉南大圳使用人員雖眾,朝三暮四,酒囊飲袋,妄自指導,空費民力、損害國土,設計未備……又兼虐細民,且貪圖賄賂……嗚呼無知小民,設此慘景,無殊啞子食黃蓮,苦在心頭……此小農民之苦況十也。」[6] 「利用岡山郡的二層行溪灌溉兩萬甲的看天田之計畫,是今日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所提出,據傳是由過去八田技師所計畫作成;目下只需1,200萬圓的工事費中的600萬元……引起岡山郡下地主與農民的注目。……由於恐懼強制三年輪作之不利……地主與農民表示絕對反對。……不希望該計畫成為第二個嘉南大圳。」[7] 換言之,這就是他所謂的「我是農家子弟」,落實後的具體表現;相對於日本傳統對於農民所採取的所謂「不可讓他吃飽,也不能讓他餓死」政策[8]與其學者所主張的所謂── 「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9] 「無人如農民既無管制又無體統,至米秋濫食米,至麥秋濫食麥,曾無留種以納年貢之意圖。」[10]; 是否八田與一先生這樣的理想,可能真是已實現了,但是這樣的「認同」,對我們台灣農民言,是多麼殘酷的「認同」啊?──正是這樣的認同,遂使得我們日據下五十年,果然台灣各方面產業成績進步了,但是我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不僅沒有增加──據資料所見,五十年間,我台先民最高壽的年代是1908年,死者平均為27.2歲,然後一路盤旋下降,稍有起伏,到產業進步的1939年與1940年,該平均死亡年齡竟然也只有22.7歲與22.9歲!──這真的是我們應該接受的,八田式的「台灣農民認同」麼? 決心──兩種煽情的描寫 這裡我們要看的,是該書中,還有多麼美妙,不顧現實的構思,完成了如下煽情的兩種「決心」故事: 「八田與一……有一天,……因忘了給水壺加水遂進到簡陋的農家要水。結果農民說,『現在沒水,請你等到中午汲水的人回來好嗎?』『到哪兒汲水?』『到曾文溪要四、五個小時。』『沒有水井嗎?』『有水井,但現在是乾旱……八田與一對嘉南農民……更加堅定了非給嘉南平原送水不可的信念。調查、設計、作預算雖然艱苦,但有夢想的工作令人期待……嘉南平原在已完成的厚厚的計畫書和圖面中間開始呼吸著。』[11] 「不得不解雇半數員工……八田與一思考後決定了退職的人選,然後由各股長傳達。股長們看到退職名單後,不約而同地發出驚訝的聲音,於是詢問八田與一:『退職名單中有相當能幹的人,以工地的立場來講,寧可裁掉這以外的人會比較好。』 靜靜聆聽的八田與一說:『我也考慮了許多』,確實想要留住有能力的人。但有能力的人可能很快就在別處上班,而沒能力的人在就業是相當困難的。……八田與一的聲音變得哽咽。滿眼含淚,淚流雙頰……八田與一位退職人員找工作奔走。而且找到能出比烏山頭出張所高的薪水時便幫他們介紹……」[12] 前者的煽情語是所謂「更加堅定了非給嘉南平原送水不可的信念」,後者的煽情描寫是那面對東京大地震後的大蕭條,組織必須裁員時,八田堅持其主見的那段所謂的「八田與一的聲音變得哽咽。滿眼含淚,淚流雙頰……八田與一為退職人員找工作奔走。而且找到能出比烏山頭出張所高的薪水時便幫他們介紹」;然而,相對的,史實是什麼──真的有那需要走到四、五小時的行程外取水的事實麼?他的嘉南大圳所能夠輸送的總水量,真能滿足十五萬甲土地的需要麼?史實是供水量極為不足,雖寫出好聽的所謂「非給嘉南平原送水不可的信念」,又能如何,過分強調渠道無所不至,只造成其無限地延長,只是增加了農民因渠道坡度平緩所造成的淤積、滲漏與在地震帶維護整修不及的嚴重負擔吧。至於,那竟然先裁掉優秀技術員的問題;我們不免質疑,用它在要求善待技術員時的話來責問他──如果如他當初所主張的「優秀的技術員能縮短工程,節省工程費。由此節省下來的工程費應該抵得上技術員薪水的幾十倍。」[13];那麼被他裁掉的眾多優秀技術員,對於大圳的工程是否一大損失〈如所稱,「解雇半數員工」〉?甚至,請問大圳後來出現的種種問題,是否與他裁掉了眾多優秀技術員有關?竟可以這樣對待我們台灣人的重大工程──而這種對於設計與監造者的縱容,也就讓我們不能不想到當年日本稍有財政專業的學者都以「不顧經費的經濟使用,從事過大不急之務」[14]、「台灣以財政支出來維持的事業,比較台灣的人口及其密度,是否過分,仍多疑問」[15]、「在殖民地,或是根據殖民者的官吏與資本家的要求,或為誇示國家的威嚴起見,……常有超過原住者經濟的設施而支出了鉅額的財政」[16]之類論述批判其當局,而被笑稱其為「台灣之所以為台灣」[17]的理由!? 兩種責任感──「災難之下」與「面子之前」 前面我們已談過了古川筆下八田的「人格主幹」與其對於我們台灣農民的「自我認同」,也探索過它筆下那大力煽情的「決心」,不知讀者是否已逐漸感受到其中與史實的巨大落差;真是頗為讓人失望啊。 現在讓我們看對於任何人的為人處世都很重要的一項問題,那就是在責任感上的表現,八田如何──請看下面的兩個例子── 「八田與一趕到工地雖然火已撲滅了,但從隧道內已運出五十具屍體,以及數名受重傷的人在呻吟。…大倉土木組的負責人歉疚地向八田與一做了說明。……『過去曾經冒出石油嗎?八田與一表情嚴肅地質問。『曾經有石油冒出來,可是不至於出事,還能夠往前挖。有些工人將石油帶回去,那跟精煉的石油沒兩樣,還開玩笑地說是否有油田?』八田與一聽完後大聲說:『為什麼當時不馬上報告,讓我知道的話,可以防止事故的……』如此罵著,但太遲了。』[18] 「在總督府聽到出乎意料的消息。據說已經邀請美國半水成填充式土堰堤權威賈斯丁到烏山頭堰堤實地調查。八田與一憤怒極了。……『有需要嗎?是不是不信任我的設計?』接著又繼續說:『賈斯丁的論文我已全部讀過,而且也實地參觀過他所設計的土堰堤,這才設計出符合烏山頭堰堤。』……不少技術員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是可預見的。……總督府開始說服八田與一。『不是不相信你的設計。……但總督府內有著種種的聲音。……這樣做對你也是有利的。』賈斯丁……調查費時三個月,以英文寫成……意見書中除對烏山頭土質合乎半水成填充式工法堰堤表示大大認同外,接著全面批判八田與一的設計。……八田與一成了日本土木界向美國土木界的挑戰者。……為了日本土木界絕不能讓步!……總督府決定檢討兩人那厚厚的論文,同時聽取他們的意見。……總督府數次檢討的結果,終於決定照八田與一的設計實施。然而賈斯丁也不服輸。『既然總督府決定按照八田技師的設計實施,我不表示意見,不過……水庫完成後,到底滲透量到什麼程度,請將結果每年向美國土木協會報告。如果滲透量沒超過我的預料時,我才認同八田技師的設計是正確的。如果八田技師的設計正確,最起碼今後半水成填充式工法的設計要更改了,而且八田技師可能留名世界土木界。……總督府和八田與一都爽快地答應賈斯汀的要求。……水庫完成後,……每年都寄報告到美國土木學會。當然,報告書上所記載的滲透量是遠不及賈斯丁所預料的。……八田與一終於獲勝了。……此後,不在有人對八田與一的設計提出批判和疑慮了。因為它已受到很高的評價。……』[19] 各位是否感覺到了八田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真應該得到如古川所給他的那樣很高的評價麼? 由前段引文,那是八田面對著那場五十人當場犧牲的重大災變,我們看他的責任感,竟然沒有看到其自責──如果他曾經對於第一線隧道工人做職前訓練,工人們怎會挖到石油時竟然毫無警覺心而只知玩笑呢,看那工頭所說,「有些工人將石油帶回去,那跟精煉的石油沒兩樣,還開玩笑地說是否有油田?」;真是多麼不必要的悲劇?看古川書中,我們沒看到八田的自責,卻只會罵那位與工人一樣無知的工頭!──這是怎樣的責任感的表現? 由後段引文,那是古川先生顯然津津樂道的,似乎反映著日本戰後五十多年在美國壓抑下的一段自慰;然而,那是關係著嘉南平原上我台灣先民生命與財產的大工程,竟然以空洞的所謂「為了日本土木界絕不能讓步!」的面子問題,作為堅持己見,拒絕美國權威意見的主要理由?這樣的八田與一,如果嘉南大圳工程所關聯的,不是我們被其賤視如草芥的台灣先民,而是廣大的日本農民,他也會以這樣「要面子」的方式來負責麼? 總之,我們台灣先民是不幸的,當甲午戰後李鴻章發出他那痛苦的告白信之時,他不可能想到,所謂「同文同種」的東洋人是怎樣的思考著;雖然他寫出自己的考慮──「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者取輕,實出萬不得已‧」──但是,他已經鑄下了大錯,因為日本陰謀裡竟預計在兩年的國籍自由選擇期內,把所有台灣居民用殺戮的方式驅逐出境,所以,真是那樣地看不起我們台灣人啊! 而更不幸的,則是我們社會中少數看不起自己的同胞,竟然會被古川這樣的作家所欺騙;上引古川筆下白紙黑字的資料,所粉飾的英雄圖像雖然巧妙,如果我們真的有心仔細去尋索其邏輯的破綻,以史實去印證其虛構,我們傳統諺語所謂,「鴨蛋密密也有縫」,怎會查不出其蹊蹺呢? 最後,本文就以1930年的一項重大史實來看,那是絕對不利於八田神話的事件,由它為何不見於古川先生的大作呢?開始發問── 請稍回憶前文末,八田以「為了日本土木界絕不能讓步!」的面子問題堅持己見時,古川筆下所大力描寫的、精采的勝利的那段──所謂「然而賈斯丁也不服輸。『既然總督府決定按照八田技師的設計實施,我不表示意見,不過……然而賈斯丁也不服輸。『既然總督府決定按照八田技師的設計實施,我不表示意見,不過……水庫完成後,到底滲透量到什麼程度,請將結果每年向美國土木協會報告。如果滲透量沒超過我的預料時,我才認同八田技師的設計是正確的。如果八田技師的設計正確,最起碼今後半水成填充式工法的設計要更改了,而且八田技師可能留名世界土木界。……總督府和八田與一都爽快地答應賈斯汀的要求。……水庫完成後,……每年都寄報告到美國土木學會。當然,報告書上所記載的滲透量是遠不及賈斯丁所預料的。……八田與一終於獲勝了。……此後,不在有人對八田與一的設計提出批判和疑慮了。因為它已受到很高的評價。……』 然而,如果我們願意接受史實的印證,試著查一下資料,想想看,賈斯丁接到的報告書如果是秉筆直書的──那就是在嘉南大圳完工通水的半年內,台南地區發生根據當年紀錄兩次震度不大的地震〈見於附圖〉,第一次烏山頭水庫就被震崩壞了三百六十尺,下游麻豆郡下數十甲淹水如漁塭〈見當年報導〉;已升官進總督府的八田趕緊南下修補維護,不料,同月,又有規模相同的地震,烏山頭水庫又發生同樣的崩壞──請問,我們應該怎樣感受古川先生的這段勝利的精采描述── 其次,儘管,我們不知道嘉南大圳當局是如何向美國土木協會報告的,美國若真的因其捏造的數據或偽造的報告而改變了賈斯丁先生原本「半水成填充式工法的設計」
|
|
| ( 時事評論|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