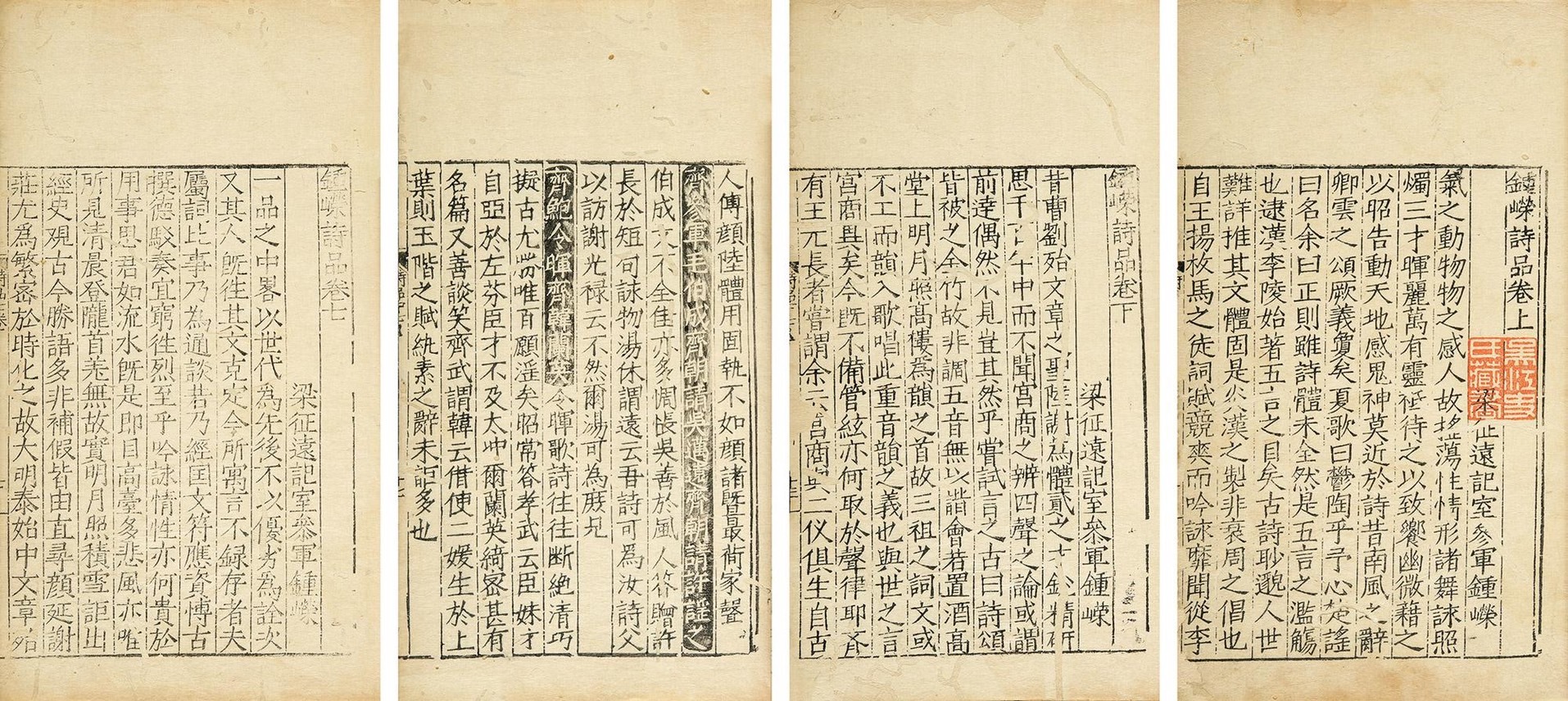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2/18 23:55:44瀏覽5544|回應0|推薦16 | |
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詩的發生 詩歌的發生,在鍾嶸以前的經典,如《虞書‧舜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禮記‧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 說明詩歌的發生,是由於人內在情感的抒發,是為表現情感而作 ;《詩大序》發揮此種看法: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從主觀自我感情發生,有情感後形之於言語,但是言語又不能完全呈現情感,故不免嗟歎詠歌,當語言詠歌都不能完全抒發情感之深蘊豐沛,則不免用手腳比劃、以舞蹈呈現。朱熹在《詩經傳序》裡引申這一段話: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按照他的看法,人類生來就有情感,表現情感最適當的方式便是詩歌,因為語言與心志相契合時,便形成一種內在與外在的自然音響節奏,只有以詩歌的方式才能表達出來,而這表達是一種「不能已」,亦即詩歌的出現不僅僅是自然,也是必然。 鍾嶸繼承了傳統經典的說法,也在《詩品‧序》中提出自己的意見: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他認為:詩歌的發生,首先是由外界客體的「氣」,讓客體的「物」發生變化,而作為主體之人心,內在「性情」 搖蕩是對於客體外物的感應作用,故詩的發生是根源於人的「性情」,同時也根源於天地自然的「氣」。 人的「性情」受到刺激感動,因此「形諸舞詠」即為個人主體對於自然客體的投射;亦是個人對自然生命的一種感動、觀照及覺悟 。由「氣之動物」、「物之感人」以至「搖蕩性情」,可以說是「氣」、「物」、「人」三者推衍出詩歌來;詩歌的產生既然是由於人們性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召和激發,則詩歌的本質是心物感應下發自於性情的產物 。 鍾嶸不同於傳統說法的是,他在主體的性情之外,更強調了客體的「物之感人」,這一點同於《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音樂的產生,是由「物」感於「心」,而感於客體之物的「心」;人的「性情」表達哀樂喜怒情緒時,投射於外,便成為「聲音。 所以假如《詩大序》以下,對詩歌發生的論述偏重在人心主觀自我「主動」的部份,鍾嶸則是兼重「主動」與「被動」,「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提出更精闢的論述。 另外,「氣」字是中國文學批評中最為習用的一個批評術語,鍾嶸此處則是取用類似漢代以來「元氣」的義涵,代表天地間蓬勃的元氣,生發萬物,萌動自然,把「氣」引進詩歌理論,是鍾嶸個人特別的運用創造 。 不過鍾嶸的說法,主要是針對創作時的心理反應而言,而並非討論「詩歌是如何出現」的問題,這也是他繼承傳統經典卻採取不同角度的地方。 鍾嶸的思想並非創見,因為緣情感物,傷時歎逝原是魏、晉以來文藝思潮的主流,一般批評者將此一性質認為是文學的特性,鍾嶸卻以之作為詩的特性。 陸機的〈文賦〉即首先標舉「詩緣情」的說法:「詩緣情而綺靡。」詩何以緣於情?人的情感經由對萬物的感受體驗,引起自覺領會,發而為文學創作,即為感物興情的作用: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陸機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遵四時」、「瞻萬物」所生的「歎逝」、「思紛」,說明情感的引發有賴於客觀事物的感召,悲喜之情即是創作的根源,亦即「詩緣情」的說解。 劉勰說詩的產生是「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同於陸機。感物興情是一切文學的根源,凡人皆具內在的性情來感物。《文心雕龍‧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春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劉勰這段文字與鍾嶸《詩品‧序》主旨類似。由大自然生命與個人生命之相互律動關係上,解釋文學的本質。 蕭子顯〈自序〉說:「追尋平生,頗好辭藻,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 他從個人創作經驗中也獲得同樣體認。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由感物興情以至性情搖蕩而表現於文學或詩,即是文學或詩產生的原因,此種思潮產生於魏、晉而成熟於齊、梁 ;鍾嶸的思想也是追隨著時代的步調。 鍾嶸「氣之動物,物之感人」的說法,在《詩品‧序》後文又做了補充:「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此段補充了「物之感人」的實際條件。 「氣之動物」,指四季及四季景物的種種變化形象與精神,就是自然生命的展示。在傳統觀念中,四季變化不僅代表自然生命的盛衰,更展示出自然喜怒哀樂的感動;詩人的生命及性情感於種種客體生命與性情之展示及活動,反照投射、激蕩而為詩的內涵,故自然物色的生命現象便不止是詩的素材,更常伴隨詩的精神主體而同時存在於詩境之中,亦即「物之感人」, 。 如果鍾嶸的緣情感物說是當時文論家的共識,與陸機、劉勰等人並無不同,純粹只是繼承與因襲關係,則提出「人際感蕩」,強調社會生活是詩歌創作的另一大根源,此是鍾嶸的獨創: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此段認為,在四季變化、自然盛衰感諸於詩者之外,社會動蕩、人際悲歡離合,同樣是詩歌發生的原因,甚至是更複雜、更令人魂魄迴蕩、愁思百結之所在。 在這裏,鍾嶸用了許多對句,囊括了歷史上屈原見讒、昭君出塞、去國懷鄉、生離死別等有代表性的例子;但鍾嶸對這些歷史人物的遭遇並非要作一番具體的論述,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這些人物組成的歷史悲劇和社會動蕩上,闡發由社會悲劇而使詩人情感豐富、內心激蕩、靈魂悸動,因此充滿了傾訴的渴望,最後不得不陳詩展義、長歌騁情的過程。 因此,「楚臣」可以是屈原,也可以是楚國甚至任何一個失意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人;「漢妾」同樣可以是王昭君,也可以是班婕好,也可以是其他並不知名的一個可憐的宮女;「再盼傾國」可以是李夫人,也可以是其他人。總之,鍾嶸在這裡想概括的,祇是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典型感情,從而證明歷史悲劇和社會感蕩是詩歌發生的另一大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六朝文論家都論述過詩歌的發生問題,注意到陰陽盛衰、四季變化與詩歌的關係,並作了許多有詩意的闡發,讓人瞭解自然景物不僅使詩成為有色彩作布景、有天籟作音響效果的田園樂章,還能感蕩人心,作為創作的內驅動力,這是「文學自覺」詩學發展歷史時期在詩歌理論上的一大貢獻。但無論是陸機、蕭子顯,還是蕭統、劉勰,都還沒有發現社會悲劇、歷史感蕩人心的另一個驅動力。 特別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五十篇中幾乎包羅萬象,決定要說清楚所有的文藝理論問題,他在〈時序〉中甚至談了時代、政治與文學的關係,說明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以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的道理,但是他對詩歌發生論的闡述,除了提出當時共識的自然感蕩以外,祇補充了「采風」需要和「言志」需要的論點,而這依舊是沿襲《詩大序》的說法 。 所以,提出種種「感蕩心靈」的人生際遇,社會客體的現象投射反映在詩的精神主體,強調社會生活是詩歌創作的另一大根源,這是鍾嶸獨到的創見。 自社會的基礎上認定詩的情性表現依附於人生現實,並以人生現象為素材的見解,是中國批評史上最古老最傳統的思想。如《禮記‧樂記》及《毛詩序》所謂「情動言形」,從政和、政乖、亡國的關鍵上解釋詩歌所涵攝的情感,分別以「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的不同面貌呈現 ,皆是從人生社會的「政治」層面說明情動言形的因由;漢人將這一見解推及於論賦,如劉安、司馬遷、班固、王逸等論屈原之作〈離騷〉,均從人生現實上解釋遭讒被逐,而有「憂愁幽思」 、「憂悲愁思」 的產品;司馬遷且進一步說:「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積,不得通其道也」 。 劉勰在〈明詩〉稱九德、五子之歌為「順美匡惡」,又稱「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等等,都是由政治的良窳上說明「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知此一層詩義,本是傳統知識份子以政教關懷的詩觀,立基於積極關懷人文世界的精神,而視詩為社會文化時空中的產物,詩是被動的反映或主觀的批評當時的社會文化現象,在此觀點下,感物的「物」實指政教現象,興情的「情」亦屬政教之情;但這個思想到了鍾嶸,卻完全不從政治上解釋情動言形。 鍾嶸雖然從社會的立場認知詩歌感應的效果,卻是遠離政教說 ,這是鍾嶸獨到的眼光,「物」既非政教現象,而「情」則是個人情懷,將詩歌脫離政治教化的束縛,只為作者而服務,只為讀者而服務,亦即只為文學而服務。 鍾嶸所謂「搖蕩性情」的見解,在西洋批評家中頗有相同的論調,法國近代詩人梵樂希(P.A.Valery)說: 詩之情緒,乃是情緒中最主要的部份。當人們遇到一種易起感觸的自然景色的時候,我們會知道他們有如何的感想。夕陽、月光、鬱鬱森林、茫茫大海,常給我們一種深沉悠遠的感思;重大的事件─我們情感生活急劇的轉變,如愛的失望,死的來臨等等─常能使我們心靈深處立刻起了響應,不論是急劇地或舒緩地、知覺地或不知覺地。 梵樂希以為這種感動的情緒與人類其他情緒不同,雖然其中仍不免夾雜著憐恤、悲哀、憤怒、恐怖、希望等別種感情,但這類感情均不能去侵犯詩情中的「一個宇宙的覺識」,這「一個宇宙的覺識」,便是詩的分野。 總觀鍾嶸的詩歌發生論,他認為詩歌乃是心物交感的性情之作,是創作活動中主體性情對外界事物的感應,亦是個人對自然生命的一種感動、觀照及覺悟;而其所謂的「物」,不單指自然的時節景物,而是兼有自然的時節景物與人事的生活遭遇,尤其後者感蕩心靈更加深刻;這樣的見解,較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把文學應該反應的社會現象,僅僅局限在「郁郁盛德」或「赫赫功業」上,鍾嶸的視野無疑是更為廣闊 。另外,他把「氣」引進詩歌理論,提出種種「感蕩心靈」的人生際遇是詩歌創作的另一大根源,以及將人生際遇、社會經歷脫離傳統的政治教化層面,此皆是鍾嶸個人獨到的創見。 二、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的創作 (一)論「興」、「比」、「賦」 在《詩大序》首揭「六義」之前,《周禮‧春官‧大師》即有「六詩」之文 ,六詩的序列是:「風、賦、比、興、雅、頌」,六義次序相同。據六詩平列來看,可能為古代的六種樂歌。 漢代傳注,對於六詩或六義均予平列解釋,並未明顯劃分「詩體、詩法」兩組,如東漢鄭玄解釋為:「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兩漢大抵是附著在「六義」或「六詩」的詁訓,並以政教關懷的立場決定六義的性質;但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已分別加入了詩的文學意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孔穎達將三義解釋為詩之用,是取用了魏、晉以後批評者對三義的文藝見解,自此六義分為「詩體」、「詩法」兩組後,說法底定,再無異辭。 鍾嶸並未依據三義原有的序列,而將「興」置於「比」、「賦」之前,一方面見到他對詩的藝術性的強調;一方面三義也從詩經中脫立出來,將舊有的詩學語詞,賦予了新的涵義,成了五言詩的語言: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鍾嶸明言「詩有三義」,在《詩品》中,他所論的是五言詩,不是《詩經》,故略去風、雅、頌,而專論賦、比、興。賦、比、興不只是《詩經》的表現技法,也是一切詩共通的表現技法,故鍾嶸以三義為詩之所用,不僅提到「宏斯三義,酌而用之」,而且提到專用比興與賦的弊病,故三義皆為表現層面,三者是同層的修辭法。 鍾嶸說「興」是「文已盡而意有餘」,此說法幾乎已脫離詁訓傳統之外,不僅字面與以往解釋均無雷同之處,而且亦不涉及「譬喻」及「感物興情」的通義,此即足以看出鍾嶸解釋之「新」。 鍾嶸以「興」為表現技法,若能使詩的語言具有回蕩的餘意,可以在含蓄中激發情性的反照覺識,便是詩興的極致,則興還是以象表出,由此可判定「文已盡」之「文」,當為「興象之語」的意思。「文」意、「言」意、「語」意對舉,在古人並無區別,因此「文已盡而意有餘」,亦可說成「言已盡而意有餘」或「語已盡而意有餘」,但依鍾嶸之意,這「文」(「言」、「語」)是特指「興象之語」而言,不能泛說為「詩的語言構造」。 鍾嶸既主感物緣情之說,又特別強調「直尋」之義(所謂「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興的表現即都具有這些特性,興象之語常為直尋所得的象;興象之語是有限的文字,卻隱示涵附於景的悲喜無限之情意,「文已盡而意有餘」便是點明興的美感情趣或美學價值,鍾嶸的新解便「新」在此處。這不是正面地由作用上去解釋興之為義,或由方法上解釋興之為巧,而是側面的從興的表現當身所具的美感情趣說興,由此轉出一個興的層面,不是經驗層面,也不是表現層面,而是藝術價值層面,能使人由文字表層進入情意深層,感受到語窮意遠的無限滋味,而不使意盡於象,象止於言,這是興的表現積極顯示的情趣與價值。 「興」是「文已盡而意無窮」的說法,轉出值得注意的新展向,此一新展向認為:語文構造的表現必須具有美感情趣的特質,亦即必須「意在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而以語文構造表現本身之富涵美感情趣的特質為興,亦以此作為詩之美學基準。 鍾嶸對「興」所作的新解,發展而下有司空圖的「韻外之致」、嚴羽的「興趣」說、王漁洋的「神韻」說為代表,開啟後世「象外」、「言外」之詩論,在中國詩論上形成了創新的發現與開拓,即今人稱之為「美感境界」的詩論。故傳統興義的發展轉向美感境界的詩論,其關鍵即在於鍾嶸。 鍾嶸釋「比」是「因物喻志」,一方面看重比的「喻」的方法;一方面也看重「喻志」的效用。由「喻志」的效用上看,他所謂的喻顯然與傳統的解釋有頗大的差異,那就是:揚棄了形貌比喻的比義,而強調譬喻在表達內心的活動。 「因物喻志」的比,可以包容明、隱兩種比喻之義,鍾嶸既然要從文學傳統中獨立出來,選擇五言詩作為詩藝術的極致,則在詩的語言藝術方面,也抦棄部份傳統觀念,而予以新的準則,故比興的涵義在古典名稱之下有了新的解釋及新的順序,比因此不以喻聲、方貌、譬事為其職責,比要達成「喻志」的大效用。 由比興的意義,可以看出鍾嶸異常強調詩的語言構造的濃縮、含蓄,經由「指事」、「寫物」而造形託意的間接表達,但濃縮含蓄及造形託意全須經由聯想、推想、想象之心理活動,又復經由經驗、知識及心靈意識的觸悟,作者的表現與讀者的觸識之間稍有偏差,則詩的語言便失去完成創作的目的,所以鍾嶸以為比興的運用以適度為限,專用比興,「意深」、「詞躓」,晦澀不明,失去鮮明活潑的詩情詩境,也並非詩的極則。 鍾嶸釋賦為「直書其事,寓言寫物。」此亦包涵兩層意義:從手法上說賦是直接描述事物之情景或形貌;由效用而言則一切事物之描述之目的皆在「寓言」,換言之,從描述的語言中寄託詩人的心意。因此,賦並非比,但賦也有言外之意,也可以完成「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興的功能。 故知鍾嶸給予賦的職司,純粹是詩的藝術性能。另外,以「直書」的手法描寫事物的語言構造要想達到有所寓託,仍需從詩的語言特性上要求它能濃縮、精切,使之「言已盡而意無窮」,不可率然直書,任意寫物,否則詩之語言便失卻興寓詩情的作用,漫然無所旨歸,因此提出專用賦體則有「意浮」、「文散」、「文無止泊」的「蕪漫之累」 。 明瞭上述三義之後,鍾嶸尚提出「幹之以風力」;關於「風力」的涵義鍾嶸並未予以文字的解釋,葉嘉瑩說「風力」是:「由心靈中感發而出的力量以支持振起詩歌之表達效果。」可備一說,另外,可由鍾嶸文章來觀察: 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曹植) 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劉楨) 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劉琨) 協左思風力。(陶潛)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詩品序》) 建安文學及詩的風力,是一種動人的慷慨的感情活力,此種活力,如劉勰的所論:「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明詩〉)。又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序〉)。鐘嶸所舉曹植、劉楨是最好的例子。 曹植詩「骨氣奇高」,能以奇卓的語言結構展示感情的高昂活力,完成了詩的生命活力,他的詩即是卓出的詩,具有由心靈感發的力量,故能感動人心。至於劉楨,他以真樸自然的語言,展示出不落凡俗的情趣活力,因此他的詩是「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也正因為他的語言真樸明朗,所以不免「雕潤恨少」,以至「氣過其文」。 在鍾嶸眼中,「丹彩」的潤飾十分重要,劉楨之不及曹植「詞采華茂」,鍾嶸將他置居曹植之下可想而知。劉琨詩有「清拔之氣」,因其詩敘述喪亂,寄託他對國家及自身遭遇的感慨悲怨,以一種清朗嚴密的語言結構展示他不同於眾的深切感情活力,他的詩具有心靈感發的力量。 陶淵明有左思風力,鍾嶸在上品評左思:「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左思以樸素精鍊的文字,而能至切的表現他含蓄諷喻的悲怨感情,故有風力。而陶潛的「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正是以宛轉適恰的語言展示了真樸高古的感情,意味無窮,所以陶淵明的一部份詩具有與左思相同的情趣活力。可以看出,鍾嶸評詩亦以風力之有無強弱為分品的依據之一。 至於永嘉到江左的詩,由於「理過其辭」,沒有生動的意趣活力,這種文字典正而意趣平庸的格言詩,「淡乎寡味」,自然稱不上有「風力」。 鍾嶸認為詩的創作,必須內容與形式並重,所以在風力之外又特別提出:「潤之以丹彩。」丹彩指語言文字的美飾,語言文字的美飾,應該從語文的形、音、義三方面來衡量它的美學價值;而語文的美飾,就鑒賞及批評而言,有了雅俗、奇正、華實、文質等等的判別。 就鍾嶸的時代而言,不論創作與批評,皆重視語文的美飾,以文采華麗為主。換言之,當時以為美的,大抵是典雅的書寫的文字,亦即士人的語言。鍾嶸重視丹彩,大抵是同於當時的文學思潮而略持守中道的。 正由於鍾嶸重視詩的語言表現的美感作用,而語言的美感亦多以作者的主觀經驗及客觀條件為主,故鍾嶸以為詩的語言的美飾亦訴諸作者的天資;換言之,即作者對語文的美感活力。因此,能潤之以丹彩完成詩的語文的美的作家,大抵是才力高者。 所以曹植「詞采華茂」,就將他喻為「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粲溢今古,卓爾不羣」,文才天成,無與倫比。陸機之華美,也因於「才高」,「張公歎其大才」、「陸才如海」。潘岳辭麗,故稱「潘才如江」。張協也被稱為「曠代之高手」。至於謝靈運「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顏延之詩「綺密」,因他是「經綸文雅才」。鮑照詩「諔詭」而「靡嫚」,由於「才秀」,此例甚多。總之,鍾嶸以為才力是詩的語言美飾的原創力,而語言的美飾所造成的美感是詩的創作所需重視 。 由三義的解釋,可以看出鍾嶸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鍾嶸所論述內在情感與氣勢與外在文學藝術技巧結合的結構,如同蘇珊.朗格(S.Langer)所論述: 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藝術品的結構,你就愈加清楚地發現藝術結構與生命結構的相似之處,這裡所說的生命結構,包括著從低級生物的生命的結構到人類情感和人類本性這樣一些複雜的生命結構(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級的藝術所傳達的意義)。正是由於這兩種結構之間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畫,一支歌或一首詩與一件普通的事物區別開來─使它們看上去便是一種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用機械的方法製造出來的;使它的表現意義看上去像是直接包含在藝術品之中(這個意義就是我們自己的感性存在,也就是現實存在)。 鍾嶸或許沒有發現詩歌與生命結構的問題,但是他卻已意識到:由情感和人性所傳達的意義才是最高級的藝術。 透過興、比、賦三種表現技巧的斟酌運用,適切地表現內在情思,表達詩人動宕蘊孕於心的詩情詩境,使生命特質及觀照事物的獨特情感鮮明具禮的呈現於內容之中並尋求語言意象的藝術性,而造成詩的語言構造及表現藝術的極致精切,成就一個富含美感價值之統一完美的藝術結構。此即鍾嶸論「興、比、賦」在「詩的創作」中的涵意。 (二)論「直尋」與「自然英旨」 鍾嶸提出「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在此他明確地把有關國家大事的各種文書,記敘德行的各種文章,上給皇帝的各種書疏,都和「吟詠情性」的話區分開來,認為前者確實很需要博通故實,索經據典,也就是「用事」,後者則並不需要。 這樣一種區分是重要的,因為它指出了以「吟詠情性」為目的的純文學的作品和自古以來各種政治性、應用性的文章是不同的,這也是魏晉以來「文的自覺」的進一步發展。 故古今詩中的名句,都不是借用補綴典故得來的,「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而是直接地去尋求如何抒發表現詩人對外物的感受的結果。 「補假」與「直尋」是對立的,前者重視的是典故的應用,後者重視的則是詩人對外物的直接的感受。所謂「直尋」,也就是鍾嶸在評謝靈運時指出的「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直接抒寫詩人對外物的感受,而不假借已有的、現成的典故。 鍾嶸這種看法的重要意義,主要不在詩的寫作能否應用和如何應用典故的問題,而在他極大膽地強調了直感在藝術創造中的作用,可以說明確提出「直尋」的觀念,並把它提到首要的地位,始於鍾嶸。 故可以知道此句之精義即:世間最美的詩句,乃由人自然真實的感情所發出,那就是最偉大、最美妙的作品。故鍾嶸又批評了依靠羅織補綴典故來作詩的作法,「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中肯地提出了它發展到了「文章殆同書鈔」的境地,使文學失去了他所強調感人的力量。可見他是絕對反對完全用典故來作成一首詩。 另外,在鍾嶸看來,作詩重要的並不在「用事」是否「新」,而在「詞」是否「奇」。所謂「詞不貴奇,競須新事」,「貴奇」是鍾嶸詩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它表現在鍾嶸對許多詩人的評論中。但鍾嶸所說的「奇」是同他所說的「直尋」分不開的。 由「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只有直接地去抒寫自己對外物的感受,努力找到最為恰當新穎的表現,這才可能有詞的「奇」。鍾嶸在評任昉時說:「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評張華時說:「其體華艷,興托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評陸機時說:「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所以他所要求的「奇」,是基於「直尋」而得到的一種既新穎又自然的「奇」,也就是他所說的「直致之奇」。這種「奇」和典故的堆砌不能相容,也不是務求文詞的華麗或謹守文章的規矩所能做到,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天才的直感的產物。 鍾嶸所謂「自然英旨」,指的是出於自然的異常精美的詩句,它和那種「競須新事」,「拘攣補衲」而成的詩根本不同。顯然這種堪稱「自然英旨」的詩句,也就是鍾嶸所說的有「直致之奇」的詩句,兩者是一個東西。但「自然英旨」的說法更為明白地指出了鍾嶸所說的「直致之奇」是得之自然的直感,也同於「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最偉大、美妙的詩句出於人自然真實感情的作品。不僅如此,鍾嶸還由此指出了它與詩人的天才的關係。 能得「自然英旨」的詩人是極少的,許多人之所以靠堆砌典故來做詩,是因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這就是說,自已的筆下沒有「自然英旨」,於是就只好多用典故,雖然趕不上天才的詩人,也可以表明自已是有學問的。這裏更進一步說明了鍾嶸是推崇天才的,他所說的「直尋」、「直致之奇」、「自煞英旨」都與天才分不開。 在鍾嶸對各個詩人的評論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天才的推崇。如他在評潘岳時說:「陸(指陸機)才如海,潘才如江」;評謝靈運時說:「若人興多才高」;評謝瞻等五人時說:「才力苦弱」;評謝惠連時說:「小謝才思富捷」;評謝眺時:「意銳而才弱」;評惠休時說:「惠休淫靡,情過其才」。 此外,鍾嶸認為有「學問」和有沒有「天才」是不同的。有「學問」而無「天才」,雖然可以通過多用典故來表明自已有「學問」,但卻缺乏「直尋」的能力,寫不出能顯示「自然英旨」或有「直致之奇」的好詩。 鍾嶸是很重視「情」的,但如他所評的惠休的那樣「情過其才」,即有「情」而缺乏「才」,也同樣寫不出好詩。鍾嶸將「天才」與「直尋」相聯,又將它與「學」的多少區別開,這都是有深刻意義的觀點,認識到了藝術創造的特徵。重直感、重天才顯明地貫穿在鍾嶸的詩論之中。鍾嶸直接、鮮明地強調了藝術創造的主要特徵,他對直感的強調,對「天才」與「學問」和詩的創作關係的論述,都深化了對藝術創造特徵的認識,並對後來宋代嚴羽的話論產生了影響。 或有論者,以為鍾嶸「直尋」與「自然英旨」說,是一種不須讀書的論調,甚至類同禪語;殊不知文學表達中,有實語與虛語,虛實不定,相輔相成,鍾嶸曰:「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這是實語,是由前面所述「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清晨登隴首」而下的評論,是有根據而言;至於後面「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這卻是半虛半實之語,是一時主觀之感受,是鍾嶸在「爾來作者,寖以成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等弊病下所發的感慨,在他的創作過程中,書寫至此,因心神激盪,不免感歎,固雖非全無事實根據,亦是當下心境的一種反映;所以讀這一句不能讀死,必須活讀,知道他是在時代弊病中所發出的牢騷,尤其是「罕值其人」一句,並非是他所立下絕對不易的評論,後世論者不太需要以此評鍾嶸為「不重讀書」。 三、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詩的功效 天地、萬物以其生命的本質及現象對詩人作了某種感召,詩人因其生命的本質與性情產生相應的「搖蕩」,才有詩歌的產生,「形諸舞詠」。故所謂詩歌的效用本質即是自然和人的生命互相的感激發揚,互相投射觀照,詩歌的完成或創作,也即自然和人的生命完成或創作。 詩之「照燭」天地人,「煇麗」萬物,不僅由於投射觀照,溝通了自然與人的生命,並且由於詩本身的特性之一是以美化的語言完成,也因此美化光照了三才萬物之存在。詩「昭告」了「幽微」,才能「動」、「感」天地鬼神,鬼神之意義不必以宗教意識來認知,因為鬼神所代表的僅是三才萬有之形而上的部份,或指為精神主宰的意義。 如就社會人來看詩的第二層效用,則簡單而具體多了。《詩品‧序》說:「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以上的話可用「羣」、「怨」二義全部包容。 「嘉會寄詩以親」,解釋了「可以羣」,如金谷、蘭亭之會,固然「感可賦詩」,以展示嘉會所激生的人際親才之情;反之,即窮賤、幽居之際,亦能借詩以傾訴其心饞之感受,得以「無悶」、「易安」,獲致與人作性情相通的快慰。故「可以羣」的涵義是二元的;除了生活形貌上使人際關係顯得密合,以肯定詩人社會存在的意願外;並要求精神意識的溝通,以肯定詩的情感的激蕩可以獲得人間的共鳴。 故羣的真義,在強調生命並非孤立的存在;詩的感情的搖蕩,也非孤立的活動,詩在人與人之間相互激蕩、投射、照觀,並完成生命交通合一的快慰。是以詩雖由個人寫成,決不僅是「為人類之中的一個自己而寫的」,因為伴隨著詩的人之生存原不是一個絕對獨立於社會人羣之外的存在。明乎此,也才能進一步解釋「可以怨」的效用。 怨的感蕩之情仍從人生出發,是個人對現實種種際遇的投射及感應;楚臣漢妾、塞客孀閨、孤臣孽子之去境辭宮、衣單淚盡、幽居窮賤,無一不由人與人之對立、人與事之不諧所造成,悲怨的情感在矛盾中激發,同時亦要求在矛盾中獲得撫慰,所謂「離羣託詩以怨」,訴怨是一種必然的行理行為,也構成詩的精神特質。由此可以證明「羣」與「怨」是互相完成的。 「怨」是在人際關係的矛盾下產生的感受,「羣」是要求通達諧合的感動;「怨」是詩的情緒的顯明的表白,「羣」是這表白情緒的目的。就「陳詩展義」、「長歌騁情」而言,鍾嶸所強調的詩「可以怨」,並非從詩的特質純以「哀愁」為主來立論;因為他最終的目的是強調生命的諧合美好,由人際關係的諧合─「羣」,更而通達到人與自然的諧合完美─照燭三才,煇麗萬有。故「怨」的效用僅是生命通達諧合的過程,「怨」不是最終的目的,更非詩的價值 。 鍾嶸既依據詩的產生是由於情感的衝激來解釋詩的效用,而情感的衝動又由於對自然生命及社會人生的投射,故他的詩的效用說是由生命的本質及生命的目的上來立論,既不從純粹感受以求取「娛樂」、「快樂」或「美」作為詩的目的,也不專就知性的活動要求詩有批評或諷刺的精神,更不認為詩完全是哲學或政教的宣揚;而這一切目的,大概都可以包容於他的「照燭三才,煇麗萬有」、「動天地,感鬼神」、「可以羣,可以怨」的融合溝通自然人生、美化光輝自然人生的大效用的涵義之中。 梵樂希說:「詩的目的,乃是在喚起人生最高的一致與和諧」。莫銳(G.Murray)說:「詩是一些事物,在不同的等級中,它不僅是屬於專門的詩人,並且屬於整個的人類」。這些解釋,都與鍾嶸的見解有共通之處 。 此文專門論詩,卻沒有引用《毛詩序》的意見,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等詩歌為政教服務的理論已為鍾嶸所拋棄。另外,循「感物興情」的基調來解釋詩歌的效用,則知鍾嶸對於詩歌的看法,是只為作者服務的,只為讀者服務的,只為展現文學本身的精神風貌、滋味美感,而使人感蕩心靈、窮賤易安、幽居靡悶,情感能獲得抒發,得到世間的共鳴,甚至是震撼天地、感動鬼神,這才是鍾嶸理想的詩歌功效。故鍾嶸根本不提「正得失」三個字,而是要完成人與自然融合溝通:「照燭三才,煇麗萬有」的大效用 。 (待續) |
|
|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