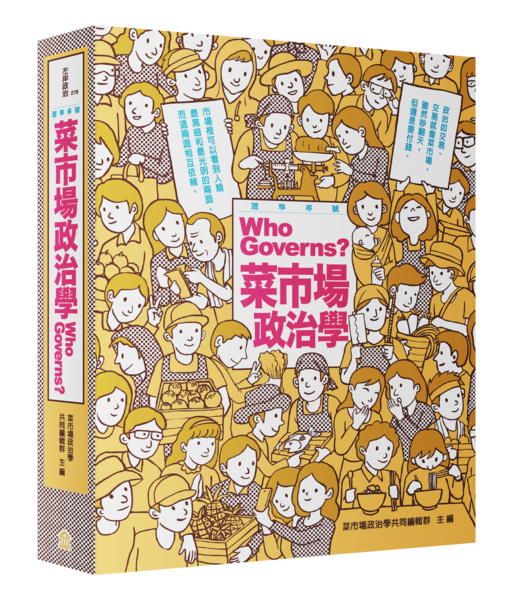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8/09/11 13:56:19瀏覽2897|回應1|推薦6 | |
女性政治人物的能力真的比較差? 為何保障名額制度可促進更平等的政治參與? 2017年,台灣歷經第三次政黨輪替,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新總統,新氣象,大家都在期待女性總統的新內閣有什麼不一樣。沒想到新名單一公布,仍舊是男閣員大大多於女閣員,嚴重性別失衡馬上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行政院的解釋是,內閣成員的組成沒有特別性別考量,完全是選用有能力者。的確,我們肯定需要有能力的政務官員來治理國家,但問題是為何有能力的公職人員「剛好」都是男人?若以有能力為出發點就「剛好」都找到男性公職人員,那背後隱含的假設是,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有能力,至少比女性有治國的能力。 這樣質疑女性行政能力的論述其實比想像中普遍。在台灣,鼓勵婦女參政的制度主要是婦女席次保障(下面會詳述這個制度),反對婦女席次保障的論述常出現相同的邏輯,即「因席次保障而當選的女性往往能力上不足,若非席次保障,無法靠自己能力擠進當選名單內」。 真的是如此嗎?在能力上,女性公職人員真的有比男性公職人員差嗎?在民意代表中,那些因席次保障而當選的女性公職人員真的在能力上較為不足嗎?是否當我們考量了性別的多元性,就必須犧牲公職人員的總體實力與能力? 要替這個問題找一個社會科學的解答,婦女席次保障的制度設計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因為一個很直觀的做法,就是去比較那些因保障而「當選的女性」與因保障而「被落選的男性」在能力上的差異。如果因保障而當選的女性先天能力不足,那兩相對比後,我們應該看到「被落選男性」的能力平均高於「保障當選女性」。 專門研究台灣女性參政的學者黃長玲有一篇新研究,就針對台灣的地方選舉做了上述的比較,她的結論是:受保障而當選的女性在各項能力的指標上,皆不亞於她們擠下的男性候選人,甚至很多時候,這些當選女性的能力更優於那些落選的男性。 「當選的女人」PK「落選的男人」 要了解這篇研究的論證,我們需要先粗略瀏覽婦女席次保障如何實踐在地方選舉中。台灣的地方選舉(也就是縣市議會選舉)是按照選區大小,每個選區選出多於一位當選人的制度,看應當選人席次多寡,通常是最高票的前幾位候選人當選(學術上稱這種選舉制度為「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根據這個選舉制度,性別保障席次運作如下:在每個選區內必須要有1/4的席次由女性擔任,若這個選區的應當選人為五人,則其中需有一位當選人為女性。若在五位最高票者中已有一位女性,則無需啟動性別席次保障的機制。但若五位最高票者皆為男性,則會啟動性別席次保障,得票排名第五的男性無法獲得席位,這第五個席位會由得票數最高的女性遞補(不論她實際的總得票排名第幾位)。換句話說,雖然地方選舉皆有婦女席次保障,但女性參選人仍舊可以不需依賴席次保障機制,而是按照自己的實力取得席位。席次保障只有在選區當選人的性別比例懸殊時才會啟動。 這樣的制度設計讓黃長玲得以去比較因席次保障而「當選的女人」與「落選的男人」。她比較台灣三次地方選舉(2002、2005與2009年),在當選的593位女性中,有68位是受席次保障而當選。換言之,另外有68位男性是因席次保障而落選。她將「當選的女人」與「落選的男人」依照選區配成68組,去比較兩位候選人的能力。 該如何比較兩人的能力呢?黃長玲按照教育程度、社會參與度以及政治經驗建立指標去衡量兩位候選人的能力。至於為何採用這些項目,除了理論指引外,在台灣選舉公報上,這三項條件也必定表列於候選人的簡歷中,成為選民評價候選人最快速也最直接的方式。 經過對比後,黃長玲發現在68組候選人配對裡,有34組是當選的女性比落選的男性能力較強;有27組雙方能力相當;最後有7組是落選的男性能力優於當選的女性。換句話說,在透過性別保障名額而當選的女性中,有90%的人不亞於甚至更優於她們擠掉的男性。 女性參政=品質更好的民主 除了得出受性別席次保障而當選的女性在能力上不輸於、甚至優於被她們排擠掉的男性外,這篇研究也發現,增加婦女保障的配額不僅會增加婦女參政,也會增加政治競爭的程度。黃長玲計算了從1954年到2009年婦女參政的趨勢,她發現雖然民主化後引入婦女保障席次,女性透過保障名額獲得席次的比率卻穩定下降。以地方縣市議會為例,當1990年台灣還在民主轉型階段時,在所有女性當選議員中(共有128位),有24%的當選人是透過性別保障名額進入議會(一共38人)。到了2009年時,總共有162位女性當選縣市議員,其中只有不到10%的當選人是受到性別保障名額的庇護而進入議會。 該怎麼解釋這樣的反向關聯?黃長玲認為這是提高婦女席位保障的正面連鎖效應。提高婦女保障名額首先提高的是婦女參政的意願。有超過一篇的研究指出,在保障名額越多的選區,會有越多的女性候選人,而女性有較高的誘因參選是因為她們認為當選的機率較高。當有越多的女性選擇參與選舉,選舉的競爭程度自然提升,這樣的正向循環也使得最終的女性當選人不需要席次保障,便能自行獲得足夠的票數獲選。這一連串的正向循環造就了法規面保障名額的增加與實際上使用保障名額比例的下降。換句話說,在台灣,提高婦女保障名額有助於提升整體民主政治的運作品質。
保障名額制度背後的民主意義 讀者們可能會有一個疑惑:既然那些受席次保障而當選的女性本身那麼有能力,那為什麼沒辦法憑己力選上? 回答這個問題,同時也可以回答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或是其他少數族群的保障名額)在民主社會存在的重要性與意義。為何有能力的女人無法選上公職,這背後有錯綜複雜的因素,包含政治場域長期由男性把持、選民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例如覺得女性應該善盡母職在家帶小孩)、整體社會的性別養成期待等,這些因素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以至於女性在主觀和客觀上都居於政治參與的弱勢。即便有客觀條件出眾的女性出面競選公職,也很可能因為長久積累的社會偏見以致落選。因此,性別席次保障或是其他促進女性參政的制度設計,並不是因為女性不夠優秀所以需要被保障,而是因為女性的優秀在結構上長期不被社會認可,我們需要這些保障制度來矯正這些偏差,讓女性終究有一天可以立足在真正公平的起跑點上與男性進行政治競爭。 民主政治的良善運行,不僅是要保障多數,同時也要尊重少數。在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裡,不同的社會群體(例如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性傾向等)理應有相同的機會參與政治,代表自己的群體,在政治過程中如實反映自己群體的政治偏好。理想民主社會的運行是在這些不同的價值中折衝出一個整體社會成員皆可接受的政策。然而,我們總是離大同世界還太遠,在現實世界裡,很多弱勢團體長久以來受到結構性歧視,根本無法在公領域發聲。這樣的民主體制在運轉上是有缺陷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有性別席次保障的制度設計(或如原住民席次保障等)來確保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保障名額的制度,無非是希望矯正長期結構的歧視,來更接近理想的民主政治。 換個角度想,性別席次保障其實就像在跑田徑賽的時候,我們會讓外圈的人站在比較前面。跑過田徑賽的人都知道,內圈與外圈的起跑點並不相同,我們不會要求所有人都應該站在同一條線起跑,因為外圈的距離就是比較遠,站在同一條線起跑反而不公平。我們會讓外圈的人適度的站在比較前方開始起跑,而我們也覺得這樣才能算是一個公平的比賽。性別保障名額乃至各式鼓勵弱勢團體參政的措施,都是讓距離比較遙遠的外圈選手可以往前站一點而已。在民主社會中真正的平等,是讓站在田徑場上不同跑道的人有不同的起跑點。 縱然台灣選出了一位女性總統,有其歷史意義,但選出了一個女總統並不代表性別參政就平等了,落實性別參政平等仍有賴於更多制度性的保障。 顏維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聚焦亞洲,興趣在國家與市場互動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政策。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