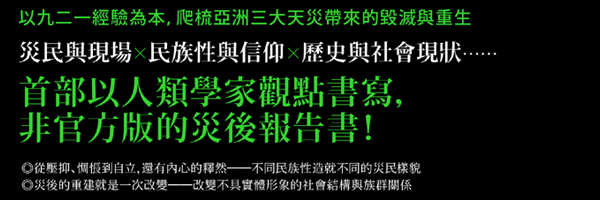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8/09/05 17:05:00瀏覽3705|回應1|推薦1 | |
海嘯在這塊土地撞出了許多洞,來自四面八方的善意,密密地將這些洞補了起來。 距離釜石災害對策總部不遠處,有個臨時搭建的小房子,門口立著「隨時可以報名救災」的告示牌。這日下午,即有二十名志工在門口排隊登記,等著工作人員安排工作並說明注意事項。 在媒體慣以「繭居族」、「飛特族」標籤化日本年輕世代時,這些包著頭巾、拿著鏟子穿梭在滿目瘡痍中的年輕身影將這些汙名踩在地下,奔馳而來。像是三十三歲的菊池隼在地震發生後,立刻到志工中心報到,帶領志工為災民清理屋子,三個月不斷。「我是和JCI(日本青年會議所)的夥伴說好一起救災的。」他的語氣很是輕鬆。
JCI(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青商會)是一九一五年在美國創建的國際青年服務組織,在「訓練自己、服務人群」的信念下,聯合青年們一起為地方服務。菊池隼二十五歲加入了JCI後,就常和會員一起參與社區工作,希望透過年輕人的精神帶動日本社會力發展。海嘯重創岩手縣,出生於此的他自然義不容辭,投入救災。
「還好我自己開公司,才能這麼任性。」他向我解釋,自己在距離釜石市兩小時車程距離的北上市,開了一家設計公司,災後這三個月,就是個專業志工。
這天下午,菊池隼帶領著一批年輕志工到受災嚴重的釜石商店街,清掃一間酒吧。酒吧離最熱鬧的商店街只有兩條街,就在一個住宅巷的最外頭,鄰近大馬路。這條馬路被路阻攔切,人車都不能通行,泥濘垃圾大多已清理乾淨,但仔細察看路旁的巷弄,還塞滿了爛泥倒木,維持著受災時的樣子。馬路另一邊的立體停車場也是災難的證明,柱子歪斜,裡頭的車輛此時不過是一個個報廢的五金、扭曲鏽蝕的鋼鐵,看不出車型。
「其實,很多公司鼓勵員工到災區服務啊。還有志工假,會給車馬費,還會捐錢。」菊池隼像是想起什麼似的,立刻補充:五月黃金周連假過後,支援災區的志工大減,旅行業者甚至跟志工團體聯手,推出觀光救災這種一舉兩得的「重建旅行團」。他說,如果有人想當志工,又不夠獨立,怕自己給災民添麻煩的話,可以參加旅行團,很方便的。
說完,他轉頭對其他志工比劃一圈,說今天的進度只有酒吧和隔壁的食堂。
「只有這樣?」話一出口,我立刻意識到自己的輕率。
「就算這樣,一天都做不完喔。」
菊池隼指了指眼前這個不過十坪左右的酒吧:「這個,兩天都不夠。」
「嗯,確實不夠。」我想起二○○一年發生在台北的納莉風災,癱瘓了四分之一個首都,我的租屋處周遭與辦公室同遭水患。大水退去後,泥濘糞屎垃圾堆積一起,花上整整一周都無法將自己的工作區清理乾淨。從不抽菸的我,甚至得靠一根又一根的白長壽氣味,來抑制這災難後的「災難」。
二○○九年的莫拉克風災過後的水災現場,同樣汙穢泥濘濁水的淹積,也令我印象深刻。在這相對乾淨的現場,我那藏在記憶角落的災後清理經驗,突然被翻攪出來,險險作嘔,逼得我不得不嚥下口水,將回憶和感受都吞下肚。
披上螢光綠背心的年輕人面無表情,不發一聲,就只是埋頭工作,各自搬出破爛的沙發木桌椅、清理窗戶邊四散的玻璃、刷清房子裡的泥濘。六月的日頭並不算強烈,況且這裡是北國之北,溫度涼爽宜人,但每個人都汗流浹背,豆大汗水滾進眼睛裡,讓他們不得不時常抓著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額頭擦擦臉。
我跟著兩名年輕人將沙發抬到屋外空地。短短的距離,仍忍不住喘氣。其中一位二十出頭歲的志工,剛出社會,難得有了一天假,便直赴災區幫忙。這是他第一次當志工,卻準備充分:腳穿長靴,頭有頭巾,面上掛著口罩,「網路上都有志工須知的資料。」他說,大家都會先做準備,盡量不造成他人困擾,「當然,食物跟水也要自己來。」日本的志工精神在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後被喚醒。
在這之前,日本的社會力陷入沉寂,當時的年輕人被批評冷血,但阪神地震的發生,讓無數大學生從那時開始前進災區,為災民服務,這年因此被稱為「志工元年」。或許因為阪神經驗如此特別,當地人會特別提到,海嘯過後,第一個趕赴災區的志工團體,便是來自阪神地區。
但早在阪神地震前半個世紀,民間就有系統性的社工服務出現:一九五一年,一個名為「日本社會福祉法人全國社會福祉協議會」(簡稱全社協)成立,在全國各地分設志工中心,來建構志願服務的網路體系,當時約九成多的市町村都參與設立。全社協平時多提供老弱婦孺等弱勢團體的社會服務,但在災難發生時,便成為地方的志工媒合中心。
以釜石市為例,當地全社協在定點設置好災區志工中心後,由其他縣市全社協專職人員加入運作,維持十人一組的駐地志工節點。畢竟,救災是一個長期抗戰。我在漁產中心停車場前方,找到志工中心負責人佐佐木英之時,他正拿著點名板清點志工。在太陽下站立許久的他,整個臉被曬得紅通通的,毛巾包在頭上,乍看以為是個年輕漁民。
「想當志工的人,都會到哪裡找資源或者報名呢?」我問。「媒體會宣傳報導。」佐佐木擦了擦汗,「想當志工的人都知道到要到全社協詢問,再由全社協分配到各災區。」「人都這麼多嗎?」我往前指了指。約莫十來位年輕人自行排成一列,等著被發派任務。「剛開始,每天都有兩百個人來我們這裡報到。現在,每天仍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志工,嗯,大概也還是有一百個人吧。」
志工需求太大,流動率也高,什麼樣背景的人都有,像是在隊伍中那一大群穿著深色道服的男子,就是來自東京高野山上的修行者。「雖然修行很重要,但來幫忙災民也是我們該盡的責任。」面對我的好奇詢問,他們回答簡明。
英國記者理查.佩理(Richard Lloyd Perry)深入災區採訪後,對日本人的「責任」有其觀察。他以為,一般而言,災民不會對政府的支援抱持期待,應該群起協力,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在歐美發生類似災害的話,受害者一定會高聲質問:「政府在哪裡?在做什麼?」儘管災後抱持著自立精神的日本人並不算少,但世人仍習慣將這些問題視作天災,而非政治問題,認為日本人是無力的災難犧牲者。「人們或許會這麼想,這種不幸,跟個人無關,跟市民影響力無關。既然非己所能為,就不得不忍耐了啊。」他因此斷言:這是擺脫個人責任的藉口。
從阪神地震到三一一的志工潮,可以被視為人們責任意識的提高,但在具有敏感度的記者眼裡看來,除了無私奉獻的精神外,還意味政府官僚的無能。「你可以稱這個現象代表著公民社會在這個國家穩定緩慢地形成……」駐日多年的美國記者凌大為發現,日本人正以各種方式學習「如何在沒有領導者的情況下過活」:即使三一一確實震出一股新的思維與力量,日本的官僚主義仍不懂得如何應付志工與民間團體。
《朝日新聞》評論員三浦俊明的批判更是強烈:人們以為國家是強大的、個人是弱小的,但日本是個人強大而國家弱小,「每一個日本人展現無比的強韌,但整體來說,我們是一團糟」
災難發生那一刻,大地沒有停止吐息。
人們如在輪轉帶上那樣,規律且反覆地醒著睡著生活著。
沒有人知道某個機台將出現變化,機台上的人更不知道――
這一秒就是命運的岔途……
|
|
|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