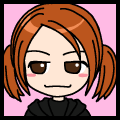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11/17 12:19:20瀏覽931|回應0|推薦10 | |
| 「小嬸也該到了。」玉笙一邊思考著之前紛擾的夢境一邊想。
「也許在這住下一兩個月,就當散散心罷。」她定了定主意,沿著米糠混合著石灰的低矮圍牆繞了一圈,推開半掩著的紅漆雕花鐵門,不留神一個踉蹌差點被兩層暗階絆個正著。 「哎呀!」 玉笙沒說話,小嬸倒是驚呼了一聲 「是玉笙嗎?」 「嗯。」 「小嬸。」 本來生份的眼光一下子全退散了。眼角的紋路是多得開了岔子,但瓜子臉、深邃雙眼與纖細的腰枝除了孕期,卻是常年不變的,故雖多年不見,玉笙仍然可以一下子便確認身分。只是小嬸當年烏黑的盤髮也花了,染的又脫了些顏色,多少斑駁陸離的日子體現在幾千髮絲上,才真正感知與被撞擊,所謂歲月無常。 「先進厝內吧,妳不知影後山天頂雲帶勾,要落雨了。」小嬸招招手,笑容可掬的臉沒有前進的意思,一邊叫著同時轉身急急返回灶腳,裡頭飄出筍絲燉蹄膀的油香。 晚飯時小嬸還忙著炒幾道菜,與她有一搭沒一搭閒聊著。 「從學校過來嗎?」 「嗯。」 「先去淡水找個朋友,才返來這。」 「男朋友阿?」 「不是。」 「女孩子喔,有對象就要把握,眼光不要太高,有男人才有肩膀可以靠,不要像阿嬸一世人歹命。」 小嬸端著炒得翠綠的空心菜走過來自顧自坐下吃飯, 「嗯。」她難以對小嬸解釋複雜的情緒,只好不停攪動碗裡過於爛熟的肉,這使玉笙覺得這頓飯吃得很彆扭。 「一個查某人也不能替妳阿公顧好這間厝,算來也是悲哀。」 小嬸斷斷續續說著這些年來的生活,大多數是人生失意的感慨;有些老有些膩,卻是最真實的人生。玉笙低頭默默扒飯,偶而點頭附和或抬起頭讚許一下菜色,才能換取小嬸得以短暫解放糾結成團的眉頭。 灶腳底仍懸著舊式的昏黃燈泡,風一陣過來便巍巍顫顫晃阿晃的,小嬸的瀏海有些塌了,隨著廚忙時逼出來的油汗斜斜貼在額頭與鬢角,彷彿生活的無奈全數攤展在飯菜裡了。她不禁想起教授,也花了的髮,他總不興染也不愛梳,讓那些個文藝復興般的自然捲終日在頂上肆虐。 「我的頭梳齊了,能讓楊貴妃在華清池沐浴個把月了。」像是幽王取悅褒姒一樣地,教授私下總愛用妙喻自嘲。 「那還不把身子洗到受傷阿?」 「不,受傷的是我的頭皮。」教授與她就這樣笑開了。 晚飯過後,玉笙把行李安頓妥當,隔壁便是祖父生前的房間。空氣潤潤的,雨遲遲下不來。燠熱使她毫無睡意,小嬸在右廂房睡了,她踱出中廳坐在屋簷下向外望。 夜裡,荒蕪許久的溪河堂仍保有記憶中的樣貌。跨過中廳的門檻左轉,祖父房間裡眠床的藺草墊緩緩飄著木製家具與草編交融成的舊時氣味,從泛白失去鮮豔紅底撒金漆原色的窗花間隙向外環視,久無人居的三合院一切如故,只是大部分空間枕著厚厚一層壓鼻的灰塵。除了住在隔壁鎮上的小嬸每逢年節會回來照應著,剩餘時間也就讓這房子靜靜躺在這裡靜待時空悠悠流逝。 童年印象中,這裡泛潮陰濕的時候多,如遇天晴的日子,夕陽總是懷著補償心態似地濃重,像肥熟過了頭的柿子,紅透得像要吞噬一切,不留骨血。每有日暮,東廂房的檀木床就像著了烈焰,床上病重的祖父總得上演一段遭火光圍困,四面楚歌的悲情戲碼。 「阿公。」玉笙從母親身後探出頭,噘起小嘴輕輕叫喚。 那時母親與小嬸已經不讓玉笙接近祖父,老人聽見童音,開始例行的掙扎,蠕動一陣之後恢復平靜,床上草蓆被陳年汗水些微浸潤,泛著蠟黃而破舊。那日,小嬸正在準備吃食,她看著母親入灶腳如平日一般詢問些許瑣事,再繞到院子裡隨意看看、摸摸玉笙的頭,而後獨自出門。 玉笙只覺得,母親這次的行李沉甸甸地,讓她跨出門檻時費了好大一番力氣。玉笙困惑注視著母親的身影在路口轉彎後,她霍然想起滾落到門外的陀螺,連忙奔過去撿起來,小嬸呼喚吃晚飯的聲音也像晚風一般渺遠,幾乎被玉笙忽略。 從此母親並沒有回到這裡,而是往南方開始另一段人生;再相見,已是不經意的時刻了。後來這些年,她從不因成長過程中少了母親而感缺憾,甚至反而自覺與母親的緣份淡薄,分開生活才是對彼此最好的決定。 「不知該說妳傻還是豁達?居然還能編理由為你媽開脫。」青惠是他的大學室友,有ㄧ說一藏不住話,玉笙喜歡她這樣不造作的個性,也常幫著她踩煞車留著神。 「她回來看過妳嗎?」 「沒有,後來我搬走了。」 「家裏的人至少有聯絡吧?桐仔腳那邊要找也是聯絡得到。」 「她一定有無法解釋的理由。」 「我不相信。至少我媽離婚前很坦白說她受不了苦,也不希望我跟著她受苦。我早就不怪她,她遇人不淑遇到我爸,也夠可憐的。我最討厭自以為不解釋別人都會懂的爛人,尤其是男人,他們都不是東西。」 心底那個人也從來不解釋,關於所有一切。有了就是有了,何必無謂解釋什麼?換你心為我心始知相憶深,心肝交換了,也全都透澈了。 但她從來沒懂過,她只是信任,那是一種奉獻式的,所有人都無法理解的信任。 就像她接受他一樣。起初她以為那只是敬愛、只是崇拜。直到他靠在背後忽然環抱著她,輕柔地像深怕捏碎了一只易碎的瓷娃娃,她側身依偎在他懷裡,明白他的珍惜卻不能肯定他的心思,感情遠近的量測如同宇宙光年,所有單位都在人們自己的度量衡中,距離是說不清楚的,除非自己就是那把尺,量出來多麼恆遠無盡,也只有自己明白。 漸漸地,玉笙聞到水淹進泥土的味道,不ㄧ會兒屋簷就成了一片瀑布,將她的雙腿噴得濕漉漉。玉笙喜歡山雨欲來前,侵門踏戶入厝內那種整團整團,泥土揉合著青草的濃濁氣味,雨勢愈暴她睡得愈沉,無論鬧脾氣或高燒了病了疼了,只要下雨,多半不藥而癒。 「妳這查某囝仔,甘是雨神下凡,遇水則興。」小嬸摸摸玉笙的頭。 「阿母說,查某囝仔目睭有水得人疼」 「妳是愛哭精,當然目睭全水」 「我才沒有!」玉笙癟著嘴委屈地否認。 「阿笙甘會想阿母?」 「不會,玉笙有阿公。」 「阿公若不在怎麼辦?」 「阿公要去哪裡?」 「很遠的地方。」 「我也要去!」 「玉笙要上學,沒辦法去。」 「阿嬸,」玉笙忽然睜大眼睛。 「阿公會跟老師一起去嗎?」 「不會,老師要教玉笙讀書、要照顧老師的阿爸阿母、要結婚生小孩,老師不能跟阿公一起去。」 那時玉笙已經十歲了,她恍然懂得ㄧ些什麼卻又解不開。其實那天曾偷偷在小嬸傍晚煮飯時溜去看祖父。赫然發覺,接近的,或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油盡燈枯失了靈魂的軀體,只靠在生與死的懸崖邊上,使玉笙感到驚懼。面容紅潤飽滿聲如洪鐘的祖父,或許已經被一場場未停歇的暴雨沖失了。 「阿笙……」祖父看似用盡全身力氣,聲色卻仍然沙啞遲緩。 「阿嬸說阿公要去很遠的地方?」 「我也要去,」玉笙怕小嬸發現,只敢咕噥著。 「還有老師。」 「玉笙……跟老師說,說阿公跟老師沒有……緣份,請老師一定要原諒阿公。」 「阿公什麼時候要去?」 「不知影……。」 「阿公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影……但是阿公會回來看……玉笙。」 「……嗯?」玉笙對不確定的答案感到有些茫然。 黃昏的小房間裡,祖父話語斷斷續續支離破碎,像是上映著慢速播放的黑白電影,老少唱著無言的小調的情境。那時祖父的混濁瞳孔似乎透出變得異常淒切的光,像必須將一件珍藏已久的寶物毀棄般不捨。 「床底……箱子……」 「箱子?」 「鑰匙……五斗櫃……底下左……左邊……」 她小心翼翼拖出祖父置於床底的木箱,費力又笨拙地開了鎖,撲鼻而來的霉味讓她嗆了一下,當時玉笙不懂那些文字資料的意義與重要性,現在想起來,那是個微小中見偉大的愛情、最平凡卻反而深刻的歷史。 玉笙拿起最上頭的一本筆記,裡頭掉出一張信紙,她心中起了異樣之感,總覺得裡頭住了個以後的自己,或是朱老師的身影。 書籤上頭褪色的字跡泛著黃斑,有些熟悉的字體斜斜寫著: 「小樓吹徹寒,多少珠淚倚欄杆。」 再往下一張,夾雜著日文密密麻麻的字只大略看懂其中兩行中文: 本籍:台北洲台北市下奎府一丁目二十三番地 住所:東勢郡新社庄大南字大南九十八番地 「要吃飯了!阿笙又跑到哪去了?阿宏去找一下。」 她聽見堂哥沿著走廊跑過來的腳步聲,細聲細語的阿嬸總是在她偷溜進祖父房間時脾氣特別大。她沒時間細想,將書籤與寫著本籍住所的紙本揣在懷裡,將箱子闔上胡亂推進床沿,閃過堂哥,溜回房間。 胡亂用過晚飯,回了房才想到鑰匙來不及藏回原處,箱子也忘了鎖。本來想鼓起勇氣在夜裡送鑰匙回去,一直熬到午夜實在睏倦,睡夢中還來不及懊悔,祖父就悄悄過世了,沒有驚動任何人事,或許只有那麼不起眼的,輕飄飄地,斷氣前的身體顫動,無人知曉。 |
|
| ( 創作|連載小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