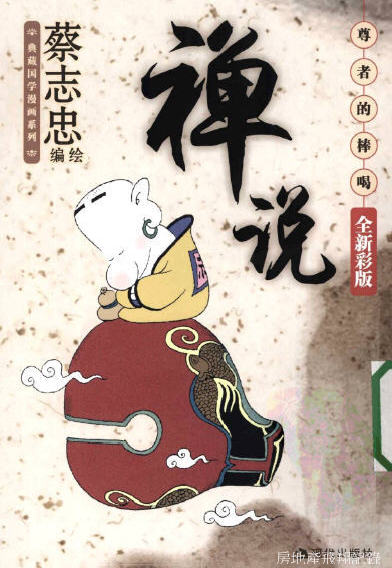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7/04/11 12:02:20瀏覽1483|回應0|推薦0 | |
有網路跟搜尋引擎真好,要是裡面的公案要我自己想出一個答案,我會想到頭破也想不出吧,我將網路上看到相關的文章重點摘要下來,對於以後再看會方便許多吧。 禪宗祖師 達摩祖師中國禪宗初祖: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達摩祖師泛海來到廣州,後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時人稱「壁觀婆羅門」。畢生提倡「二入四行」之教法,於弘法時屢遭險難,先後五次遭毒害。約魏文帝大統二年,因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於第六次被毒害時從容滅度。因其將佛陀「明心見性」的禪法傳入中土,故為中國禪宗的初祖。 中國禪宗二祖慧可大師:慧可大師,南北朝人,俗姓姬,武牢人,中國禪宗二祖。早年精於儒道,通老莊易學,後棄俗學,依寶靜禪師出家。為求無上大法,立雪斷臂,師事達摩。畢生力排誹議,雖屢遭險難,但仍堅持隨宜說法,廣渡群品。周武宗滅佛時,與同參曇林法師力挽狂瀾,護送經典佛像。後隱司空山,付法三祖僧璨。慧可得師精髓,承師遺志,弘揚達摩禪法。寂於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世壽107歲,諡「大祖禪師」,可謂中土禪宗第一人。 僧璨大師中國禪宗三祖: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後周武帝破滅佛法,三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傳法四祖道信。後適羅浮山,悠遊二載,卻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三祖為四眾廣宣心要訖,於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年)合掌立終,諡「鑒智禪師」。傳燈法本為《信心銘》。 中國禪宗四祖道信大師:隋朝蘄州人,俗姓司馬氏,中國禪宗四祖,世稱雙峰道信。幼慕空門而出家,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入舒州皖公山,參謁僧璨,言下大悟,奉侍九年,得其衣缽。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歸蘄州,住破頭山三十餘年,傳法於弘忍,另有弟子法融別立「牛頭禪」。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道信大師垂誡門人,安坐而逝,世壽七十二歲,建塔於東山黃梅寺。世人稱道信與弘忍的道法為東山法門,遙尊為東山法門之初祖。著有《菩薩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門》等書傳世。 弘忍大師中國禪宗五祖:弘忍大師,俗姓周,湖北黃梅人,生於隋仁壽元年(公元601年)。 七歲時,從四祖道信出家。年十三歲,正式剃度為僧。他在道信門下,日間從事勞動,夜間靜坐習禪。道信常以禪宗頓漸宗旨考驗他,他觸事解悟,盡得道信的禪法。永徽三年(651)道信付法傳衣給他。同年九月道信圓寂,由他繼承法席,後世稱他為禪宗第五祖。因為四方來學的人日多,便在雙峰山的東面馮茂山另建道場,名東山寺。唐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二月,五祖示寂,世壽74歲。傳燈法本為《最上乘論》。 中國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慧能大師,俗姓盧,祖籍范陽(今河北涿州)人,生於唐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三歲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砍柴為生。因聞客讀《金剛經》有所悟,前往黃梅禮五祖弘忍大師為師。初見五祖,五祖問他是哪裡人?來求什麼?慧能說是嶺南新州百姓,來求作佛。五祖說:「汝是嶺南人,又是獦僚,若為(如何)堪作佛!」他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僚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心驚而不便表示,後讓他去堆房春米八個多月。五祖選衣缽傳人時,慧能因呈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而獨得五祖之心。後五祖秘傳衣缽與慧能。慧能離開五祖後,隱居獵人隊中17年,後於曹溪廣演頓悟禪,開創出禪宗一花開五葉的輝煌禪史。唐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六祖示寂,世壽76歲。弟子法海記錄其教法成《六祖壇經》,流傳於世。
書內公案網路搜尋不錯解答 P15 六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不願意建立一最悟道的文字形式,也不應執著於佛經中的文字,而應當活用,更不應當以為別人依照這一套方式,就可得到解脫,就是要人不要被文字所惑,更不要拘於文字中,而成為文字蟲了。菩提之道,是以心傳心的,所有的佛經都只是幫助我們達到自悟的方便之門而已,如果死依賴佛經,結果將是什麼也得不到。 人的自性,就好像本體一樣,心是自性的作用,內存在人中。自性是絕對的善,但心卻未必都為善,直指人心,就是要人從自性的觀點來提升心,使心能進入清淨光明的涅槃淨地,所以慧能在談到心時,不僅談到淨心、善心、平心、直心、道心及菩提心,,也談到不淨心、不善心、邪見心、煩惱心及妄心等。慧能指出心不是靜的整體,而是動的歷程,像水一樣,有時純淨,有時混濁,有時急湍。 慧能不認為歸依於佛、法、僧這三寶,而要依賴覺、正、淨這三寶,因為論是從內或從外而言,成佛都是一種自性作用的效果,慧能主張一切應以自性為目標,他說:「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就可知慧能是以人的自性和自心來解釋佛理,而不是以外在的對象為目的,
P20 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眾生執著於生死與涅槃為二元隔絕的迷見,因此,經由斷盡煩惱才能得到脫離六道的解脫世界而開悟。為此,必須經歷無量長時間的歷劫修行。但是,實際上煩惱是無數的,凡夫畢竟無法全部斷盡。煩惱是由生活中,種種不如意所引生的心境,菩提是由生活中,種種如意不如意所得的覺悟心境;由此可知,煩惱(梵語klesa)不離生活,菩提也不離生活。生死是有生有死,有生有滅,涅槃則無生無滅,無生無死;佛看眾生的生死即是涅槃,凡夫看佛的涅槃境界是生死; 生死即涅槃,涅槃不覺悟,涅槃提生死;離生死無涅槃可得,離涅槃無生死,只是迷悟染淨有別;
P20 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 佛教謂生死往來之世界有三:一曰欲界,有淫欲、食欲,有情之所住,自六欲天,下至無間地獄,稱為 欲界 。二曰色界,色為質礙之義,有形之物質,在欲界之上,離二欲有情之所住,四禪天,或立十六天、十八天。三曰無色界,無色、無物、無身,有四無色,稱為 四無色天或四空處 。十方為佛教用語,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十方。泛指各處、各界。三界是唯心所造,明心時三界便空,所謂「迷時三界有,悟時十方空,欲知成佛處,會是淨心中。」參禪不能廓然大悟,即使坐破蒲團,依然迷而又迷。迷時以三清為三界, 悟則即三界是三清。因此「迷時三界有,悟時十方空」勸喻人須明心見性、頓悟幻空以明成佛。
P142 有和尚問崇慧禪師:「達摩未到中國之前,中國有沒有佛法?」禪師答:「沒來之前的事暫且擱著,你自己的事怎麼樣了?」和尚不解,崇慧禪師又說:「萬古 長空,一朝風月。」「萬古長空」把時空拉得很長很大,「一朝風月」則把時空凝聚到眼前當下。對修行人來說,不要管它萬古長空,只管一朝風月就可以了;當下 是什麼就是什麼,當下說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句禪語是把時空的長短和達摩帶來的禪法或釋迦牟尼佛的心法對比起來講的。其實那位發問的人知道,處處都是佛法,佛法本來就是現成的,跟達摩來 不來中國沒有關係。但他這句話問得太遠了,跟當下沒有關係,可是他自己不清楚。崇慧禪師答以「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是點明對方不管目前、現在、當下,卻想到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大的空間,完全不切實際。一朝風月是萬古長空中的一點一段,但若無這一點一段,就沒有著力處。
P144 溈山靈祐禪師(771~853)唐代僧。為溈仰宗初祖。福州長溪(福建霞浦縣南)人,俗姓趙。十五歲隨建善寺法常(又稱法恆)律師出家,三年後,於杭州龍興寺受具足戒,又從錢塘義賓受律部。曾先後遇寒山、拾得。二十三歲至江西參謁百丈懷海,為上首弟子,於此頓悟諸佛本懷,遂承百丈之法。憲宗元和末年(806~820),奉懷海之命,棲止潭州大溈山,山民感念其德,群集共營梵宇,由李景讓之奏請,敕號「同慶寺」。其後,相國裴休亦來諮問玄旨,聲譽更隆,學侶輻輳,海眾雲集。會昌法難之際,師隱於市井之間,至大中元年(847)復教之命下,眾迎返故寺,巾服說法,不復剃染。裴休聞之,親臨勸請,始歸緇流。師住山凡四十年,大揚宗風,世稱溈山靈祐。大中七年正月示寂,世壽八十三,法臘六十四。諡號「大圓禪師」。著有《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語錄》一卷、《溈山警策》一卷傳世。嗣法弟子有仰山慧寂、徑山洪諲、香嚴智閑等四十一人。其中,慧寂於仰山宣揚師風,承其後而集大成,世稱靈祐與慧寂之法脈為『溈仰宗』。
P146 馬祖道一禪師 AD709-788,馬祖道一,唐朝四川人,俗姓馬,故世稱馬大師或馬祖。他的容貌奇偉穎異,兩眼虎視眈眈,舌頭長過鼻尖,腳下有兩個輪紋,走路就像牛在步行一般。道一幼年出家,後來到南嶽衡山學習禪坐,巧遇懷讓禪師以磨磚成鏡接引之,終於契悟上乘佛法。 大梅山法常禪師,馬祖道一禪師之法嗣,湖北襄陽人,俗姓鄭。幼年即出家,從師子荊州玉泉寺 。其容貌清峻,性度剛敏,具有超人的記憶力,“凡百經書,一覽必暗誦,更無遺忘”。二十歲的時候,于龍興寺受具足戒,後參禮江西馬祖大寂(道一)禪師。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參馬祖大師問道:「如何是佛?」什麼叫作佛?佛在哪裡?如何才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你發問的這念心就是佛,不必另外去找了。除了能問的這念心以外,哪裡還有佛的存在?離心別無佛,離心別無道。法常禪師言下大悟,入大梅山住二十年。 明州大梅山的法常禪師一聽馬祖大師說「即心是佛」就開悟了,便至大梅山保養聖胎。這個消息不脛而走,後來傳至馬祖大師耳中。馬祖大師想測驗、測驗他,是否真的悟到「即心即佛」的道理,於是派了一位法師前去試探,說道:「聽說你在馬祖大師門下開悟了,所以在此住山。你當時悟到什麼?得到什麼?」法常禪師回答:「馬祖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這位僧人馬上就說:「馬祖大師近日說法又不同了,以前是講即心是佛,現在又不講即心是佛了。」大梅法常禪師就問:「作麼生別?」既然不講即心是佛,那麼現在又講什麼法?這位法師接著說:「馬祖大師近日不講『即心是佛』,他說『非心非佛』,既不是心,也不是佛。」什麼意思?就是不准開口,講佛不對、講心也不對,一說出來就是生滅,開口即錯,動念乖真,所以近日又講「非心非佛」。 「非心非佛」也是一種法門。以前講「即心即佛」,是由文字般若契悟實相般若;由有念、有想,契悟無念、無想的這念心;由有言、有說,契悟到無言、無說的這念心。換言之,馬祖大師觀察眾生的時節因緣,現在不採文字、言說來接引了,開口即生滅,所以又道:「既不是心,也不是佛。」說心、說佛皆是生滅,好比「刻舟求劍,劍去遠矣」,所以不能講、講不得,這是最高的境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講出來便成為形容詞。上上根機的人一聽到「心即是佛」,馬上就能開悟。後來這句話慢慢流傳卻變成口頭禪,人人都會說「即心即佛」。因此祖師馬上又開出另一種法門──不准開口,就講「非心非佛」,免得大眾落入口頭禪。 大梅法常禪師又講:「不管馬祖大師橫說豎說,以前講『即心是佛』,現在又講『非心非佛』,這個老頭兒專門使人錯亂顛倒,迷惑、欺騙別人。」為什麼大梅法常禪師會這麼說?因為他已經悟到「即心即佛」的道理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知道所有的言說都是方便,何時該讚佛歎祖?何時該呵佛罵祖?就懂得拿捏。本來這念心不生不滅、一法不立,馬祖大師偏偏要說這麼多東西出來,使人去捉摸、去思惟,使人落入口頭禪,落入方便,失去究竟。所以大梅法常禪師呵斥馬祖大師專門迷亂人,任憑他說「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 大梅法常禪師已經悟到諸位聽法的這念心,不管怎麼講他都能明白,絕對沒有絲毫的懷疑。這位僧人便回去據實稟告馬祖大師,馬祖大師云:「梅子熟也。」這人不會受騙了,任憑怎麼講,就算釋迦牟尼佛現前說:「非心非佛」,他也不會相信佛祖所說的話,因為他已經契悟了這念心,契悟「即心即佛」的道理,一切言說都是方便。以上舉這兩則公案來說明「即心即佛」的原委。《景德傳燈錄》 宗寶道獨禪師(1600~1661)明末曹洞宗僧。南海(廣東)人,俗姓陸。號宗寶,別名空隱。世稱空隱宗寶、宗寶道獨禪師。六歲喪父,隨母近寺而居,聞鄰嫗「發願來生童真出家」、「見性成佛」等語,乃立定出世之志。稍長,得六祖壇經,初不識字,乃禮請大德誦讀,竟能成誦。年十六,禮十方佛後自行執刀剃髮。歸隱龍山,結廬而居,侍母盡孝十餘年。二十九歲,往謁博山無異元來,受具足戒而得法。出住廬山,其後歷主廣州羅浮山、福州長慶、閩之雁湖、南臺山之西禪寺、粵(廣西)之芥菴、海幢等諸剎。清順治十八年七月示寂,世壽六十二,法臘三十三。有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六卷行世。
P148 蜘蛛之絲 作者:芥川龍之介 一天,佛世尊獨自在极樂淨土的寶蓮池畔閒步。池中蓮花盛開,朵朵都晶白如玉。花心之中金蕊送香,其香胜妙殊絕,普薰十方。极樂世界大約時當清晨。 俄頃,世尊佇立池畔,從覆蓋水面的蓮葉間,偶見池下的情景。极樂蓮池之下,正是十八地獄的最底層。透過澄清晶瑩的池水,宛如戴上透視鏡一般,把三惡道上之冥河与刀山劍樹的諸般景象,盡收眼底。 這時,一名叫犍陀多的男子,同其他罪人在地獄底層掙扎的情景,映入世尊的慧眼。世尊記得,這犍陀多雖是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大盜,倒也有過一項善舉。話說大盜犍陀多有一回走在密林中,見到路旁爬行一只小蜘蛛,抬起腳來,便要將蜘蛛踩死。忽轉念一想:“不可,不可,蜘蛛雖小,到底也是一條性命。隨便害死,無論如何,總怪可怜的。”犍陀多終究沒踩下去,放了蜘蛛一條生路。 世尊看著地獄中的景象,想起犍陀多放蜘蛛生路這件善舉。雖然微末如斯,世尊亦擬施以善報,盡量把他救出地獄。側頭一望,說來也巧,淨土里有只蜘蛛,正在翠綠的蓮葉上,攀牽美麗的銀絲。世尊輕輕取來一縷蛛絲,從瑩洁如玉的白蓮間,徑直垂向香渺幽邃的地獄底層。 這邊廂犍陀多正和其他罪人,在地獄底層的血池里載沉載浮。不論朝哪儿望去,處處都是黑魆魆暗幽幽的,偶爾影影綽綽,暗中懸浮著什么,原來是陰森可怕的刀山劍樹,讓人看了膽戰心惊。尤其是四周一片死寂,如在墓中。間或听到的,也僅是罪人懨懨的歎息聲。凡落到這一步的人,都已受盡地獄的折磨,衰憊不堪,恐怕連哭出聲的气力都沒有了。所以,恁是大盜犍陀多,也像只瀕死的青蛙,在血池里,惟有一面咽著血水,一面苦苦掙扎而已。 偶然間,犍陀多無心一抬頭,向血池上空望去,在闃然無聲的黑暗中,但見一縷銀色的蛛絲,正從天而降。仿佛怕人看到似的,細細一線,微光閃爍,恰在自己頭上筆直垂落下來。犍陀多一見,喜不自胜,拍手稱快。倘抓住蜘蛛絲,攀援而上,准保能脫离苦海。不特此也,僥幸的話,興許還能爬進极樂世界哩。如此,再不會驅之上刀山,也庶免沉淪血池之苦了。 這樣一想,犍陀多赶緊伸出雙手,死死攥住蛛絲,一把一把,拼命往上攀去。原本是大盜,手并足抵,區區小事一樁而已。 可是,地獄与淨土之間,何止千万里!不論犍陀多怎樣心焦气躁,要想爬出地獄,真談何容易。爬了一程,終于筋疲力盡,哪怕伸手往上再升一級,也難以為役了。一籌莫展之下,只好住手,先歇會儿喘口气,便吊在蛛絲上,懸在半空中,一面放眼向下望去。 方才是不顧死活往上攀,總算沒白費力气,片刻前自己還沉淪在內的血池,不知何時,竟已隱沒在黑暗的地底。那寒光閃閃,令人毛骨悚然的刀山劍樹,也已在自己腳下。如果一直這樣往上爬,要逃出地獄,也許并非難事。犍陀多將兩手繞在蛛絲上,開怀大笑起來:“這下好啦!我得救啦!”那吼聲,自打落進地獄以來多年不曾得聞的。可是,基地留神一看,蛛絲的下端,有數不清的罪人,簡直像一行螞蟻,跟在自己后面,正一意在攀登上來。見此情景,犍陀多又惊又怕,有好一忽儿傻不愣登張著嘴,眨巴著眼睛。這樣細細一根蜘蛛絲,負擔自家一人尚且發發可危,那么多人的重量,怎禁受得住?万一半中間斷掉,就連好家伙我,千辛万苦才爬到這里,豈不也要一頭朝下,重新掉進地獄里去么?那一來,可乖乖不得了!這工夫,成百上千的罪人蠢蠢欲動,從黑洞洞的血池底下爬將上來,一字儿沿著發出一縷細光的蜘蛛絲,不暇少停,拼命向上爬。不趁早想辦法,蛛絲就會一斷二截,自己勢必又該掉進地獄去了。 于是,犍陀多暴喝一聲:“嘿,你們這幫罪人,這根蛛絲可是咱家我的!誰讓你們爬上來的?快滾下去!滾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方才還好端端的蜘蛛絲,竟噗哧一聲,從吊著犍陀多的地方突然斷裂。這回有他好受的了。霎時間,犍陀多像個陀螺,滴溜溜翻滾著,唆地一頭栽進黑暗的深淵。 此時,惟有极樂淨土的蜘蛛絲,依然細細的,閃著一縷銀光,半短不長的,飄垂在沒有星月的半空中。 佛世尊佇立在寶蓮池畔,始終凝視著事情的經過。當犍陀多倏忽之間便石頭般沉入血池之底,世尊面露悲憫之色,又重新踱起步來。犍陀多只顧自己脫离苦海,毫無慈悲心腸,于是受到應得的報應,又落進原先的地獄。在世尊眼里,想必那作為是過于卑劣了。 不過,极樂蓮池里的蓮花,并不理會這等事。那晶白如玉的花朵,掀動著花萼在世尊足畔款擺,花心之中金蕊送香,其香胜妙殊絕,普薰十方。极樂世界大約已近正午時分。 (一九一八年四月)
P152 羅生門 作者:芥川龍之介 某日傍晚,有一家將,在羅生門下避雨。 寬廣的門下,除他以外,沒有別人,只在朱漆斑駁的大圓柱上,蹲著一只蟋蟀。羅生門正當朱雀大路,本該有不少戴女笠和烏軟帽的男女行人,到這儿來避雨,可是現在卻只有他一個。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這數年來,接連遭了地震、台風、大火、饑懂等几次災難,京城已格外荒涼了。照那時留下來的記載,還有把佛像、供具打碎,將帶有朱漆和飛金的木頭堆在路邊當柴賣的。京城里的情況如此,像修理羅生門那樣的事,當然也無人來管了。在這种荒涼景象中,便有狐狸和強盜來乘机作窩。甚至最后變成了一种習慣,把無主的尸体,扔到門里來了。所以一到夕陽西下,气象陰森,誰也不上這里來了。 倒是不知從哪里,飛來了許多烏鴉。白晝,這些烏鴉成群地在高高的門樓頂空飛翔啼叫,特別到夕陽通紅時,黑魆魆的好似在天空撒了黑芝麻,看得分外清楚。當然,它們是到門樓上來啄死人肉的——今天因為時間已晚,一只也見不到,但在倒塌了磚石縫里長著長草的台階上,還可以看到點點白色的鳥糞。這家將穿著洗舊了的寶藍襖,一屁股坐在共有七級的最高一層的台階上,手護著右頰上一個大腫瘡,茫然地等雨停下來。 說是這家將在避雨,可是雨停之后,他也想不出要上哪里去。照說應當回主人家去,可是主人在四五天前已把他辭退了。上邊提到,當時京城市面正是一片蕭條,現在這家將被多年老主人辭退出來,也不外是這蕭條的一個小小的余波。所以家將的避雨,說正确一點,便是“被雨淋濕的家將,正在無路可走”。而且今天的天气也影響了這位平安朝1家將的憂郁的心情。從申末下起的雨,到西時還沒停下來。家將一邊不斷地在想明天的日子怎樣過——也就是從無辦法中求辦法,一邊耳朵里似听非听的听著朱雀大路上的雨聲。 1平安朝,公元七九四年—一九二年。 而包圍著羅生門從遠處颯颯地打過來,黃昏漸漸壓到頭頂,抬頭望望門樓頂上斜出的飛檐上正挑起一朵沉重的暗云。 要從無辦法中找辦法,便只好不擇手段。要擇手段便只有餓死在街頭的垃圾堆里,然后像狗一樣,被人拖到這門上扔掉。倘若不擇手段哩——家將反复想了多次,最后便跑到這儿來了。可是這“倘若”,想來想去結果還是一個“倘若”。原來家將既決定不擇手段,又加上了一個“倘若”,對于以后要去干的“走當強盜的路”,當然是提不起積极肯定的勇气了。 家將打了一個大噴嚏,又大模大樣地站起來,夜間的京城已冷得需要烤火了,風同夜暗毫不客气地吹進門柱間。蹲在朱漆圓柱上的蟋蟀已經不見了。 家將縮著脖子,聳起里面襯黃小衫的寶藍襖子的肩頭,向門內四處張望,如有一個地方,既可以避風雨,又可以不給人看到能安安靜靜睡覺,就想在這儿過夜了。這時候,他發現了通門樓的寬大的、也漆朱漆的樓梯。樓上即使有人,也不過是些死人。他便留意著腰間的刀,別讓脫出鞘來,舉起穿草鞋的腳,跨上樓梯最下面的一級。 過了一會,在羅生門門樓寬廣的樓梯中段,便有一個人,像貓儿似的縮著身体,憋著呼吸在窺探上面的光景。樓上漏下火光,隱約照見這人的右臉,短胡子中長著一個紅腫化膿的面疤。當初,他估量這上頭只有死人,可是上了几級樓梯,看見還有人點著火。這火光又這儿那儿地在移動,模糊的黃色的火光,在屋頂挂滿蛛网的天花板下搖晃。他心里明白,在這儿點著火的,決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家將壁虎似的忍著腳聲,好不容易才爬到這險陡的樓梯上最高的一級,盡量伏倒身体,伸長脖子,小心翼翼地向樓房望去。 果然,正如傳聞所說,樓里胡亂扔著几具尸体。火光照到的地方挺小,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具。能見到的,有光□的,也有穿著衣服的,當然,有男也有女。這些尸体全不像曾經活過的人,而像泥塑的,張著嘴,攤開胳臂,橫七豎八躺在樓板上。只有肩膀胸口略高的部分,照在朦朧的火光里;低的部分,黑漆漆地看不分明,只是啞巴似的沉默著。 一股腐爛的尸臭,家將連忙掩住鼻子,可是一剎間,他忘記掩鼻子了,有一种強烈的感情,奪去了他的嗅覺。 這時家將發現尸首堆里蹲著一個人,是穿棕色衣服、又矮又瘦像只猴子似的老婆子。這老婆子右手擎著一片點燃的松明,正在窺探一具尸体的臉,那尸体頭發秀長,量情是一個女人。 家將帶著六分恐怖四分好奇的心理,一陣激動,連呼吸也忘了。照舊記的作者的說法,就是“毛骨悚然”了。老婆子把松明插在樓板上,兩手在那尸体的腦袋上,跟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一般,一根一根地拔著頭發,頭發似乎也隨手拔下來了。 看著頭發一根根拔下來,家將的恐怖也一點點消失了,同時對這老婆子的怒气,卻一點點升上來了——不,對這老婆子,也許有語病,應該說是對一切罪惡引起的反感,愈來愈強烈了。此時如有人向這家將重提剛才他在門下想的是餓死還是當強盜的那個問題,大概他將毫不猶豫地選擇餓死。他的惡惡之心,正如老婆子插在樓板上的松明,烘烘地冒出火來。 他當然還不明白老婆子為什么要拔死人頭發,不能公平判斷這是好事還是坏事,不過他覺得在雨夜羅生門上拔死人頭發,單單這一點,已是不可饒恕的罪惡。當然他已忘記剛才自己還打算當強盜呢。 于是,家將兩腿一蹬,一個箭步跳上了樓板,一手抓住刀柄,大步走到老婆子跟前。不消說,老婆子大吃一惊,并像彈弓似的跳了起來。 “吠,哪里走!” 家將擋住了在尸体中跌跌撞撞地跑著、慌忙逃走的老婆子,大聲吆喝。老婆子還想把他推開,赶快逃跑,家將不讓她逃,一把拉了回來,倆人便在尸堆里扭結起來。胜敗當然早已注定,家將終于揪住老婆子的胳臂,把她按倒在地。那胳臂瘦嶙嶙地皮包骨頭,同雞腳骨一樣。 “你在干么,老實說,不說就宰了你!” 家將摔開老婆子,拔刀出鞘,舉起來晃了一晃。可是老婆子不做聲,兩手發著抖,气喘吁吁地聳動著雙肩,睜圓大眼,眼珠子几乎從眼眶里蹦出來,像啞巴似的頑固地沉默著。家將意識到老婆子的死活已全操在自己手上,剛才火似的怒气,便漸漸冷卻了,只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低頭看著老婆子放緩了口气說: “我不是巡捕廳的差人,是經過這門下的行路人,不會拿繩子捆你的。只消告訴我,你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在門樓上,到底干什么?” 于是,老婆子眼睛睜得更大,用眼眶紅爛的肉食鳥一般矍鑠的眼光盯住家將的臉,然后把發皺的同鼻子擠在一起的嘴,像吃食似的動著,牽動了細脖子的喉尖,從喉頭發出烏鴉似的嗓音,一邊喘气,一邊傳到家將的耳朵里。 “拔了這頭發,拔了這頭發,是做假發的。” 一听老婆子的回答,竟是意外的平凡,一陣失望,剛才那怒气又同冷酷的輕蔑一起兜上了心頭。老婆子看出他的神气,一手還捏著一把剛拔下的死人頭發,又像蛤螟似的動著嘴巴,作了這樣的說明。 “拔死人頭發,是不對,不過這儿這些死人,活著時也都是干這類營生的。這位我拔了她頭發的女人,活著時就是把蛇肉切成一段段,晒干了當干魚到兵營去賣的。要不是害瘟病死了,這會還在賣呢。她賣的干魚味道很鮮,兵營的人買去做菜還缺少不得呢。她干那營生也不坏,要不干就得餓死,反正是沒有法干嘛。你當我干這坏事,我不干就得餓死,也是沒有法子呀!我跟她一樣都沒法子,大概她也會原諒我的。” 老婆子大致講了這些話。 家將把刀插進鞘里,左手按著刀柄,冷淡地听著,右手又去摸摸臉上的腫瘡,听著听著,他的勇气就鼓起來了。這是他剛在門下所缺乏的勇气,而且同剛上樓來逮老婆子的是另外的一种勇气。他不但不再為著餓死還是當強盜的問題煩惱,現在他已把餓死的念頭完全逐到意識之外去了。 “确實是這樣嗎?” 老婆子的話剛說完,他譏笑地說了一聲,便下定了決心,立刻跨前一步,右手离開腫包,抓住老婆子的大襟,狠狠地說: “那末,我剝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怪我,我不這樣,我也得餓死嘛。” 家將一下子把老婆子剝光,把纏住他大腿的老婆子一腳踢到尸体上,只跨了五大步便到了樓梯口,腋下夾著剝下的棕色衣服,一溜煙走下樓梯,消失在夜暗中了。 沒多一會儿,死去似的老婆子從尸堆里爬起光赤的身子,嘴里哼哼哈哈地、借著還在燃燒的松明的光,爬到樓梯口,然后披散著短短的白發,向門下張望。外邊是一片沉沉的黑夜。 誰也不知這家將到哪里去了。 (一九一五年九月) |
|
| ( 知識學習|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