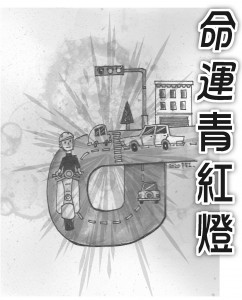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1/04/12 16:05:36瀏覽1585|回應2|推薦50 | |
命運青紅燈 黃瑞田 本文刊登於2021年4月12日更生日報副刊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detail/1475483
這篇文章由兩篇記實短文組成,第二篇〈悲喜交集〉,已無「喜氣」,因為文章中那五位友人──尤增輝、逸峰(洪秀雄)、洪醒夫、李文賢、彭選賢都已仙逝,令人唏噓。
一、氣爆餘生 去年二月,我感冒咳嗽,到鄰居范醫師的內兒科診所求診四次,仍不見好轉,第五次門診時,范醫師幫我轉診到鄰近的教學醫院胸腔內科做進一步檢查,照X光之後,發現右肺左上角有一個小膿瘍,服用了兩星期抗生素之後,依然咳嗽,再度回診照X光,膿瘍已結痂,醫師推斷可能還沒完全好,再拿兩星期藥,其中包括抗生素,可是,藥吃完了依舊夜咳。 我想到四十年前幫我治好鼻子過敏的鍾醫師,他在那時候的招牌是「鍾OO耳鼻喉科診所」,在六O年代,以「耳鼻喉科」為診所名稱的並不多,在還沒有健保的年代,我和家人若有感冒,就會去找他看診,他儼然是我家的家庭醫師。 民國七十七年,我家從南高雄搬到北高雄,感冒就不曾再去找三公里外的鍾醫師求診。我這次咳了一個多月,教學醫院也只能給我抗生素之類的藥,而且,我吃了一個月的抗生素,已經超量了,會影響日後的藥效。於是,我想起鍾醫師。 三十年,對每個人都可能有很大的變化。我先上網找鍾醫師的診所,確認他仍在原址營業,不過,他只有上午和晚上看診。 那天上午十點半,我抵達鍾醫師的診所,掛號後,連同我有四個人候診,等了半小時,輪到我。我一走入診間,鍾醫師看見我,就像見了老朋友一般的招呼:「黃老師,好久不見。」 「是啊!」我隨即應答:「三十多年了。」 鍾醫師仍然沒有穿醫師袍看診,習慣穿霧白色襯衫:「有嗎?你看起來沒什麼變。」 「三十多年前就老在這裡等了,」我在他的左側椅子坐下來,說:「你只有診所裝潢變得更典雅,人沒有變老,只是皮膚比較黑。」 「孩子都大了,當爸媽的怎麼可能沒有變老?」鍾醫師笑著說:「我常去爬山曬太陽。」 我突然想起他的營業時間變了:「鍾醫師下午都到其他醫院看診嗎?」 「沒有啦,自從氣爆案之後,我的人生觀就改變了,下午就跟太太去爬山、打網球、散步、吃美食等等,讓生活過得悠閒一點、享受一些,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下一秒鐘是不是還活著?」 「是啊!誰都無法料想到氣爆怎麼會炸成那個樣子,您這裡離爆炸現場不遠,應該可以聽到爆炸聲音。」 鍾醫師食指輕敲桌面說:「豈止聽到爆炸聲,我和太太還差點被炸死。」 「怎麼會呢?您這兒距離三多、武慶路口差不多兩百公尺。」 「我太太從台北搭晚上九點三十分的高鐵回來,我開車去左營高鐵站接她,太約十一點二十分接到人,就走高速公路,從中正路交流道下來,開到三多一路右轉,直走到武慶三路交叉口,剛好是紅燈,我就停下來,前面路口停了四輛機車,我車子右邊名貴飯店前面也停了三輛機車,正後方停了一輛;武慶路方向沒有車子,而紅燈還要等二十多秒才會轉綠燈,我心裡雖想左轉,卻又想到這輩子不曾違反交通規則,再等二十多秒,不會怎樣;可是,又閃過一個念頭:這麼晚了,不會有警察……於是不自覺的打左轉方向燈,闖紅燈左轉到武慶路,往診所開,開不到一百公尺,突然『轟隆』一聲巨響,我從後照鏡看到武慶、三多路口一片火光,我突然雙手發抖……我如果不闖紅燈左轉,乖乖等在路口等紅燈轉綠燈,我和太太可能難逃一死…。」鍾醫師停下來長嘆了一口氣。 我聽得幾乎愣住了,隔了幾秒鐘才說:「您的運氣真好!」 鍾醫師說:「我運氣好,但是那八個機車騎士,唉!他們都逃不過死神的掌心。」 「我有看到報紙報導,名貴飯店提供騎樓擺放八個罹難者大體,」我說:「那八位罹難者,可能就是那八位遵守交通規則的機車騎士。」 「氣爆隔天,我臨時決定診所休診,帶著太太到高雄市區每一間大廟去拜拜,感謝神明保佑。」鍾醫師伸出他的雙掌,說:「我雙手拿香拜拜時,不斷的發抖。」 「您一定嚇壞了。」 「沒錯,我連續休診三天,因為我的手抖個不停,電腦按鍵按不準,無法輸入病歷,唉!」鍾醫師搖頭長嘆:「氣爆後幾天,我良心很不安,我闖紅燈撿了兩條命,他們八個人守規矩卻丟了命,我一直覺得愧對他們。」 「應該是您當了四十多年醫生,積了許多陰德,神明才會暗中保佑,引導您闖紅燈。」 鍾醫師聽了忍不住的笑了,說:「我復診之後,下午就不看診了。差點忘了你是來看病的,你怎麼了?」 我遞給鍾醫師健保卡,將這一個多月來就診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他。他先是默不作聲,上了我的雲端病歷,逐一檢視這一個多月來我吃過的處方藥,然後說:「這些都是醫界使用多年的學名藥,我開給你最新的咳嗽藥,你吃看看,若不咳了,就不用再回診。」 我再次看到鍾醫師,是在高醫眼科,他跟我一樣,有嚴重的青光眼。
二、悲喜交集 在「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明清時代,鹿港是台灣的第二大港口,商船雲集,熱鬧滾滾。十九世紀末,日本政府修建鐵路,要經過鹿港,據說地方士紳極力反對,認為鐵路貫穿會破壞龍脈風水,於是鐵路轉往彰化,鹿港因此沒落,發展遲緩,得以保存許古舊建物及風土文化。 出生於鹿港民族路的尤增輝,新竹師範畢業之後,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及鹿港文史探討,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現實邊緣」專欄介紹鹿港風俗文物,結集出版《鹿港斜陽》及文圖並茂的《鹿港三百年》兩書,獲得海內外一致好評,鹿港街坊因此又活絡起來,成為旅人喜愛探訪的古蹟小鎮。 尤增輝,於一九八O年十一月下旬,打電話告訴我,台中一家日報的副總編輯桑品載先生邀請他出任該報副刊主編,希望我能幫忙寫稿。他說:「兄弟,我們終於有一塊可以共同耕耘的園地。」那年代,寫作風氣極盛,但有許多「小圈圈」,大報副刊因為被「小圈圈」把持,圈外人投稿被錄用刊登的機率很低,他要打破「小圈圈」,已打電話給很多文友,請大家支持,把好作品投給他,不要讓他漏氣。他還把出任副刊主編當做喜事,打電話向近親長輩及同輩堂、表兄弟姐妹報喜。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桑品載的夫人帶著十歲兒子由台北來台中,尤增輝要請他們吃晚餐。尤增輝騎車載桑小弟先行前往餐廳,桑品載夫婦及另兩位報社同事搭計程車稍後出發,當計程車經過三民路和健行路交叉口時,繞過一處車禍現場,卻不知道車禍受害者是尤增輝和桑小弟。原來肇事者邱貴仁酒駕,疑似闖紅燈撞上尤增輝的機車,尤增輝頭部受創昏迷,桑小弟左手及右腿骨折,兩人都由救護車送順天醫院急救。桑小弟無生命危險,尤增輝經腦部開刀後,發現大腦嚴重挫傷,轉往澄清醫院繼續搶救,於十二月三日不治身亡。 尤增輝是當時重要的文史作家,他車禍往生的消息,各家報紙都詳細報導,連一向不報導社會新聞的國語日報也破例刊登。 隔了幾天,我打電話給住在台中的學弟彭選賢,他是年輕小說家,經常在桑品載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小說,與桑品載熟識,我請他問桑品載,尤增輝的告別式的時間。 彭選賢立即打電話問桑副總,得知尤增輝告別式日期還沒敲定,桑副總要彭選賢接任尤增輝空出來的副刊主編,情勢發展令我感到十分意外。 我住在高雄,對於尤增輝的後事幫不上忙,只能靜待他的訃文到來。 等了三天,沒想到我先接到彭選賢的喜帖,婚宴時間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 再過四天,尤增輝的訃文寄來了,日期竟然也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時間在上午九時。 太巧合了吧?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要如何調整悲喜的心情? 那天上午八點半過後,我由高雄開車抵達台中尤增輝的告別式場,一些認識的中部文友也都提早到達了,例如散文家逸峰、小說家洪醒夫也來了,我的學弟小說家李文賢過來打招呼,陪我閒聊。在家祭前幾分鐘,一位五十歲左右的黑衣黑長褲的壯漢,匆匆走進會場,向禮儀人員說明來意後走向靈前,禮生遞給他三炷香,司儀用麥克風說:「各位朋友,現在車禍肇事者邱貴仁來向尤增輝先生上香致意。」 司儀說完,喪家家屬們突然集體大哭,尤增輝的母親,用鹿港腔哭喊著:「我的心肝仔子啊~~」那淒厲的嘶喊,讓人聽了痛徹心扉。 有人大聲叫:「跪下,跪下來拜。」 邱貴仁沒有跪下,三拜上香之後,轉身低頭就要離開,有人攔住他,用台語說:「去向尤老太太道歉。」 邱貴仁不說一語,閃過身,在家屬嚎哭聲中,逕自離開了,沒有人奈何得了他。 來送行的親友非常多,告別式進行得十分緩慢,家祭後追思,許多鹿港耆老在靈前悼念,公祭的單位也很多,整個告別式倍極哀榮,儀式到將近十一點才結束,十幾位住在台中、彰化的文友都說要回家沈澱心情,大家心照不宣,不說晚上再見。 我來自高雄,要找個地方等候到晚上六點,參加彭選賢的婚宴。學弟李文賢好意要我去他家,我覺得不妥,因為民俗有個禁忌,參加過喪禮,不能把穢氣帶去別人家裡,雖然李文賢不介意,但他的幼兒在家,我覺得要避免。 距離午餐時間還早,我們去台中中山公園湖心亭閒坐時,我又想起多年前曾經和尤增輝一起划船的往事,他一邊划船一邊唱〈教我如何不想他〉,其實,他的音樂素養很好,不僅歌聲好,還會吹小喇叭和洞簫,如今歌聲已邈,人也仙逝,不禁又令我心緒難以平靜。 十二點過後,我們去附近餐廳吃午餐,然後去看了兩場電影,片名都忘記了。看完電影,已接近下午六點,我們立刻趕往喜宴餐廳。 大約有三十位文藝界人士,分坐三桌,他們大部分曾在早上去參加尤增輝的告別式,但此刻都是談笑風生,我想大家對尤增輝和彭選賢這兩位朋友的際遇,都有無限的感慨。 喜宴進行中,洪醒夫跑過來向我敬酒,他說:「你跑到高雄去,要見個面都不容易,只有在好朋友婚喪喜慶的場合才能碰面。」 我舉起酒杯,輕輕碰一下他的杯子,意有所指的說:「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我補充一句:「《陽關以西無雨》寫得好!」 洪醒夫曾經發表一篇小說《陽關以西無雨》,聽我這麼一說,他立即接了一句:「撥雲見日,陽關以西無雨,乾杯吧!」 這是洪醒夫最後一次和我喝酒、談話;兩年後(一九八二年)的七月三十一日,他也因為車禍往生,文壇又殞落了一顆閃耀的巨星。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