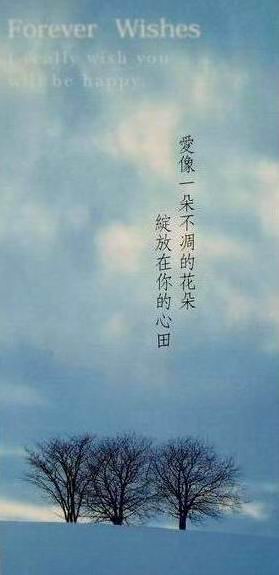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6/11/27 00:58:24瀏覽2121|回應12|推薦56 | |
你肯定不知道我常自問自答:「我愛他嗎?不!我恨他!我恨自己身上流著他的血,活著是他給的命,總有一日,就還他一條命吧!」饒是如此,還是不曾死去。真的!你絕對無法想像我有多麼恨他。 曾經這麼想過,或許,愛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如今長長長長的歲月帶走了年幼時的無知、青春叛逆時的恨意,也鬆開了長久以來沉重禁錮的心靈,遲來的淚水洗滌了一切,如今我確然的知道:真的很愛很愛他,自小到大,賦予我生命的這個男人──我的父親。 常常在回娘家時跟他這麼提起:「你的脾氣早在八百年前就改成這樣,多好?不那麼火爆我就不會那麼早出嫁,你看現在——後悔了吧?少個人幫你,我們家少賺多少錢哪?真捨不得你這麼勞累。」 「還說哩,也不想想妳以前是甚麼脾氣?妳要像現在這麼溫順貼心,我捨得把妳那麼早嫁出去啊?」他老是笑瞇瞇的回說兩句,卻總能夠讓我啞口無言,因為他說的是事實。 知道嗎?其實我真捨不得。捨不得他在滿頭白髮的今天仍然得為家計辛勞奔波,雖然嘴上說不出甚麼好聽話來甜甜他的心,但心裡疼他著實疼的緊。一個在生活上歷盡風霜,逐漸有著返老還童之心的老小孩,我能不疼嗎? 是這樣的,自從發生那件事之後,我自己才恍然大悟,我是真的在意他的一切感受,也感同身受。 前兩年,已然是家裡經濟支柱的妹妹打電話來說件事給我聽:「今天我跟爸爸吵嘴啦,他把我氣的忍不住對他說了重話:『我壓力很大呀!再不聽話老是讓我煩惱,以後就不養你!把你送進老人院去當孤單老人,再也不理你啦。』然後爸爸聽了以後就咿咿哇哇的哭了。姐,妳猜怎麼著?」 妹妹的口氣既輕鬆又調皮,我忍著將要發作的情緒好奇的問著:「怎麼著?」 「爸爸說他不要住老人院啦。爸爸忽然可憐兮兮的說話,結果媽媽聽了居然也跟著哭了,她說她也不要住老人院啦;天哪,這兩個老人怎麼變成小孩子啦?讓人真無法想像!」 是無法想像,我那威嚴如山的父親會像小孩子一樣癟嘴哀哀的哭?除了不捨還有不忍,當下,電話這端的我對著那端的妹妹破口大罵:「以後妳膽敢再這樣威脅他們兩個老人家,妳給我試試看,真是過份啊!妳,簡直是不孝!」 「哈!真難以想像,以前妳跟爸爸是死對頭呢,今天居然會心疼起他了?說起不孝,妳最不孝順了大姐,以前跟爸爸頂嘴頂的最兇的人就是妳啊,妳最忤逆他了,不是嗎?真是不可思議,妳的反應居然會這麼激烈?我也只不過是說個笑話給妳聽啊;爸媽居然越來越像小孩子一樣,需要人家哄了呢。」 話說的不假。對妹妹而言,爸媽對於晚年歸宿返老還童的反應之外,我那母雞護小雞般護著爸媽的反應又是另一個難以想像,她不明白婚姻改變了我──為人父母了,有一天我也會老,我也會覺得孤單,害怕被丟下;我真的懂爸爸害怕的那種倉皇無依。 有沒有跟你提過他像座山啊?不管是他的脾氣或是他的人。 父親跟我的脾氣都如同火山,同時爆發時所帶來的的破壞力是如此的不可忽視,而遭殃受牽連的總是無辜的家人。 身為長女的責任讓我無法盡情揮灑生命的彩筆,年少時的灰暗讓人覺的青春無色,生活的滋味盡是經濟帶來的壓力、無奈與不平;我並不覺得生命有你說的那麼的可貴。生命在我眼裡簡直是一無是處。我是那麼樣的不願意苟活著!我甚至恨起自己是父母男歡女愛下帶來的附屬品。 錢!錢!錢!生命只為了不斷的追著金錢往前跑?這錢是我要的嗎?為了幫著養家糊口,理想與抱負都得埋在我不能示人的夢裡了?!這要人如何甘心? 我決定死去! 說來好笑,你知道我決定死去前的最後一個決定嗎──我想著,臨走前,不能再增加他們的負擔了,總是得賺足了自己的喪葬費用。家裡經濟夠緊了,怎能再加添父母的負擔呢?心裡這麼想著:我起碼得幫自己買口薄棺才行。 那個晚上,我捧著飯碗夾起一口菜在嘴裡嚼著,在食不知味的當中,心隨意動脫口而出細聲的問著:「買具棺材要多少錢?」 「X你娘!」隨著那句耳熟能詳的國罵之後,接下來的聲音是碎了一地的碗盤乒砰作響,與滿桌被掀起落下的菜餚。那餐飯大家都沒得吃了,弟弟妹妹們哀怨的看著我、怪起我了:「姐,妳幹甚麼在這時候觸爸爸的楣頭?這下子害大家都得陪著妳餓肚子了!」 看著他的轉身離開,我居然沒有一絲惶恐害怕,反而有些可悲的幫忙收拾殘局,彼時我冷冷的思索著:這麼容易就可以惹惱一個人,左右他的情緒?那麼我呢?我平日的情緒被甚麼人或甚麼事左右著?此時我怎麼反而沒有半點激動與不安?莫非我的良心被狗吃了?或許心已經變冷成了涼心了?人家說愛的另一面不是恨,是冷漠;我對他的反應到底是恨還是冷漠?不管是哪種反應──我,愛他? 十八歲的那個夏天,在那個晚歸的夜裡,我終於明白,自己真的可以如此狠心與無情── 他扳開我的嘴巴想要聞我是否抽菸。我不抽菸的,身上的菸味是民歌屋中央空調的傑作,他卻不信任我,也不聽我解釋,強忍著他粗魯不信任的舉動,我絕望的聽著他的辱罵與接受棍棒無情的落下,一如往常,不躲不閃不流淚……他說了很多難聽粗鄙的形容,他是這麼形容說我的晚歸:「看妳的穿著像個小太妹,像個交際花也像個妓女,妳穿的這條褲子前後的口袋是讓人朝妳吐口水用的?……」 那天我身上穿的是一件泛白的牛仔吊帶褲,胸前跟後腰上各有一個可愛實用的口袋──我剪掉那件讓我自愛的生涯中,害我被貼上「壞女孩瑕疵品」標籤的牛仔褲,後來。 真的很懷疑:我真是他親生的?就在他說我像花蝴蝶交際花之後。我動手搶下他手上揮打在我身上的棒子,用盡全身的力氣狂吼:「我痛恨自己身上留著你的血,冠著你的姓,你不配讓我叫你一聲爸爸,從今以後我跟著我媽姓林!」我咆哮決絕的說出這樣的話,瞪大赤紅的雙眼面對著另一雙血絲四竄的炯炯大眼! 「X你娘,老子今後再跟妳說上一句話,我是婊子養的!」那張與我一樣,有著濃眉大眼的臉上露出難堪與憤怒。我緊接著抬高下巴挑釁的冷笑著:「記著你今天說的話!」 母親傷心惶恐的夾在兩座火山間燒的渾身發痛,看著無情的棍棒重重的落在我的身上,又聽見我忤逆犯上的口出狂言,她心焦心疼的急著說:「閉嘴!妳這孩子怎麼這麼說話?他是妳父親啊!再怎麼不是,妳也不能如此忤逆他呀!」 看著母親的臉,我無奈的閉上嘴巴。我恨極了這個愁雲慘霧的家庭,恨極了自己生而為人!無論我如何潔身自愛,他們總認為我極有能力招蜂引蝶。我恨極了這個世界,我決定折磨這個男人! 往後的半年內,我盡是跟著全家人談笑風生,就是把他視為無形,哪怕是家中只有我跟他兩個人時,我也寧願享受著只有自己一人的無聲世界。 他是不被我看在眼裡的,常常直到那一聲電話鈴響劃破沉默──「請你重撥。」我說。沒有贅言的掛上電話,直到電話鈴聲引來了他──那是找他的電話。 又一日,我跟媽媽妹妹們說到興高采烈時,聽到他興沖沖加入的聲音,看著他一臉的興致勃勃,我兜了他一頭冷水:「你何苦害我奶奶當了你口中的婊子?你忘了半年前跟我說的狠話?你說再跟我說話你就是婊子養的。」 那一臉又青又白直至轉呈紅色的一張臉讓我覺得快意十足,我的殘忍引來了家人的不平:「姐,妳太過分了」「妳這孩子真不懂事,妳不跟妳爸爸低頭認輸,怎麼妳爸爸拿著梯子想讓妳下來也不懂?妳爸爸在讓著妳啊!」這下子連他們都不願站在我這邊與我同國了。 先別說我倔強,讓我跟你說說:其實那時,我很不快樂! 忘了報復之後的感覺是甚麼,但是我很失落無助,甚至覺得全世界都遺棄了我。我還覺得很寂寞很孤單!我並不以為對他的打擊讓自己覺得已經比他還強,我更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覺得自己像個人——是否在良心變成涼心時我就已經死了?或許像空氣一樣讓人看不到摸不著的人是我?我覺得自己像一隻鬼! 你知道找不到工作待業中的那種感覺嗎?像隻浪費糧食的米蟲!面對著當米蟲的那種自卑,我是怎樣也逃不出那種心靈折磨的,失業中的我在這個家再也不願也無法開口了。 別說我反應過度,你倒是說說,米蟲怎好有地位來發出任何參表大小意見的聲音呢?面對著辛勞工作的長上,我只能覺得無地自容,只好盼用勞力整理家務,也好換來一絲尊重。 終於,內心的自責給肉體帶來了巨大的折磨,直到我無法起身。我發起高燒並且咳到胸口發疼,五腑六臟都咳的似乎移位了;沒人知道我後來沒有起身做家事,也沒有出門找工作,大家都依照自己的作息走在自己的軌道上。 忽然靜悄悄的空氣裡有了一絲絲的不同,靜默中彷彿有條蛇絲絲作響竄遊而入,我無力的睜開雙眼看見了他,他不帶一絲感情冷聲的問著:「妳怎麼在家?」 很冷,彷彿結冰般的氣氛籠罩著我,因為那不帶情感的一句問話,而我正發著高燒呢;很衝突的一種感覺啊,你知道嗎? 看不出情緒的一張臉,見不到我慣有的叛逆反應之後,那張臉反而有了一絲異動。 他伸出那雙粗糙長繭的大手摸著我的額頭。閉著眼睛,我聽到他稀罕的溫柔問道:「生病啦?吃藥沒有?好好休息別做家事了,家事等媽媽回來讓媽媽做吧,起的來的話,桌上有吃的東西,記得多少吃一些。我出門上班去啦。」 沒有對話──事實上我無力,也不願開口與他對話。我們之間沒有對話的日子已經過了大半年且繼續延長,他也只能被迫無奈的接受我的倔強──我們之間沒有問答的對話。 淡淡的,屬於他的味道隨著空氣流動逐漸薄稀,那漸遠的木香味說著他正要離去。面對著他的離開,我張開眼睛,以低望高看著他的背影流下眼淚──他怎麼好在這時候對我這般溫柔? 無力的拉上棉被蓋頭掩面,把自己埋了起來,並且在被窩中恣意的讓淚水流過臉頰,淹進了耳朵。我聽不見空氣的輕鬆,卻聽見自己的心在小小聲的狂喊:「爸爸,其實我好愛你,我真的好愛好愛你,好愛好愛──爸爸,其實我要的只是你這樣的一點點溫柔,這樣就足夠了,你知道嗎?」 透過窗外照進屋子裡的一絲明亮──那天,爸爸轉身離去的畫面讓我永遠無法忘記──那親像山的一個背影帶來了冬日暖陽。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