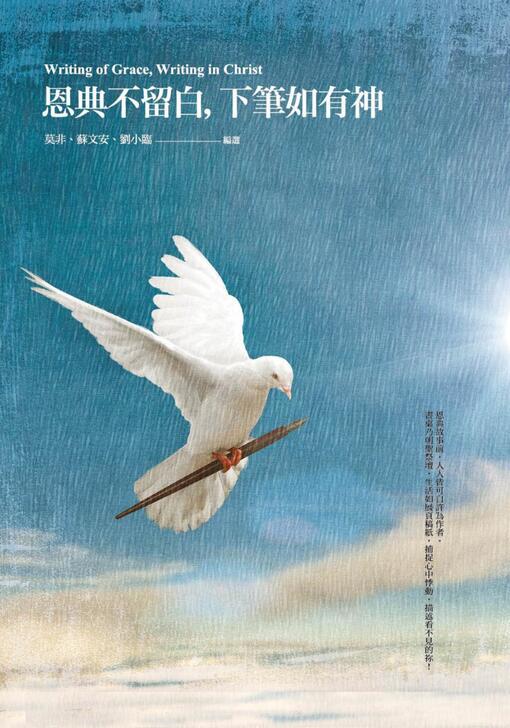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3/11/13 12:31:06瀏覽668|回應0|推薦1 | |
作者對墮胎女性有細緻的關懷和觀察,指出她們內心隱藏的創傷,提出了走出傷痛的建議。這篇文章,給人關懷給人警戒給人啟示。
大家有沒有到過日本東京的增上寺呢?那裡本來是供奉德川將軍家族的寺廟,卻有一隅擺放著一個個稚子的人形,何解? 據說,在日本一些窮鄉僻壤也有相類的擺設,除了是為婦女小產或生育時夭折的嬰孩所設置的靈位,還有就是紀念那些因墮胎而消失世上的骨肉。日本可耕地極少,田地所出極難支援人口的發展,懷胎的婦女會因應家庭經濟情況需要,而進行人工流產。直至後來明治天皇在十九世紀取代德川將軍家族的政權,才因為要顯示與白人文明看齊,表面移除了如墮胎這類在當時西方認為不人道的民風。 可是,即使人工流產在明治維新前是廣被接納的求存方法,婦女墮胎亦因順應家庭經濟狀況而毋須愧疚,為何仍會懷念打掉的胎兒呢? 在家庭輔導家泰瑞·雷瑟(Teri Reisser)及其丈夫家庭科、精神科醫師保羅·雷瑟(Paul Reisser)合著的Finding Healing and Wholeness After Abortion(暫譯《墮胎後尋找治癒和安寧》)一書中指出,美國竟有相類情況,縱使今天支持墮胎的團體,常表示人工流產的只是「子宮的東西」、「受孕的組織」或「懷孕的結果」。 泰瑞察覺不少曾經墮胎的女性向他們的診所求助,即使手術發生在很久之前,她們的內心仍飽受困擾,不能釋懷。這與一般人認為的,打胎解決了當下之急,隨著時間流逝,心情便會逐漸平復的看法,大相徑庭。
泰瑞稱這些心靈憂傷的婦女為「孤獨哀傷的群體」,她們打胎後的困擾,在早期因懷孕慌亂得到解決、生活得以回歸正軌而壓下。可是,墮胎所留下的傷痛,不會因解決了「當下」的煩惱便消失;而是會持續依附在心內,常伺機再度冒出頭來。尤其是當她們後來發現自己不育,或經歷小產時,不少會悔咎當初不珍惜骨肉,以致要承受不可再懷新生命或流產的惡果。 就算曾墮胎的女性再次成功懷孕,可是在做產前檢查的時候,用超聲波看到胚胎一直慢慢成長的各個過程,往往不期然地便想到從前以為只是一團組織,原來是活脫脫一條不斷成長的生命,因當初的一念便扼殺了。一直深藏內心不讓自己觸碰的難過之情,常會不可控地湧上心頭。又或者,有些婦女並未再計劃生育,看到了關於胚胎生長的紀錄片,也會產生愧疚之心。 也許你會說,今時今日在大部分西方社會,已沒有了早期道德或宗教的羈絆。可是,即使女權運動支援者雄辯滔滔地爭論女性墮胎的權利,卻鮮有曾選擇人工流產的婦女站出來,談自己的勇氣和感受。墮胎作為一個公共議題,支援者可以奮勇地激辯;但墮胎作為一位女性的個人經歷,卻相對極少見詳盡輕鬆喜樂地分享。為什麼呢? 因為,女人與生俱來的母性,是超越文化及時空的。一個女人懷胎後,便會自然生出與體內孩子的身心情牽。若這心連心的繫鏈被切斷,即便是媽媽自己的決定,其心靈深處也猶如被奪走了一塊重要的部分,留下一個無底洞難以填補。這種天生的母親悟性,不僅刻在遠古的日本女性心中,也刻在當下先進國家的婦女心中。雖然美國自1970年代已將墮胎合法化,女性自主權及非宗教的論調已成為主流,但是,母子連心仍跨過時空、種族、文化,根深蒂固地潛藏在母親心底深處。 從泰瑞的輔導經驗中,不論是未婚或已婚,經歷一次或數次人工流產的婦女,大多數都深覺身心所失的哀傷。在墮胎已廣為大眾接受的古代日本,當然很少人會安慰或體恤要拿掉腹中塊肉的婦女;但是,即使在墮胎文化已深入民心的現今美國,大部分墮胎診所在術前術後,亦極少關注墮胎婦女母性使然的不捨及失去的憂傷。即若有婦女尋求支持墮胎的輔導員開解,持這種立場的專業人士,多會解釋其為情緒波動,是身體荷爾蒙的反應,或者另有令她愁煩的主因,與打胎無關。 可是,正由於人工流產後女性沒有機會或空間面對哀傷,要求或支援她墮胎的男友、丈夫、父母或友人,通常亦不想舊事重提,以致當事人只能逃避傷心的情緒,或刻意忘記,若有朝一日痛苦浮湧上來,便只有孤清地默然哀慟。 不幸地,不少反對墮胎的宗教團體,也犯了支持墮胎者的疏忽,把焦點放在墮胎這個議題的論辯上,但是對曾接受墮胎的當事人,鮮會花心思憐恤和眷顧。以致心坎滴著血的婦女,在教會更不敢分享自己的過去,甚或遠離教會人士。正如在十六歲便懷上了男朋友的孩子,最後選擇墮胎的托利·肖(Tori Shaw),在I Had a Secret for Seventeen Years: A Story of Redemption and Healing after Abortion(暫譯為《我有一個17年的秘密:作為保守的一員,墮胎後救贖和治癒的故事》)一文中所言,她縱然後來信主,也不敢向任何人分享,並因信仰而更自咎,無法從罪責感中得釋放。直至她遇到一位過來人,向她坦承墮胎帶來多年沉鬱無言的痛苦,才讓她恍然大悟,自己並不是唯一孤清地獨自哀慟的人。 曾經墮胎的女性如何走出多年隱藏的傷痛呢?根據泰瑞及丈夫保羅的建議,有五個主要的步驟: 一、面對往事 首先,她們必須從積壓已久的痛苦情緒中釋放出來,因為這些情緒有如未被醫治的感染,常會被某些事情(如墮胎週年)或場景(如好像墮胎吸管的吸塵機聲音)再次勾起心靈創傷,甚至會不斷迴圈對身心造成的傷害。 托利在自己再度懷孕卻又小產時,心境陷入了低谷。後來為墮胎婦女而設的查經班,引導她重新面對墮胎過往。雖然過程不容易,要重溫不想回顧的殘酷抉擇,但最後也因這樣的正視和分享,她不再為埋在心底的禁忌所折磨,能夠有勇氣檢視這經歷對她的影響。
二、內疚與寬恕 當然,有宗教信仰的信徒,會基於教義有強烈的罪惡感;不過,不是基督徒的婦女,基於天生的母性,以及借先進的科技,如超聲波影像,愧疚感也會越來越強烈。 基督徒婦女常會害怕自己的一念之差得不到神的饒恕,教會牧者和基督徒輔導員可引導她們,再次肯定主耶穌為世人釘上十字架的贖罪大能。托利回想自己當初連在禱告中也不敢提這往事,直至她清楚主耶穌在她身上的饒恕大能後才如釋重負。 沒有信仰的女性,也可在輔導師的勸勉引導下,一方面從羞愧的陰霾中走出來,另一方面也明白到須承受過去行為的後果,人生雖不完美,卻有力量承擔,再上人生路。 三、釋放憤怒 女性在得知懷孕到要決定打胎的倉促時間內,通常都會牽及胎兒的父親、懷孕女性的父母或勸誡的朋友。當婦女悔不當初時,會覺得過去身邊的人冷酷無情,如何不支援她或強迫她就範,內心充滿憤怒。 她若不再以受害者自居,體會到各人自有難處,也會做錯決定,自己也有責任時,埋怨別人的怒氣可望徐徐消減,慢慢打開通往寬恕他人的道路。 托利對昔日的男友,即今日的丈夫,當初沒有陪伴她前往墮胎診所的怨憤埋藏了多年,直至她坦然和他分享長久的委屈,才得以釋懷。丈夫也明白到因自己的疏忽,傷害了她而不自知。 四、接受所失 大多數人工流產的女士沒有見過胎兒的遺體或殘肢,這會令她們難以具體表達永久失去孩子的哀傷。托利為自己未成形的嬰兒取了一個名字,因為她不知道其性別,故此選了一個中性的名字泰勒(Taylor)。 此外,正如葬禮可以令喪家正式接受家人已經逝去,同樣地,曾墮胎的婦女也可以為胎兒舉行簡單的追思儀式,托利在紀念墮胎兒的花園(A Memorial Garden for the Unborn)擺上刻有孩子名字的磚塊,更在2019年開創了紀念墮胎兒的追思服務(Memorial Service for Victims of Abortion)。曾打胎的女士也可以用日記寫出個人對胎兒的感受,或寫一封信,這樣可以把哀痛化作語言表達出來。 五、繼續前行 即使打過胎的婦女一步步跟隨這些步驟,但各人的康復時間都會不同,而且也不代表她們會完全忘掉墮胎的經歷。關鍵是,她們要知道雖然墮胎是她們生命中重要的一課,但這一課已經完結;若日後悲慟之情再次湧上來,即若難免灑淚,她也已知道舊事已過,她的人生可以繼續。 托利回顧她墮胎的經歷時漸漸明白到,她看作羞恥的過去,已經透過神的啟示得到更新。她鼓起勇氣的分享及同理心服務,成為仍陷在幽暗中愁煩不能自拔的婦女的安慰。 近年來,越來越多輔導員發現那些尋求墮胎的婦女,雖然短期內似乎解決了懷孕帶來的煩惱,可是,日積月累下來,卻成為長期的憂傷,因而興起了流產後綜合征(Post-Abortion Syndrome)這個診斷名詞。 造物者真奇妙,不論在未接觸基督信仰時期的日本,還是力挺墮胎權利而否認腹中胎兒是生命的今天西方社會,經歷過人工流產的婦女,心中仍具造物者賜下的心繫胎兒的母性,遠非潮流文化所能取代! -END- 作者簡介 玲言 美國俄亥俄州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Ohio) 歷史檔案學碩士及歷史系博士,專研美國華人歷史。在臉書專頁「來,咬一口」分享讀書心得,並不定期為美國華文雜誌如《真愛》、《神國》、《傳揚》等撰稿。 圖書推薦
《恩典不留白,下筆如有神》 -莫非 蘇文安 劉小臨著- 恩典故事前, 人人皆可 自許為作者, 書桌乃朝聖祭壇, 生活如展頁稿紙, 捕捉心中悸動, 描述看不見的你! 購買資訊: 台灣:橄欖華宣 https://www.cclm.com.tw/book/19314 北美:gcwmi622@gmail.com |
|
| (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