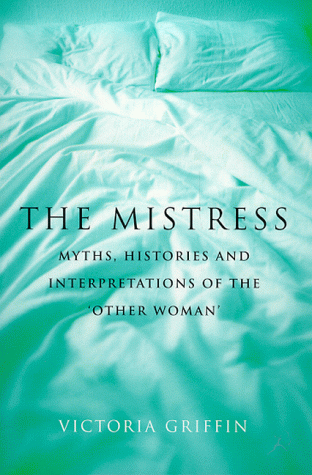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6/02/17 00:07:57瀏覽8456|回應7|推薦40 | |
維多利亞‧葛麗芬(Victoria Griffin)自承是情婦,並且寫了一本《情婦》。她搜羅、研究西方文化中所謂「情婦」的傳記、史事和神話,不只為了討論「另一個女人」這個角色的歷史、典型和社會定位,並有意從中「檢視自己」的情婦生活。 葛麗芬以通俗並耐人尋味的文筆記錄並解剖「情婦」的迷思,雖不乏自省,但又比較像為情婦辯解,更多是自我安慰:只有認同「情婦」的社會定位和功能,「情婦」才可能盡興地活著或愛著。 「情婦」(Mistress)不但是男人的發明,且是父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分類,無論在西方或東方都充斥著貶義和偏執,是一個老掉牙的名詞。因此,自稱或多或少是女性主義者的葛麗芬表示自己是「情婦」,並且樂意「對號入座」,使本書徹底響著一種矛盾的基調:所謂的「情婦」既是贊成「一夫多妻」的獨立女性,同時是遵從傳統社會價值但又逃避社會秩序的怪物。 葛麗芬強調,「只要有婚姻,便有情婦」,她評頭論足的不只是現代婚姻制度,更把矛頭朝向結婚的家庭婦女,她說,「現代婚姻企圖創造平等的伴侶關係,而女人在要求平等的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必須放棄從前扮演的角色,不僅包括無可逃避的母職,甚至包括成為丈夫的好幫手」,她進一步說清楚:「現代社會忙碌的家庭主婦已無暇為在外頭忙累一天的丈夫斟酒放音樂,也沒有意願耐心地傾聽他們,有誰能彌補這些空缺呢?當然是情婦了。」葛麗芬認為,「情婦」便是現代婦女在婚姻關係中必須付出的龐大代價。 「情婦」所謂的情欲解放,乍看是一種掠奪,但無論在新舊社會中,卻又只能處於被動及比「元配」低下的社會地位。而忙著為現代情婦角色定位的葛麗芬,不小心卻一頭栽進舊式父權社會價值標準的陷阱。忙碌的家庭主婦可能無暇體貼丈夫,倘若雙方彼此尊重和相愛,為什麼傾聽或斟酒倒茶只是家庭婦女的義務呢? 「情婦」的出現絕不是家庭婦女單向的問題,是婚姻生活中雙方可能承受的一種分歧面貌,與情婦對象之感情態度也息息相關。葛麗芬知道,大部分與「情婦」交往的男人,不會只甘於一個情婦,但「感情關係的非法,正是愛情的明證。男人冒若干風險,就證明他還愛慕著她」。葛麗芬可能弄錯了,在非法的感情關係中,冒險的人絕不只是男人,做「情婦」的人可能必須具備更大的勇氣。葛麗芬忽略的正是,只有那些想逃離婚姻約制卻不能的男人才會尋找「情婦」的伴陪;與「情婦」和「元配」共生的感情方式,經常是那些不負責任且沒有愛人能力之男人的最佳選擇。 這裡便是從古至今所有情婦的共同命運:她們不但必須活在《崔斯坦與伊索特》的悲劇本質中,只能把分離的悲苦當成人生激情,且時而必須處於兩極對立的心理狀態裡,一種永恆身分認同的追尋和質疑,一方面自認比「元配」優越,一方面又不得不自問:我究竟是不值得被愛呢,或者我根本不要那樣的婚姻關係? 情婦因此不只有可能是佛洛依德所稱的「道德受虐狂」,可能也同時必須服膺某種程度的享樂主義。按照葛麗芬的說法,追求婚姻是情婦的下下之策,不但目標錯誤也不會成功。只有禪學那種「活在當下」的人生態度才可能讓情婦的生活圓滿,只有「愛但不求回報」的感情方式才能拯救情婦的人生。但這些說法不但容易流於自欺欺人,很可能也只是「情婦」逃避現實生活最大的藉口。 葛麗芬傳統的「異性戀」邏輯漠視了成為第三者的其他可能,譬如「情夫」,儘管這個名詞在英文中尚不存在,但正因現代家庭婦女在婚姻之外也可能與他人發生戀情,更印證了「情婦」這個字被附加太多如玫瑰騎士般的古老社會意義。 現代女性在潛意識中極力想顛覆的也許正是傳統社會裡「情婦」典型。「情婦」這個名詞不但不再存在,含意的正是一種矛盾女性情境,對社會的屈服和反抗,一種自我與原我間的反覆掙扎,一種傾向自私或自恨並逃避現實的情感。 誰想當情婦? |
|
| ( 不分類|不分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