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曠野中獵日 陳 今
——戰車兵手記
…………
坐在戰車內,背靠著堅硬的車壁,像坐在船內,戰車被石塊海浪震得一路顛顛簸簸。暈眩。一陣又一陣極強烈的混亂猛搖晃著腦海。無法靜下來。也無法逃脫。必須穩定自己。必須尋找一個姿勢,重心剛好最適合自己去抵抗那幾乎已成為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前進震撼。
鐵是坐不暖的。尤其在冬天的深夜,蜷縮在破浪猛進的戰車內,我只感到冰冷。抬頭仰望開敞向夜空的頂蓋門,無數顆銀星正夢般地懸在遙遠的空曠中燦閃著它們那亮麗的寧謐。如此含蓄,如此超卓,永遠孤絕於塵世的動盪之外……
黃昏時,戰車開進野樹林。今晚就在此地過夜。從外面很難發現我們。
巨拳般揮向野生灌木的九○砲被樹枝緊緊抓住了,無法搖到預定的警戒方向。裝填手從工具箱裏取出斧頭,下車砍樹。他用力過猛,斧刃像砲彈般飛出去了,結實地打在履帶上。再高十公分,正站在戰車上旁觀的駕駛手勢必非「跳腳」不可。「想殺人滅口啊?!」我下車協助裝填手把斧頭修好。接著是一陣淒切慘絕的斷裂聲。邊下毒手我邊向那幾棵愛作怪的野樹道歉。
夜幕逐漸籠罩大地。砲塔室內的射手終於把九○砲搖到預定的方向加入本排的警戒網。
夜行軍。
全副武裝,我們沿著公路兩旁的路燈前進。遠處的田野一片漆黑。「蕭邦!」「卡夫卡!」「蕭邦!」「卡夫卡!」*像在夢中朝聖似的。弟兄們躺的躺,坐的坐,站的站,大部分都在休息,也有的在聊天。我背靠著隧道外面的斜坡假寐。好冷。霧越漫越濃。河谷凹凸不平,到處都是死硬的石頭。天空跟大地一樣黑,甚至連自己的手也被絕對的黑所浸透。只剩下感覺是活的。心,七上八下地舉步,每一步都是危險的未知。沒有任何人能替你走完這趟旅程。為了保密,翻山越嶺時就算摔死了也不准亮手電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行軍時,有些弟兄喜歡用閩南語默唸:「右腳!」「左腳!」「右腳!」「左腳!」也有些弟兄喜歡暗自答數。我則喜歡默唸我心目中最神聖的兩個名字。
挾著M十六步槍,他警戒右方,我警戒左方,「醜臉的」和我面對面地在林園的大門口站衛兵,防阻歹徒衝進園內破壞戰車。部隊已帶去山頂實施「夜間倒置訓練」,要到凌晨才會回來。
「醜臉的」打開他的防毒面具袋,拿出偷藏在裏面的兩罐鳳梨汁。「這罐給你。」我們邊喝邊聊天,同時更加機警地注意周遭的一切動靜。因為學過「鶴拳」,所以「醜臉的」擁有一張酷似鶴的尖臉。他淡淡地向我述說他在連上揍人的往事(語氣那麼淡,彷彿談的是別人,不是他自己):「都是該揍的……『硫磺』偷換戰車最終傳動器的螺絲,被我抓到……『死混的』慢接衛兵還不肯道歉……阿昌向『心酸的』借五百元不肯還,以為新兵好欺負……」他都是在半夜一對一地執行他 的律法。很公平。但被他「點名」的壞蛋卻沒有一個不鼻青臉腫的。
除了拳頭比別人硬之外,「醜臉的」也寫得一手好毛筆字。那是他手掌心夾著生雞蛋,拜師苦練出來的絕活。「什麼體?」「顏體。」尖削的鶴臉上,霎時靦覥地綻開兩罈酒窩,像古井般的。
那種草很高,穗灰白,像梳子,也像孔雀羽毛。風吹過時,彷彿揚琴的觸刷般輕敲著呼嘯的韻律。我突然聯想起女人白皙的手在如風般不斷柔拂著男人大地般的胸膛。那麼多的手!那麼多曖昧的溫柔!有點兒令人噁心,也有點兒令人震驚於人類的原慾之旺盛。
那種草生長在泥地上,荒涼乾硬的泥地上,不是蘆葦。
喧噪的蟬聲緊緊包圍了我們設在林中的營地。聲浪一波未息另波又起。一種非物理學的加速度,越來越尖銳的。是在抗議陌生人擅闖私地?還是在歡迎嘉賓遠道來訪?
半夜,被蚊子叮醒。兩隻手密聳著包子般的肉山。攜帶睡袋、野地的蟲聲和一顆懊惱的心,回歸我們第三排的大帳棚。
這些傢伙,一個比一個會享受!你看他們,個個都四腳朝天,睡得不省人事。這兒那兒,到處都有蚊香環繞在他們身邊為他們殺蚊催夢。空前大爆滿!恐怕連蟑螂都很難擠得進去。但我不肯死心,還是拚命地往裏面硬擠,猛擠。終於在帳棚進出口處的臭鞋堆旁邊爭得一席安身之地。
「總算可以好好睡一覺了……」沒想到,眼還沒闔攏,剛下衛兵的小朱竟異想天開,把腦筋動到我頭上來了。他也學我的樣,拚命地往我這邊硬擠,猛擠,好像把我當成一具沒有感覺的屍體似的。我實在受不了了,驀地喝斥一聲—— 「!!!……對不起!……我不曉得你還沒睡……」被嚇了一大跳的小朱又尷尬、又羞愧,像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卻被人當場逮著似的,忙不迭又逃往別的海域去尋找願意讓他的小船泊岸的港口。
翻過身去,我在心中暗暗告訴自己和鼻尖那堆睡相比豬還要邋遢的臭野戰鞋:「其實你並不厭惡小朱,一如你並不厭惡那個拒絕再被蚊子叮醒的自己;你也並不可憐小朱,並不可憐那些剛下衛兵的弟兄,因為再過兩個多鐘頭你自己也要上衛兵。在軍中,大家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同情別人。然而我知道你痛恨蚊子,打從心底痛恨——那些吸血像喝水的惡鬼!——永不知足地,牠們老想在我們身上掘出奇癢難耐的墳塚!」
在曠野中預演陸總部仿步兵連的核生化測驗。
預演完畢,連長下令:「衣服沒有濕透的,去跑到濕透,才准上車。」敞篷的卡車硬擠了六十幾人。經過妓女戶時,兜繞一圈,才回營。三個妓女,我們叫,她們笑,相互揮手。其中一個妓女說:「嘿,我認識你嘛!」手指著我們車上的某位弟兄。大家都很純潔地笑了。
我們這一組分三班,從左翼發動攻擊。三人一班,採三角隊形。我躲在草地左邊,小柏樹的陰影下。晴空萬里。一個適合戰鬥的好日子。太陽熾烈得像一鍋熱騰騰的金湯銅漿。我前面和右邊的草地上各趴臥著一位弟兄。蓄勢待發的蚱蜢般,另一組的人馬趴臥在馬路的另一邊。硬邦邦的碎石路。等待。一種焦躁不安的空白。風呼嘯著掠過曠野。沙塵從地面飛揚向天空。一陣又一陣的黃霧……
哨音響了!……
「攻擊前進!」
衝啊衝啊衝鋒至鐵絲網邊臥倒出槍槍身靠在鐵絲網上鋼盔靠在槍身上腦袋靠在喘息上等待另一組的人馬狂風般掃掠過身邊衝向三十步外的電線桿提槍跟進衝啊衝啊衝鋒至另一草原遠處兩輛卡車顛簸飛馳浪花般沙塵越濺越遠臥倒怦怦怦怦心跳怦怦張口喘息等待煙幕信號彈驀地劃空爆響翻身仰躺白花花一片炫亮猝然猛刺雙眼好潑辣的火球雙腳夾槍脫盔扯開掛在左腰的袋釦取出防毒面具迅速戴上復盔翻身趴臥出槍警戒汗水氾濫全身濕透黏熱渴由它去吧提槍躍起繼續衝啊衝啊衝鋒前進˙ㄎㄡ˙ㄎㄡ˙ㄎㄡ什麼東西連踢屁股好幾下邊跑邊回頭看啊水壺掉了該死的掛鈎後面那位弟兄幫我撿起來還我鋼盔下的臉是一副森黑的防毒面具從噩夢中逃出來的妖怪邊跑我邊用左手接住水壺抱在左胸前像抱什麼心肝寶貝似的右手提槍搖來晃去繼續衝啊衝啊衝鋒前進防毒面具透明的眼罩模糊不清看外面的世界像一場正在上演的電影主角是我也是觀眾邊跑邊看戲衝衝衝衝衝衝衝肺快暴脹到極限了心跳怦怦嚴重缺氧都是濾毒罐作怪過濾掉大部分的空氣衝啊衝衝衝衝衝老天我快無法呼吸了踉踉蹌蹌身體會不會突然散掉不行不行只剩幾百步再苦你也要撐給測驗官看衝啊衝啊這是陸總部的測驗攸關本連榮辱不賣命演出如何向大家交代衝衝衝衝振作起精神繼續衝向前去越跑越慢該死的曠野為什麼這麼寬闊彷彿永遠跑不完似的怦怦怦心跳怦怦肺快炸開了啊老天這次我真的快窒息而死了為什麼不肯讓我卸下防毒面具多給我一些空氣咬緊牙關忍下來吧衝啊老兄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熬過去的別想撒賴你還得再熬半個世紀才夠資格安息呢衝啊衝啊駝背埋頭望前衝噢可恨的防毒面具我絕不向你棄械稱臣衝吧繼續衝啊衝啊衝衝衝衝衝衝衝終於我終於跟其他弟兄一起衝進這片伊甸園般的灌木林飛撲向比人還高的雜草叢擱槍脫盔猛拉鬆緊帶卸下防毒面具打開草綠服上面的鈕釦一口一口又一口迫不及待地吞進如此寶貴的空氣疲憊已極仰天躺臥在彷彿自世界末日的噩夢刀口逐漸回返人間世的深沉喘息中……
肺和心臟都很寬宏大量,它們不一會兒就跟空氣握手言歡了。我坐起身來,環顧周遭。這片灌木林很大,很茂密,裏面一片綠。像在跟誰玩捉迷藏遊戲似的,弟兄們這兒躲一個那兒藏一個,大家都緊抓住機會,盡量讓自己過得舒服些。我旋開水壺蓋,仰天一連灌下好幾口水。啊,真爽!順手撿起一塊石頭敲正水壺的掛鈎,然後解下S腰帶,把耶穌釘上十字架般地掛上水壺。水壺跟S腰帶剛好形成一個鈍重癡肥的十字架,缺了頭的。我躺回乾草堆的懷抱,頭枕著鋼盔歇息。風沙很大,有一搭沒一搭地掠過樹梢,宛若大地之母在哀號她的悲歌。但林裏很靜,很寧謐。「偵檢組」和「消除組」的弟兄正在林外正前方不遠處當著測驗官諸公的面表演這次核生化測驗的重頭戲。邊解毒邊報告。台詞不是用說的,而是用嚷的,又機械又響亮,我閉上眼睛都可以在腦海中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動作。此刻,他們之中的兩位弟兄——很可能是「肉餅」和「查某人」,至少聲音很像——正在協助「肥豬」穿上百毒不侵的「太空衣」。一定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數吧?辛苦他們了。我懶洋洋地睜開眼睛注視地上的野草、沙粒、螞蟻……啊,好大的小世界!造物主真是心細如絲……一縷縷味如淡茶的香煙慷慨地從什麼地方飄來我這邊讓我過乾癮。那是阿忠。他坐在我雙腳左前方的灌木旁,屁股壓著他的鋼盔……
「嘿,快起來!我們馬上要出發了!」這禮拜值星的老車長「甘蔗嫂」像隻獵犬般機伶地在灌木林裏到處挖角找人。
我迅速著裝完畢,擁槍鑽出雜草叢,漫步上前線,和陸續自樹蔭下冒出面具黑得可媲美暗夜的弟兄們一起趴臥在灌木林的前緣待命衝鋒。逍遙的「蜜月」終於接近尾聲了……
「攻擊前進!」
衝啊衝啊剛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百獸之王」般我在曠野中瘋狂追獵自己看不見的獵物而且還煞有介事地堅持自己所選定的方向筆直飛去像一枝長了兩隻腳的箭閃電般「狀況解除!」猝然劈響是副連長林肯在解放黑奴的雄偉聲音霎時墓碑一塊接一塊紛紛撲倒在大地上翻身仰躺脫盔卸下原先被毒氣綑綁在臉上的黑色面具塞進掛在左腰的袋子裏復盔翻身趴臥提槍躍起繼續衝啊衝啊衝鋒前進至假城鎮被一聲爆響啊核子彈空襲絆倒在民房牆腳漆有黃綠兩色迷彩頭背向炸點身體與牆平行雙肘撐地塞耳掩鼻張口胸部離地十公分闔眼等待置身事外的空白只是演戲「狀況解除!」提槍躍起從左側繞行越過亦即攻佔假城鎮繼續衝啊衝啊衝衝衝衝衝上山去矯健如豹「鍋巴」從這一山頭凌空騰躍至另一山頭鼓舞接應尚未凌空騰躍的彼岸弟兄「不要怕!盡量往上跳!」斷崖與斷崖間約莫兩公尺中空深淵不知有多深越來越近掉下去準沒命亂恐怖的對岸落腳處微向上傾一二三四豁出去跟你拚了衝啊身軀凌空拔起恍若蒼鷹般飛刺向高懸頭頂虎視眈眈的太陽落地接住老車長有力的援手「謝啦!」邊衝鋒邊上刺刀「殺!殺!殺!殺!」前進突刺壓槍砍劈聲震天地刺向敵軍兵敗如山倒的假想心臟……
一個接一個,我們小心翼翼地沿著沒有路的陡坡下山。集合。整隊。恭聽測驗官講評。汗水果然沒有白流,高昂的鬥志為我們打贏了漂亮的一仗。當我們踏著抖擻的步伐托槍經過兩山交界處時,弟兄們都不約而同地抬頭仰望那介於兩山之間的恐怖深淵。沒有人會忘記,剛剛,在那「空前絕後」的凌空一躍中,在那超脫於生死之外的剎那間,我們曾牢牢地攫獲那永遠高高在上,一動也不動,卻又無時不在動,似乎永遠不可能被觸及的「光之神祇」(因為它無時無刻不在迸射出足以銷熔一切的狂烈熱焰;投身向它,亦即投身向毀滅)——那無從還原的永恆太陽。而不知怎的,正陶醉於光榮凱歸行列中的我,內心深處突然湧現出一種理解,一種越來越堅實的理解,那就是,也許我們可以如此看待眼前的這三座舞台:第一座山是可知的現狀;第二座山是謎般的未來;而介於兩山之間的深淵,則是刺激我們超脫現狀躍昇至更高未來的嚴酷考驗。
庸俗的人在經歷了卑微的偉大事件後,往往會為自己的怯懦冠上英勇的訓示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在軍中,猶如在與世隔絕的極地中一樣,有誰不需要烈日的慰藉?
和「老千」到水溝裏,拖出昨天下午就預先割好的牽牛花藤蔓。一人抱一大把,披上我們的戰車當偽裝網。
其實披了反而比沒披更容易被敵機發現:一座鐵灰色的、會走動的笨重花園, 上面爬滿了鬍鬚般的青綠色藤蔓,盛開著淡紫色的牽牛花。
有什麼辦法?沒錢買偽裝網,又不能不應付上級的檢查。
「車尾那邊鋪完就可以了……不曉得這樣行不行?……我再去拿牽牛花……」一向木訥的老駕駛手朝我無奈地笑笑,走了。
我有些擔心草屑會從引擎蓋的縫隙鑽進車的體腔內,遮住散熱片——那簡直 跟蟯蟲鑽進人的體腔內蛀蝕人的腸壁一樣可怕——因為戰車行進時總是晃盪得很厲害,而牽牛花的藤蔓又總是窩藏了那麼多的草屑。
散熱片一破,我們的「鐵蛤蟆」就算再神勇也會四肢癱瘓,當場停擺的。
出車支援裝步營演習。
頭探出頂蓋門,背靠著砲塔壁,腳踏在車內鐵製的座椅上,我閒閒地挾著M十六步槍看風景。
軍事風景。乾燥的曠野。雜草。碎石。熾烈的陽光猛刺著肌膚,猛刺著萬物,毫不容情。
我們的戰車是鐵打的神祇,龍騰虎躍在溫馴脆弱的大地子民身上,掀起驚天動地的信仰風暴。黃沙滾滾。坐在我們雷霆部隊的戰車上,相信就算再卑微再頹廢的人也會被這種威風八面的前進氣魄給激盪得豪情萬丈。而車外的那些異教徒 ——那些裝甲步兵——則苦哈哈地尾隨在我們戰車後面拚命向前衝鋒陷陣。他們端槍快跑前進,又猝然臥倒出槍,在荒涼的曠野中激起一波又一波不足為外人道的果敢沙塵……
貨櫃般的巨大車廂。黯淡的鏽紅色。輪子不知流浪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座鐵打的監獄,門戶洞開向對面的公墓。因年老而遭淘汰。
跳下戰車,我們這羣年輕小夥子一窩蜂衝進這個臨時避難所躲雨。
同樣的場地,同樣的營測驗,一樣是六十碼外的歸零靶,一樣是戰車三○機槍的第一習會射擊,今天,代表本連受測的孫車長打了滿靶,為自己贏得三天的榮譽假,而去年受測的別營弟兄卻出了命案。
他叫「小黑」,是該車的老駕駛手。當時,蹲在戰車上剛檢查完機油的他,人還沒完全站起來而致命的劇痛卻已伴隨意外的兩聲「達!達!」鑽進並爆潰他的意識層,將他重重摔倒在引擎蓋的鐵板上,甚至連回頭瞪死神一眼都來不及。
聽說只要再熬一個多月,他就可以功成身退,榮歸故里了。由於不甘心,夜半時,他的冤魂經常會出現在他們營上的車場,陪伴他同連的弟兄守著戰車站衛兵,和他們一起癡癡地等待退伍解放日的到來。直到那天真的被他等到了,他的冤魂才像踐履了一句諾言似地,翩然消失,從此不再驚嚇車場中的衛兵。
至於跟他同車的那位菜鳥裝填手,後來到底有沒有被判刑,或到底付了多少賠償金,知道的人並不多,因為出事之後,他就立刻被帶走了,再也沒有回到他的連上。我們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這位在無意間當了殺人兇手的菜鳥裝填手,日後必然會因自己當時的無知和疏忽而痛悔不已。他一定會一再地憶起:在他貿然裝子彈——因為「靶場安全守則」有如下之規定,而這是我們戰車兵人盡皆知的:未接獲命令,任何人均不得擅自裝填或擊發子彈——之前,他根本不曉得砲塔室內的那挺三○機槍有毛病,更不曉得子彈才剛裝進槍膛,竟然會馬上就自動發射出去(「我根本沒碰扳機啊……」),而且還連射兩發,一下子打爛了素來為他所敬重的老駕駛手的脖子,就好像老練的政客連揮兩刀,一下子斬斷了無辜的雞頭那樣。「我當時為什麼要貿然裝子彈呢?」「是怕到測驗開始時才裝會來不及?或者僅只是由於無聊?僅只是由於不曉得該如何打發測驗前太過緊張的等待時刻?……」然而,無論他如何悔疚,無論他如何自責,已發生的事情就是已發生了,永遠也無法改變,永遠也無法補救。這種事實甚至比金剛鑽還要堅硬。
生命太脆弱,有些錯誤人是絕對犯不起的,尤其是那些專靠無知和疏忽來成全的殘酷錯誤。
靶場。戰車砲射擊。
十二輛戰車同時爬上射擊台。「九、八、七……」猝然自噩夢中驚醒般,幾乎在同一瞬間,大地激狂地朝一向高壓於其頭頂的天空迸吼出十二響銳悍的霹靂:「ㄅㄧˋㄤ!ㄅㄤˋ!!ㄅㄨˋㄥ!!!……」浩氣因相互重疊而壯大數十倍,將心虛的時空震撼得悸顫不已而釋放出十二個月分或十二顆美夢,宛若一條條金蛇般拖曳著熾燦的流星尾巴飛竄向高聳在一千五百碼外崖岸上的藍色紗網戰車靶,然後不論命中這些巨型墓碑或落空,都頹然墜入永遠那麼深邃的宇宙大海……
…………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七日; 獲當年中國時報散文獎甄選首獎。此文還被收入九歌版的 《七十五年散文選》和二魚版的《臺灣軍旅文選》中;並 被英譯收入臺灣的中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 Winter 1987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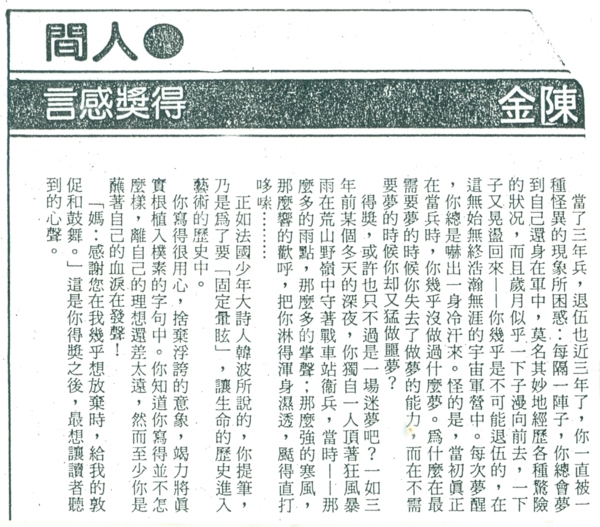
更多資料請參閲:https://album.udn.com/chenjin1960/632245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
字體:小 中 大